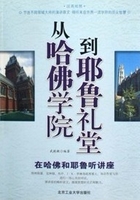染上了残余的毒,似乎并不只是伤到了表面,而是悄无声息地渗入到了更深的地方。
哪个角落都渗到了,麻酥酥的感觉,仿佛千万只细微的小虫,交错慌乱地爬动着……
燥乱的世界,燥乱的一切。
所有的真实都变得虚浮飘渺,无根无据。
红袖觉得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像是忽然如坠入七尺寒冰之中,浑身冷得打颤,而瞬间的工夫,又仿佛沉浸在烈焰的炙烤之下,五脏六腑都滚烫难忍,就这样忽冷忽热,忽热忽冷,几千年弹指而过。
无数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嘈嘈切切,来自遥远的九天之外,杳无人迹的山谷深峦,传过来,又拂过身畔,没有一句能够听得清楚,仿佛又回到了将军府,她还是几岁光景,光着脚在空无一人的碎石子路上奔跑,一个人都没有,四处静得可怕,蒿草长得比她的身体还要高,湖水死一样沉闷,花树的繁叶谢了一地。
各处房间的门都紧紧关着,拱桥边,疏影下,再也没有来往穿梭的人。
只有高高的慈恩斋上,还有一声声空洞的木鱼之响,回荡在寂寥苍冷的将军府。
她仰望,只看到某人一个飘过的衣角,一个朦胧的背影,也许是花了眼。
风景忽而变换,她又置身于铁马金戈的大漠之中,两处江山利益的碰撞,让她的脚下血流成河,哀号遍野。
红袖依旧是那个光着脚的孩子,将军牵着她的手,从刀枪剑戟中走过,人们只被血腥的杀戮疯魔了双眼,竟然看不到这两人正从身边走过。
“爹爹,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残杀?”
“因为他们都是可怜的棋子,要巩固别人的位置,只能冲锋陷阵,死而无怨。”
“谁让他们去死,这一切是谁安排的?”
“是权利。”将军微笑着,静静回答:“是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人,那个人,手里握着这些棋子的命运。”
红袖只是略一思索,再抬头间,发现将军早已松开了她的手,渐渐走入在风沙中,好远,与她隔断了难以跨越的距离。
“爹爹!”红袖赤脚追过去,越是追,将军的身影就越模糊。
红袖不敢再走,她站在原地,流着泪,大声呼叫:“爹爹,你要去哪里?你带我一起走……”
将军一身铠甲,威风凛凛,只是眉宇间似乎多了几分凄凉和无奈。
“红袖,爹爹也是一个棋子。”
“爹爹不能带你走……”
他凄楚的笑容还隐约可见,在一个虚无的空间里,和无奈的声音,一同晃晃荡荡——
回过神来,是将军府里湖水的荡漾的倒影。
哪个是梦,哪个是现实?
无数命运的片段,红的,橘黄的,赤金的,在狂风汹涌的湖水之中,上蹿下跳,歇斯底里地厮杀着,又悄无声息地归于平静……
一切都平静了下来。
整整六天。
红袖昏昏沉沉,在六天之后的下午,轻轻开启双眸。
身子仿佛被抽空了,虚飘无力。
“含玉……”
细弱蚊蝇的一声,还是被坐在桌子边发呆的含玉听到,她扑倒在床边,把红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眼泪迅速翻滚着溢出来:“小姐,小姐,你可醒了,你要让含玉死掉了。”
“我这是怎么回事。”红袖望着四周。
“小姐,你中了毒箭,忘了吗?”
红袖轻簇着眉,意识渐渐聚拢了来,是了,在密林里,一支呼啸而来的长箭,她替兰儿拦了下来,此后的事,她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红袖努力坐起身,肩膀靠近胸口的地方,还是隐隐作痛,她倒吸着气。
“兰儿,她没事吧?”
“没事!”含玉为她掖着被角,擦干脸颊,有些不满地说道:“到现在还只顾惦记别人,你知不知道,你中的可是毒箭!是有性命危险的,要不是少……”
含玉突然止住不说,只闷头给她倒来一杯热茶,小声说道:“这些天,小姐迷迷糊糊的,都没怎么吃东西,先把这热茶喝了吧。”
几口热茶饮下,红袖全身都暖了起来,她定定神,疑惑而略带责备地望着含玉,轻声说道:“你怎么又叫我小姐?”
“含玉是觉得,左右……现在……”她忽然咽下下半句,脸微微一红:“小姐不喜欢,我再改过来就是了。”
“含玉,你今天怎么吞吞吐吐的,难道有什么事,瞒着我么?”
“没有……没事。”含玉的脸越发红了。
“含玉。”红袖放下热茶,佯装生气。
含玉咬着嘴唇,过了半天,才低头轻声说道:“小姐中了毒箭,是少庄主为小姐拔出来的,又用冰泉为小姐浸泡疗伤,小姐的女儿身份,少庄主他……他已经知道了……”
“什么?”
红袖坐直身子,胸口一阵刺痛,她额头冷汗直冒,盯着含玉:“你说的,都是真的?”
含玉点点头。
红袖一时呆在那里。
含玉犹犹豫豫地说道:“小姐昏迷的这几天,庄上很多人都来看过你,慕容寂,安伯还有庄主他们都来探望过,庄主他……为小姐吸毒,自己身体也受到了影响,近日才好些,他还来给小姐喂过药。只是小姐昏昏沉沉,都不知道这些。虽说少庄主他看穿了小姐的身份,但是似乎并没有说出去,别人也还蒙在鼓里。”
红袖的眼睛还是直直的。
“来看望小姐最多的,自然是兰儿,她每一天都要来问好几遍,问你醒没醒,按时吃药没有,小姐,含玉看得出,兰儿姑娘她,似乎对你动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