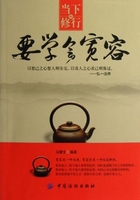“柳尚书勿怪,我从不曾怀疑柳尚书的公正,可是光凭一个老鸨的证词将霍如氏的死因强行牵扯在霍帝师身上,未免过于牵强。”欧阳时易抬起头来,目光迥然,“更何况,柳尚书如何能够证明老鸨的证词切实可信?难保她不是为了有心人的威胁利诱而说出违心话来。”
“你!欧阳尚书你这才是牵强附会!为了维护霍帝师而说出这种话来,你不觉得虚伪!”
欧阳时易忙朝着司马天熙拜了一拜,大声说道,“陛下,非臣维护霍帝师,只是这其中有太多蹊跷之处,还请陛下再细细查询,免得冤枉了朝臣,让众朝臣寒心。臣愿意以项上人头担保,霍帝师光明磊落,绝对与霍如氏之死有丝毫牵扯!”
霍氏一派立刻跟风跪下,“臣等也愿意以项上人头担保!”
霍凤回头看着身后跪倒的一大帮人马,心中说不出什么滋味,明明知道这些人都是趋炎附势或者惧怕她日后报复而跪倒的,可仍然多少一些感动。感动之余居然全是惧怕。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凤眸微睐,心中微动便定了计议,她看向司马天熙双膝及地而跪,“陛下,臣光明磊落,绝不会做这种伤人性命的事情!臣愿自愿下狱,待陛下彻底调查后还臣清白!”
只有自愿下狱,才能让司马天熙的君王颜面得以保存,对她日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司马天熙此时已经坐直了身子,食指微屈叩击桌面,一时沉吟不语。
桌面乃金木所制,敲击之下其声沉郁,在寂静的御书房里分外明显。
一滴冷汗从额际之上滑落,霍凤双拳紧握,尖利的指甲刺入掌心,钻心的痛。
“老师可如此说,孤可不敢如此办啊。”
霍凤心中一紧,“陛下!”
柳泉猛地跪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霍如氏虽然小小女子,可也不能死的糊里糊涂,还请陛下为她伸冤!”凶戾的瞪了霍凤一眼,“就算杀人者是朝廷重员,陛下也不可徇私!”
叩击之音蓦然一顿。司马天熙有些苦恼的皱了皱眉,“不过是一个小小女子而已,还要劳烦孤烦心,老师,你道该如何是好?”声音里居然全是仰赖之意。
霍凤吃惊抬头,他有没有搞错,这种事情居然问她这个犯罪嫌疑人。
果然,夏侯逸咳了声,“陛下,此事问霍帝师,恐怕有失公允。”
司马天熙似是呆了呆,转而看向夏侯逸,“那夏侯有何良策。”
夏侯逸面露惶然,“臣不敢!”
“说你敢就敢,昨日劳心太久,孤也乏了。”话一说完,他双手往桌上一搁,居然仆桌小憩了起来,金袍飘飞,风姿说不出高雅。霍凤看的有些呆,再看向四周,众官都是一脸泰然,似乎已然习以为常。
暴汗不已,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君王。
“臣以为……”夏侯逸思忖了一下,慢慢说道,“光凭春香阁老鸨的证词确实有些勉强,为了不失公允,臣以为可以令一大臣主审此案,此外再派人监察,如此一来,定然不会误放了凶手了。至于这主审大臣……”他嘴角扬笑,笑似狐狸,“臣推荐欧阳尚书。”
漂亮的凤眸微眨了眨。她有没有听错?
夏侯逸唇边的笑容愈发诡秘难猜,“至于这监察之人,臣推荐霍帝师!”
霍凤彻底呆住,缓缓瞪看夏侯逸。
柳泉本在夏侯逸提名欧阳时易时已经震住,又听霍凤是监察之人,更是如遭雷击。他不置信的看着夏侯逸,声音有些发苦,“相爷,这万万不可啊。”这摆明是纵虎归山,相爷糊涂了吗?
夏侯逸不置可否,轻道,“陛下以为如何?”
司马天熙似乎已然睡着了,呼吸均匀,隐约有轻微的鼾声传了出来。
小林子小心翼翼的轻叩桌面,司马天熙猛然从睡梦中惊醒,睡眼朦胧,“夏侯是说了什么来着?”小林子连忙低声在他耳边重复了一遍,司马天熙听完,闻言击掌大叫,“好主意,众位爱卿可有异议,若无异议,就这么办了。”
众朝官齐齐恭道,“陛下圣明!”
“陛下!这有失公允啊!”柳泉急叫!“陛下,霍家势大又有野心,不得不除啊!”
司马天熙眯了眼睛看了会,忽的用力拍案,勃然大怒!
“柳泉,朝臣都不反对只有你一人说孤有失公允,霍家又是九代忠臣容得你这么污蔑!念在你年事已老也到了颐养天年的份上孤就不重罚你,从明日起你就不用来见孤了,你的位子就交给夏侯兼任着吧!真是混账,退朝!”
他哼了声,匆匆拾阶而去。御书房内一阵寂静,众朝官松了口气,纷纷离去。
柳泉依旧匍匐在地上,长须灰发似乎更加苍白了些,嶙峋身骨在一群昂首挺胸笑意昂然的官员愈发显得狰狞。一双青色缎靴停在他的身前,他抬起头来,眼中有火色缭绕,“夏侯相爷,老夫看错你了!”本以为这次可以扳倒霍凤,原来,还是一场空!
夏侯逸微笑,“柳尚书,做人该识时务才是。”
“当初明明是你……”
“尚书在说什么,夏侯完全听不明白。”
柳泉眼中陡寒,寒光凌冽似要将夏侯逸分尸!夏侯逸不以为意的笑着,极为有礼的颌首,离开。
这条毒蛇!如果霍凤是猛兽,那这个人就是毒蛇,为什么他会相信这条毒蛇!
悔恨老泪纵横,他知道了!这原本就是一局棋,而他就是那个被牺牲的小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