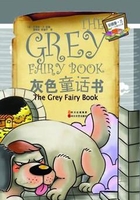抗战胜利后,萧军于1946年9月23日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哈尔滨。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从此萧军便被排斥出文艺界,被湮没了整整三十年。萧军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中写出《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以及《第三代》最后部分,《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近作》等重要著作。萧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这些作品,思想更见深沉,艺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但保存了宝贵的文学史料,而且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艺术珍品。特别是后两部作品,名为“注释”,其实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品。
习武1917年,十岁的萧军随做生意的父亲到长春,当时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甚嚣尘上,有志之士都以刺死伊藤博文的朝鲜志士安重根为榜样,修文习武。萧军经父亲同意,拜了江湖侠士山西人段金贵为师。从此,他就开始了昼习文夜习武的少年时代。
1926年,19岁的他到吉林北山当兵。当时,北山聚集了一批武士文人,作为文职兵,他有机会同这些江湖义士弹琴赋诗,练拳舞剑。在这里,他因路见不平,也出过几次手。由于他的剑术出众,演京剧《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的演员秦小舫拜他为师,学习舞剑。1927年,他考入沈阳宪兵训练处,在这八个月的学业中,他学习了格斗—柔道—日本劈刺和侦察技能。之后,他被分配到哈尔滨当宪兵。虽然只干了几个月,但他对欺凌民众的兵痞,污辱妇女的警察,抢劫钱财的贼盗,都施展了他的武功,打了几次漂亮的仗,战无不胜。此年,他考入了沈阳的东北讲武堂。在此学习期间,他开始用不同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第四学期将毕业时,发生一场动武事件。起因是,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中校教官朱世勤,无理鞭打一位同学,萧军气愤之下,以行意拳为同学挡开鞭子。朱世勤翻过来就打萧军,并且拔出佩刀,萧军拾取一把铁锨,格开佩刀,泰山压顶,照朱的头顶劈去。由于众多同学拉架,才没劈死后来当了汉奸的朱世勤。但是,萧军因此挨了军棍,不给毕业证书。他就这样离开了讲武堂。由于他的武功声望,辽宁昌图县的一个陆军旅,便聘请他去当了武术教官。
1931年“九一八”后日寇占领东北,他在沈阳结识了著名武师辛健侯,两人共伸爱国情怀,切磋武功,使他的武功更臻精熟。这时他已精通长拳,花拳,行意拳,八卦拳,太极拳和各路刀剑,还有日本的柔道和劈刺。不久他和辛健侯先后到了哈尔滨。
他在哈尔滨与萧红同居后,以写作为生,有时仍和辛健侯练武。在当地他结识一位白俄拳师后,又迷上了西方拳击。以后,他走青岛,奔上海,逃武汉,赴西安,涉兰州,到成都。两次投奔延安,一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坚持练武。就是在解放后了无声息的许多年间,北京的一些武师与他还有来往。
(89)逝情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原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她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当地有名的官僚绅士,不仅对佃户奴仆很残暴,对萧红也十分严厉。家庭环境和冷漠的亲子关系使萧红从小就养成叛逆的个性。1931年,专横的父亲逼着萧红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汪殿甲(王恩甲)。萧红断然拒绝,和封建家庭决裂,逃出了父亲的控制。
她逃婚出走至北平,考入女师大附中,未婚夫汪殿甲尾随而至,两人因经济困窘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同居。1932年,汪殿甲以回家取钱为由,将怀孕中的萧红抛弃,险些被旅馆老板卖到妓院以抵还六百多元的食宿费。孤苦无助、重病缠身的她向报社投书求助,报社主编裴馨园收到信后非常同情这个不相识的女读者,便派萧军到旅馆探望。萧军按照信上所示的地址找到了萧红。萧军这时看到的萧红是一个憔悴的孕妇,脸色苍白,神态疲惫,穿了一件已经变灰了的蓝长衫,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
萧红对萧军的到来,非常惊喜,更没有料到来看望她的人正是她所佩服的作家三郎。萧红读过萧军以三郎笔名发表的诗歌和小说。萧军当时头发蓬乱、衣着褴褛,活似个流浪汉,然而,却散发着豪爽的英气,萧红不由产生信赖和亲切的感觉。年轻的萧红在那狐鬼满路的茫茫人海里,终于遇到一个知音,便打开心扉,把自己的悲惨身世,不幸遭遇,难言的屈辱,痛苦的心情,对爱和美的渴望与追求,尽情地倾诉出来。萧军在萧红的床上,发现了散落的纸片上画着图案式的花纹,虽是胡乱勾勒的,但线条洗练流畅,显示出勾勒者非凡的艺术才情。接着萧军又看到纸片上有几节字迹秀丽工整的短诗,萧军被震动了!他感到无比的惊异,眼前的是一个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他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这个灵魂!但是萧军心有余而力不足,适巧松花江决了堤,遂得以趁乱从旅社救出萧红。萧军与萧红在患难中结为夫妻,两人在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同居。萧军送给妻子的礼品,不是什么珠宝首饰,而是比珠宝更珍贵的三首定情诗,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
萧军与萧红结合的六年,是他们各自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六年,是他们出成果最多、最艰苦也最快乐的六年,也是打打吵吵的六年。
萧红确实如萧军所说,“自尊心过强,有时膨胀到病态的地步。非常敏感。她有消极的一面,生活意志很弱”等等,这是她的性格问题,萧红生来一副多愁多病身,她不是伟人,无力自控,但她对萧军是真正投入了感情的。1938年,他们来到设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工作,萧军总是闹着要上前线抗日,要去打游击;萧红则认为抗日应各尽所能,我们的特长是写作,应当用笔为抗日呐喊。两人各执一词,不欢而散。正是这一次争吵,让萧红下定了与萧军分手的决心。
萧军也尽了自己的努力。他一直跟着萧红,不想分手,但又忍不住不吵不闹。最后,萧军只得默默接受这一切。他在兰州遇上了贤淑温良的王德芬,并与之恋爱结婚,这一次婚姻延续了半个世纪,直到萧军逝世。萧红与萧军的同居关系维持了六年(1932—1938),正式分手时,萧红已经怀孕,那孩子后来不久夭亡。1939年(一说为1938年),萧红另与端木蕻良结婚,婚姻关系维持了四年,直到她病逝于香港。萧红临终前还想起萧军,念叨道:“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情书
致萧红
吟:
前后两信均收到了。你把弄堂的号码写错了,那是二五六,而你却写了二五七,虽然错了也收到。
今晨鹿地夫妇来过,为了我们校正文章。那篇文章我已写好,约有六千字的数目,昨夜他翻好四分之三的样子,明晨我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已搬到环龙路来)再校一次,就可以寄出了。其中关于女作者方面,我只提到您和白朗。
秀珂很好,他每天到我这里来一次,坐的工夫也不小,他对什么全感到很浓重的兴趣,这现象很好。江西,我已经不想要他去了,将来他也许仍留在上海或去北平。寄来过一次,你的第一封信她已看过了。今天在电车上碰到了她、明、还有老太太,她们一同去兆丰公园了,因为老太太几天要去汉口。
三十日的晚饭是吃在虹他们家里,有老唐、金、白薇(她最近要来北平治病了,问你的地址,我说我还不知道)。吃的春饼。在我进门的时候,虹紧紧握了我的手,大约这就是表示和解!直到十二时,我才归来。
踏着和福履里路并行的北面那条路,我唱着走回来。天微落着雨。
昨夜,我是唱着归来,
——孤独地踏着小雨的大街。
一遍,一遍,又一遍,……
全是那一个曲调:
“我心残缺……
我是要哭的!……”
可是夜深了,怕惊扰了别人,
所以还是唱着归来:
“我心残缺!……”
我不怨爱过我的人儿薄幸,
却自怨自己痴情!
吟,这是我做的诗,你只当“诗”看好了,不要生气,也不要动情。
在送你归来的夜间,途中和珂还吃了一点排骨面。回来在日记册上我写下面几句话:
“这是夜间的一时十分。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那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
吟,你接到这封信,不要惦记我,此时我已经安宁多了。不过过去这几天是艰难地忍受过来了!于今我已经懂得了接受痛苦,处理它,消灭它,……。酒不再喝了(胃有点不好,鼻子烧破了)。在我的小床边虽然排着一列小酒瓶,其中两个瓶里还有酒,但是我已不再动它们。我为什么要毁灭我自己呢?我用这一点对抗那酒的诱惑!
偶尔我也吸一两支烟。
周处既找不到,就不必找了。既然有洁吾,他总会帮助你一切的,这使我更安心些。好好安心创作罢,不要焦急。我必须按着我预定的时日离开上海的。因为我一走,珂更显得孤单了。你走后的第二天早晨,就有一个日本同志来寻你,还有一个男人(由日本新回来的,东北人)系由乐写来的介绍信,地址是我们楼下姓段的说的。现在知道我地址的人,大约不少了,但是也由它去罢。
《日本评论》(五月号)载有关于我的一段文章,你可以到日本书局翻看翻看(小田岳夫作)。
花盆你走后是每天浇水的,可是最近忘了两天,它就憔悴了,今天我又浇了它,现在是放在门边的小柜上晒太阳。小屋是没什么好想的,不过,人一离开,就觉得什么全珍贵了。
我有时也到鹿地处坐坐,许那里也去坐坐,也看看电影,再过两天,我将计划工作了。
夏天我们还是到青岛去。
有工夫也给奇和珂写点信,省得他们失望。
今天是星期日,好容易雨不落了,出来太阳了。
你要想知道的全写出来了。这封信原拟用航空寄出,因为今天星期,还是平寄罢。
祝你获得点新的快乐!
你的小狗熊
五月二日
(注:此信系萧军于1937年5月2日所写,当时萧军在上海,萧红在北平。)
(90)师谊1934年夏,萧军与萧红在好友舒群的安排下,到了青岛,住在舒群岳父家。萧军担任了《青岛晨报》副刊的主编,但他的主要任务是抓紧《八月的乡村》的写作,而在青岛最大的收获是在地下党员孙乐文的帮助下,与鲁迅取得联系。在青岛待了不到半年,两人迫不及待地到了上海。
鲁迅是他们心中的希望和明灯。如果能见上鲁迅,那此行所有的悲苦辛酸都值。他们只好继续给鲁迅写信。鲁迅的回信总如期而至,但谈及见面,不禁让人凉了半截,先生的意思是“从缓”。鲁迅被当局通缉数年,当时环境之恶劣与现实之残酷,让先生不得不谨慎万分。但鲁迅对人生地不熟的二萧又十分牵念,怕他们病急乱投医,再三提醒“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他真诚地说:“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
出乎鲁迅意料的是,他在复信中称呼萧红为“女士”,遭到她的不满与抗议。更出乎二萧意料的是,这一因过于敏感而炮制的抗议竟然博得了鲁迅的好感,他似乎看到了这对年轻人身上温润如玉的天真,他认为,他出来保护这对年轻人身上的美好东西责无旁贷。他们再通信就像老朋友一样俏皮嬉戏,而见面的机缘也已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