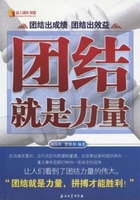诗是卖不上价的。有家杂志向朱湘索稿,他答应了,但要求四元一行。结果,那位索稿的编辑就不要他的诗了。有的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长期不寄稿费,他也不催,更别说上门去讨了,倒头来只能是自己吃亏生闷气。失业的生活很不安定,心境也因此很差,为了生计又不得不写,写了又无处发表,积下了数种诗稿,放在妻子的身边,找不到出处,只能被束之高阁。
在失业的一年多时间里,朱湘一直在京沪两地间奔波,希望能谋到一份固定的职业,杭州、天津、武汉等地有他的同学和同事,他也去了。
1932年的秋天,朱湘来到武汉谋职,住在汉口码头旁边一家三等小客栈里,已是身无分文。他每天除了吃两碗面,便只拥着一床薄薄的毡子蒙头睡觉。饭吃不饱,又付不掉房钱,走不成,住不得,真比死还难受。走投无路之际,朱湘想到了他在安徽大学的同事苏雪林,她已从安大调到武汉大学,他便向她伸出了求助之手。手心向上借钱,对任何爱面子的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尤其是对一向自视很高的诗人朱湘来说,更是令他感到羞耻的事。他在信中借口途中被窃,旅费无着,请求通融数十元。信发出后,朱湘仿佛盼救星似的,屡屡问茶房有没有武大的人来找他。苏雪林接信后到旅馆一看,朱湘的容貌憔悴,服饰邋遢,她真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当年在安大趾高气扬的诗人。毕竟同事一场,苏雪林没有计较朱湘当初对她的不恭,如数付给他所需的路费。
第二年的10月,朱湘仍然没有找到工作,他再一次来到武汉,又去武汉大学拜访了苏雪林,以求能找到一点让他担任的功课。武汉大学的教授由教授委员会聘请,私人引荐没有多大用,再说当时也不是更换教授的时节,所以,朱湘的希望是无望的。
其实,朱湘有清华同学在武大任职,还有一个哥哥在武汉做官,若求他们,兴许可以解救他于危难之中。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直不去求他们帮忙,而只是去找帮不了他大忙的女士苏雪林。这可能是他不愿让官场上的得意之人看到他的落难而因此更加得意。他以为,求苏雪林这样的文人,有一个“文”字相通,可以获得同情和理解。朱湘的这种心境,在他给他的留美同学时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柳无忌的信中,有过真实的坦露:
在这个各大学已经都开学了,上课了许久的时候,才来托你,不用你说,我还有不知道是太迟了之理么?……我能不能教书,我们也同学过两年,你无有不知道的。现在才来托你,自然是嫌迟;我不过是对于我自己尽一分的人事罢了。能否有位置,有钟点,学校方面肯否找我去教,这些,不用你说,我也毫无把握;不过,既然生了,又并不是一个不能做事的人,也就总得要试一试。若是一条路也没有,那时候,也便可以问心无愧了。
无故的,忽然向了你说出这一些感伤的话,未免太煞风景;你也是一个文人,想来或者不会嫌我饶舌。就此停下……倘若,不论有指望没有,你能给我一个回信,那是我所极为盼望的。
类似这样的信,朱湘连连地寄给他的同学和同事,但都无下文。
1933年10月6日,朱湘由北平南下路过天津,特意到南开去看望柳无忌。两个老同学自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分别以后,五年没有见过面,虽有书来信往,略知各自的近况,但一见面,柳无忌仍然为朱湘的精神状态吃了一惊。柳无忌留朱湘吃了一顿午饭,下午在英文系为他安排了一场演讲,四十多位同学济济一堂,出于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大家对他的演讲报以极大的热情。朱湘讲的是中国新诗的派别、趋向及其成就,热情洋溢地朗诵了好几首个人的诗作,又当场回答了同学们诸多关于诗学问题的提问,产生了极好的效果,给南开英文系的学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南开的这次演讲,是朱湘在失业之后过得最愉快的一个下午,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发挥他的才华。他是多么渴望重返大学讲坛,把他的学识奉献于中国的教育,把他在诗歌艺术上探索多年的收获奉献于中国的文学,然而,偌大的中国,竟没有他的一席生存之地,失业的痛苦正在一步步地把他逼向绝境。
朱湘的求职心情之切,那是外人所难以体验到的。求不到职,饥饿每天都在威胁着朱湘。他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为了糊口,就接连地把妻子寄给他的棉袍、皮袍送进当铺,他已经连御寒的衣服也没有了。柳无忌找同事给朱湘凑了一点路费,朱湘由天津抵达南京,然后乘船去上海,钱又花光了。他搭上了船,却没有钱买船票,挨到上海以后,茶房不许他下船。他好说歹说,茶房才同意他把行李押在船上,跟他一齐上岸找钱来赎。朱湘带着茶房来到赵景深家里借钱,这才摆脱了一场无地自容的尴尬。天气实在太冷,走出赵家,朱湘冻得受不了,又折回头去向赵景深借了五元,买了一件棉袍。
一次次扑空,一次次失望,朱湘被失业的包袱压得透不出气来,他的精神渐渐接近崩溃的边缘。
情殇朱湘三岁那年,母亲因病离开了他;十一岁那年,父亲也跟着离开人世。他是由哥哥养大的,却因为彼此年纪相差太大有些隔阂。可想而知,他的童年该是多么的孤寂,更别谈凡人享有的慈母父爱了。后来,他便开始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渐渐在当地文坛有了些名气。这时,一位女子的出现,搅乱了朱湘平静的读书生活。她便是两年后成了朱湘妻子的刘霓君。
其实,他俩是由双方家长指腹为婚的,按理没有感情基础可言。从懂事起,朱湘便极力想摆脱这场包办婚姻。父亲去世后,他才在去清华上学的空当躲过了这次“劫难”。在北京,大哥前来探望他。兄弟两人就一阵客套的寒暄起来,突然发现了站在角落里的刘霓君。刘霓君大胆地望着朱湘,叙说着她在报纸上读到的朱湘的诗歌,言语中流露出崇拜和爱意,但是朱湘打断了她的话。因为,她已惹怒了他。
朱湘断然离去,只留下旅馆里的刘霓君,独自伤心哭泣。回到学校后的朱湘把摆脱这桩包办婚姻的希望,寄托在了赴美留学上,他认为,离家远了,时间长了,刘家便会自行解约。但就在这个时候,清华学堂里贴出了开除朱湘的布告,而此时距离留美仅剩半年的时间。他因为抵制学校早点名制度长达27次,受到这一处分,也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离开清华,朱湘来到上海,不久,在大哥的口中得知刘霓君也来到了上海。大哥告诉朱湘,刘霓君的父亲不久前去世,兄长独占了家产,她只能一个人跑到上海来找工作,希望自己能养活自己。这个信息激发了朱湘的同情心,他觉得不管婚事成与否,去看望一下刘霓君,也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3年冬日的一天,整个浦东在外滩西式建筑群的映衬下,显得破旧衰败。朱湘穿过由几间旧房构成的厂区,来到了离厂房不远的一排工棚区,这是纱厂的洗衣房。一看刘霓君在这个洗衣房洗衣,还有低矮的厂房和各种气体冒出来,他的心理开始发生变化。两人见面,却是长久的沉默。最后,刘霓君冷淡地对朱湘说了声:谢谢你来看我。但朱湘却一个劲地摇头,她只好慢慢转过身去,低着头走回了洗衣房,消失在白腾腾的雾气里。
这一刻,朱湘在与刘霓君的婚姻问题上,开始动摇了。黄浦江的江水在寒风中静静地流淌,朱湘向刘霓君表示,愿意接受这份由旧式婚姻演变而来的爱情,他在安慰刘霓君后,快步拉着她离开纱厂宿舍,并决定与对方结婚。从厌恶到同情,从同情到相爱,朱湘的情感世界发生了彻底地逆转,以至于爱到至深。然而,这场戏剧式的婚姻,在若干年之后,因为生活的贫困而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折。
结婚后第二年,朱湘留学美国,但因为无法忍受外国人对自己的歧视,频频转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
在这期间,朱湘给妻子刘霓君写了100多封情意绵绵的书信,寄托自己的异国相思之苦。留学生活进入第三年后,因为经济拮据,他未能完成学业,在1929年8月回国,回国后担任安徽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但不久后因为学校经费的问题被迫辞职。这时候,朱湘与刘霓君生下了两人的第三个孩子,取名再沅。由于失业,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因为小儿子的夭折,刘霓君开始怨恨丈夫的无能,夫妻关系逐渐恶化。之后朱湘开始辗转漂泊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由于性情孤傲,得罪了不少人,谋职四处碰壁,只能依靠写诗卖文为生,可最后,连诗稿的发表都越来越困难。到了1933年的冬天,朱湘穷困到只剩一堆书籍和自己亲手写下的诗稿。
刘霓君见朱湘整日守着诗稿无事可做,便托朋友帮他找了一份工厂里的临时工作,但遭到了朱湘的拒绝。只会写诗作文的朱湘,因为把诗歌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因而与曾经患难与共的妻子之间,矛盾越来越深。
从此,朱湘步入他生命中的最为凄惨的最后一段岁月。
从安庆到朱湘的老家太湖百草林只有百十公里路程,他的四哥朱文庚少时从湖南回老家,继承了全部家产祖业,拥有数千亩良田,靠雇工收租过着小康的日子,生活相当安逸。在安大辞职以后,朱湘完全可以把太太刘霓君和孩子送回老家,靠四哥的帮助暂时过渡一下。这样,他可以从容地再去谋职,即可减轻许多压力,也可省去很多烦恼。然而,虽是同胞兄弟,他也不肯回去吃“嗟来之食”,而是把太太送回了湖南长沙的娘家。
作为孩子的父亲和妻子的丈夫,朱湘很不称职,严格地说,他不配享用这两个名分。他最最钟爱的是诗,而诗给他带来的则是贫穷,从结婚到当教授,他都没有给太太和孩子创造任何幸福,并且很少想到他们的饥寒温饱。相反,太太和孩子却因他受尽了人间的磨难。
留美之前,朱湘和霓君有一次生气吵嘴,他失手打了她,她被逼无奈回了娘家。他还好,连忙赔礼,哀求她原谅,绝对是真诚的。到美国以后,他在信中向太太解释了他发脾气的原因:“我受了外面的气,负了一屁股的债,又要筹款留学。”霓君原谅了他,带着孩子在国内,无依无靠,四处漂流,时而寄居在她妹妹的婆家,时而在尼姑庵中借宿,娘儿们忍饥受寒供朱湘读书。
其实,朱湘对霓君是怀着满腔的深情的,他曾很动情地写信向她表白:“回国以后,我要作一个一百分好的丈夫,要做一个一百分好的父亲。”后来,他在美国写给霓君的情书编为《海外寄霓君》,书中充满了对家庭对朋友的爱,也充满了对国家对人类的爱。怎奈他无力摆脱经济的重压,因为经济,他提前回国了;回国以后,他在经济上并没有翻身,因而也就无法兑现他向霓君的承诺。
在安徽大学教书期间,霓君因事需回娘家几日,把儿女们托付给朱湘照管。他最小的儿子大病了一场刚好,又才断奶不几天,朱湘每日强迫他吃香蕉一枚,吃不下也要填鸭式地填下去,结果,这个婴儿因消化不良夭折了。这件事给霓君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朱湘因一时义气,自己砸掉了自己的饭碗,彻底断了经济来源。失业后,他为了尽快谋个职业,南北奔走,四处漂流,今儿北京,明儿上海,行踪不定。家里入不敷出,老债未清,又添新债,他沦落到穷愁潦倒的地步,对妻小更是无力无暇顾及。霓君有苦无处诉,寄居在娘家忍气吞声,靠帮人做粗活维持她和孩子的生活。
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的清苦导致了家庭的不幸,谋职无望,家境凄惨,朱湘和霓君的感情已面临严重的危机,离婚的话题无可避免地被提上了家庭的议事日程。
朱湘在求职的路上接连碰壁,及至绝望之时,他终于“明白”过来了:是诗歌和文章误了他的前程,害了他和他的太太孩子。
“以前我是每天二十四点钟之内都在想着作诗,生活里的各种复杂的变化,我简直是一点也没有去理会;如今,总算是已经结清了总账。”(《致柳无忌信》)
朱湘所要结清的“总账”,就是要与写诗和作文彻底决裂。在与柳无忌分手之际,朱湘一再叮嘱他的老同学,叫他转告他们的另外两个同学罗念生和罗皑岚,劝他们不要专写文章。这不是一时的赌气,而是痛苦的醒悟,因为他坚信:做文章误了他的一生!
朱湘清醒地意识到,不能适应环境是他的致命弱点,他甚至对自己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认为他的生活只是一个失败,一个笑话,“我真是一个畸零的人,既不曾作成一个书呆子,又不能作为一个懂世故的人。(《我的童年》)”当诗人感到自己不能超越现实,而现实又令他痛苦不堪之时,他便认定,选择自杀这条路,是最好的解脱了。
1933年12月5日,在由上海开往南京的吉和轮上,朱湘倚着船舷,取出随身携带的酒瓶,一边饮酒,一边吟诵着海涅的诗。轮船行至马鞍山李白投江的采石矶下,朱湘纵身一跳,跃入长江,只溅起一圈凌乱的浪花,便被汹涌的江流吞没……船主从朱湘遗在船上的一口皮箱和夹袍内发现了他的名片,还有他太太的地址,当即给他的家里写了一封信。于是,刘霓君在第三天接到了丈夫的噩耗,诗人投江自杀的新闻旋即登上了京沪等地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