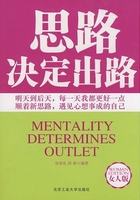(47)感铭周作人的《“沉沦”》一文,发表在1922年3月的《晨报·副镌》上。文章说理通透,立场明确,一些对《沉沦》噪噪嚷嚷的声音,才渐渐消散开去。郁达夫是一个“摩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李初梨语,见郭沫若《论郁达夫》)。对现实人生,他又是充满感念心情的。对周作人为自己写辨正文章这件事,郁达夫几乎终生未忘。周作人后来回忆说:“但是达夫似乎永不忘记那回事,有一年他在世界书局刊行《达夫代表作》(仿佛是这个名称,因为这书已送给一个爱好达夫著作的同乡,连出版的书店也记不清了),寄给我的一本,在第一页题词上提到那回事情,这实在使我很是惶恐了。”
对于这事,周作人确实没记清楚。郁达夫题词的,应当是原由上海春野书店出版的《达夫代表作》,此书后来转在现代书局出版时,在扉页上题了这样一句:“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献辞的发表时间是1930年元月。可其实在更早的文字里,郁达夫就表达过这样的感激之情。1927年,郁达夫在为自己《鸡肋集》题词中,有这么一段话:“在这一年的秋后,《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这《沉沦》的诲淫冤罪,大约可以免去了……”像这样一再表达的谢词,可以看出郁达夫感铭的程度。
因了这样一种文人间的援手,郁达夫与周作人之间,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据周作人日记,他们的初次见面当为1923年2月11日。几天后的2月17日,周作人宴请郁达夫等友人。这次宴会,鲁迅也出席了,这应该是郁达夫与他的第一次见面。由此他们两人也建立了长久而真挚的友谊。
郁达夫后来表示,要为鲁迅的《呐喊》和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写评论文章,文章虽然没有写出,可却与周作人鲁迅兄弟,保持了长久的亲密友谊。在郁达夫,对周氏兄弟,不仅仅只是人事,对他们的文章,也是由衷敬佩,甚至推为当代作家之首的。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要编辑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来全面反映中国新文学最初十年的业绩(1917—1927)。周作人与郁达夫,受邀编辑其中的散文部分。据郁达夫介绍,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茅盾等名家文章,归他择选。结果呢?其他名家,每人多不过五六篇,少的仅一篇,可鲁迅,一下子选了24篇,周作人更惊人,选了56篇。这两兄弟文章加起来,占了全书“十之六七”。郁达夫对周氏兄弟文章的珍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样选择,当然得说得出理由。在郁达夫看去,这理由太充分了。在书前的“导言”中,郁达夫这样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于古雅遒劲的一途了。”郁达夫甚至这样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
(48)轶事郁达夫还有一个外国名字,叫James Daff Yowen(詹姆斯·达夫·郁文),这个笔名的由来是这样的。1919年秋,达夫应长兄之召回国参加外交官及高等文官考试,他在北京时很想能见见当时鼓吹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胡适,就给胡适写了一封求见信,信上說:“万一你不见我的时候,恐怕与我的dignity(尊严)有些关系,所以我现在不能把我的姓名同我的学籍告知你。”信尾他写了这个英文名字。
1921年,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尾崎在演讲中将中国称作“清国”,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突然,一位青年站起来,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回忆此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刘开渠学成回国一年多,从来没有人请他塑像。郁达夫对刘很是理解和同情,积极为他奔波,刘终于接到了第一笔订单——为一商人的亡母作浮雕肖像。郁达夫还在肖像背后为其撰文。
郁达夫带着侄女郁风到护城河边溜达,看见一个车夫溺水而亡,其妻在一旁痛哭。郁达夫坐过那位车夫的车,很是同情,想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钱给车夫的妻子,但身上却无分文,只有一个银表。他趁着车夫的妻子不注意时,将银表偷偷塞进她的小兜里。
黎锦明回忆:“达夫天性仁爱,对一切不幸的人和生活,时常怀着极深厚的怜恤。”1926年,郁达夫与黎锦明从浦东码头乘船去广州,二人将行李运上船后,见有时间,便上岸浏览一番。他们在街上路遇两群瞎子少年相互厮打,东西摔得满地都是,有的人被抓伤了头皮,鲜血直流。郁慌忙跑上去,拉开他们,出言呵斥闹事之人,将地上摔破的东西捡起来,又掏出几角钱给受伤的少年,安慰他们说:“买点药,回家好好的养伤。你们真奇怪,为什么这样不互相合作,你们都是弱小的人!……”将他们遣散后,郁达夫还独自伤感地苦笑着。
1929年8间,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版税,准备请律师进行诉讼。北新书店的李小峰忙请郁达夫居中调解。当时,郁正在杭州小住,接到李的电报后,立即返回上海。经过几次商谈交涉,鲁迅答应暂时不提出诉讼,而北新书局则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事情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郁达夫为此事前后花费了20天左右,还耽误了自己的写作。
郁达夫曾参加在林则徐故宅举办的一次“诗钟”。题目临场公布:有、无,二唱。郁很快提笔在纸上写道:“岂有文章惊海内,断无富贵逼人来。”第一个交了卷。此联上联取自杜甫诗,下联则为清龚定庵的诗。谁知却得了“状元”。主持人的评语是:“浑成自然,天衣无缝,裁对工整,无异己出,应冠全场。”
有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接着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命题。演讲和作文一样,也不可以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完了。”从在黑板上写那三个字到说完话,他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郁达夫对于金钱怀着厌恶和复仇心理。有一次郁达夫在饭店请客吃饭,结账的时候,郁达夫脱去皮鞋,从鞋底取出钞票付账,并诙谐地说:“这钞票,它以前压得我不舒坦,如今我也要践踏它,以出怨气!”在郁达夫的小说和日记里面,也多次出现类似的描写。
1936年在福州时,郁达夫有次领取薪水,回到家里后,就把钞票全部抛撒在地板上,来回践踏以泄愤。这被房东老太看做他是“神经病发作”。
郁达夫碰到不愉快的时候,往往会悄然无声地从家中出走一次,但不会走得很远。有一次王映霞受好奇心驱使悄悄跟踪他出门。他们在曾相携散步的路上一前一后走着。郁达夫偶尔回头发现了,马上喊了一辆人力车,叫车夫把车子拉到妻子身边先让她坐上去,自己后坐上去。到家后,郁达夫的气已消了。
郁达夫嗜酒如命,每顿必饮黄酒一斤,有时喝白兰地。他经常饮得酩酊大醉。有一天,他一夜未归,翌日黎明,只见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踉踉跄跄地踏进了客堂。原来,他昨夜酒又喝醉了,在冰天雪地过了一夜。于是,夫人王映霞“约法三章”,规定凡朋友请郁达夫出去喝酒吃饭,必定要负责送回,否则不让出门。起初尚有效,久而久之,夫人的约定便成为一纸空文。
殇谜1945年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却迎来了他的噩耗。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去了,衣服都未来得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所获取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却都找不到。
另外,关于郁达夫的失踪还有几种说法:
其一、可能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以后不利的话,便扼死了他。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此说缘于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证据来源者的姓名,其说成为孤证,因而颇受置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