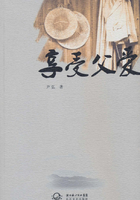“如此说来,你想让我做一个咨询侦探?”
“不仅如此,我需要你的指导,你见识广博,经验丰富,所以希望你能告诉我下一步我该如何走。”
说话时,他呼吸急促,声调颤抖,语句断断续续,仿佛他始终都在竭力压制着自己的感情。
他说:“没有哪一个人会愿意对外人说自己的家务事,尤其是与两个陌生人讨论自己妻子的行为。而更烦人的是我已到达毫无办法的地步,只好向别人求救了。”
福尔摩斯说道:“亲爱的格兰特?芒罗先生……”
来客猛地跳了起来,大声说道:“你是如何知道我的姓名的?”
福尔摩斯满面笑容地说:“要是今后你还想隐瞒自己的姓名身份,我劝你不要再把名字写在帽里儿上,或者当你再拜访别人的时候,别再把你的帽里儿冲着人家了。请你赶快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我吧。”
来客仿佛觉得很痛苦,他把手又放在了额上。突然,他像是下定决心不再保守秘密了,用紧握的拳头作了个坚定的手势,他说:“福尔摩斯先生,我结婚已有三年了。这段时间里,就像任何一对夫妻一样,我们生活美满,没有任何矛盾。可是自从上星期一开始,我发觉在生活上和思想上,我对她知道很少。我们的生活出现了阻碍,而我们也变得有些疏远了。事情就是这样,我实在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要先让你知道,艾菲是很爱我的,你不要有误会。你清楚,男人发现女人在爱他是很容易的,只是如今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个秘密,如果弄清的话,我们就能恢复关系了。”
福尔摩斯变得不耐烦了:“芒罗先生,请你赶快切入正题吧。”
“初次遇见艾菲的时候,她仅有二十五岁,她的前夫赫伯龙先生已经死了。从很小,她就定居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城了。在那里,她嫁给了一个成功的律师赫伯龙,并有了一个孩子。后来,她的丈夫和孩子双双死于黄热病。她回到米德尔塞克斯的平纳尔和她未婚的姑母一同居住。另外,她的前夫留下了四千五百镑的遗产,而且她能得到她丈夫在世时的投资年利七厘的利息。我们在相识几个月后就结婚了。
“我每年的七八百镑收入源于我做的蛇麻生意。在诺伯里,我们租了一幢年租金为80镑的小别墅,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在一定的季节里才进城办事。所以我们在住所里得以纵情欢乐,而且在此之前根本没有过任何的不愉快。
“另外,在结婚的时候,我妻子把她的资产都划到了我的名下。在她的一再坚持下,我就照她说的办了。大约六周前,她来找我说:‘杰克,你说过,我给你的那笔钱我在任何时候要都可以。’我说:‘那当然。’‘好,我要一百镑。’我十分惊讶,因为我感觉她只是想要一件新衣服或其它类似的东西。我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开玩笑地说:‘噢,你仅仅是做我的银行保管人的,这种人是根本不能乱问别人的。’
“我说:‘要是你要拿这些钱当然可以,但你一定需要它吗?’
“‘当然,我急需这笔钱。’
“‘能告诉我用途吗?’
“‘不行,过几天我才能告诉你。’
“尽管我也给了她一张支票,这却是我们夫妻间第一次产生秘密。
“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有一所小别墅,中间则是一块田野。只有沿着大道走到对面,再绕到一条小路上,才能到小别墅。一片茂密的苏格兰枞树就长在小别墅的另一边,平常我也常在那里散步。非常可惜的是八个月来这所小别墅一直没人住。而我就常在这二层小楼边徘徊,幻想能住在那里的舒适感觉。
“上星期一晚上,我走过去,想看看这个别墅到底租给了什么人。但同时,我突然发现上面的窗户里有一张脸也正在看着我。
“当时我似乎背上冒出了冷汗,尽管我当时没看清楚那张脸。惟一的印象就是那张脸有点儿不自然也不太像人脸,为了看清楚到底是谁,我赶快向前走去。而那张脸却突然消失了。我不能分辨出那是个男人还是女人,因为离我太远了,而我却深深地记住了那张面孔的颜色:白垩土般的青灰色与不自然以及吓人的僵硬呆板。我决定去看看这家新的住户。敲了敲门,一个体态瘦削而又极为高大的、面容丑陋的、令人生畏的女人为我开了门,接着,用北方口音问:‘你想干什么?’
“我朝着自己的房子点了点头,说:‘我就住在你们旁边,看看能否帮上你的忙。’
“‘需要的时候,自然会去找你的!’我就这样被打断,感到特别生气,转身就回家了。那天晚上,我只是在睡前告诉她那座小别墅里已住了人,但她却没有说话。
“通常,没有什么能吵醒我。可那晚,也许是那种事情的小小刺激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在我似睡非睡时,我感觉到我妻子已穿好了衣服,披上了斗笠,戴上了帽子,还在屋里不住的走动。而当烛光映在我妻子那张异常苍白的脸上时,我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因为她呼吸急促,在扣紧斗篷时,还偷偷地看着有没有惊醒我,接着悄悄地溜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我就听见了大门合页的响声。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看了看表,是凌晨三点钟,而这个时候,我妻子要干什么去呢?
“坐了大概二十分钟,我一直在寻找一些说得通的解释。就在我越想越感到古怪的时候,门又轻轻关上了,她又走上楼来。
“一见她,我就问:‘艾菲,你去哪儿了?’
“她大惊失色并猛地尖叫了一声,而在这一惊一叫中含着难以形容的内疚,这就更让我感到烦恼了。看着一个像我妻子这样的一个性情直爽而真诚的女人悄悄溜进屋里,我感到非常心寒。
“她勉强笑笑,大声说道:‘杰克,你醒了,我还想没有把你吵醒呢。’
“我更加严厉地问道:‘你去哪儿了?’
“她连忙说:‘我感到气闷就想去透透气,我要是在屋里,就一定要晕倒了,几分钟,我就彻底恢复了。’
“她那完全与平常不同的声音表明她说的都是假话。在我心中,充满了千百种恶意的猜测和怀疑。我感到,必须查明,要不,我是不会安宁的。但是我不想再听一次假话,所以也就没有问她什么。可是那夜,我是一直在猜来猜去,越想越糊涂。
“第二天,异常恼怒使我顾不得进城做生意了。我看出她早已六神无主,也晓得我不相信她的假话。所以吃早饭时,我们并没有说话。饭后,为了思考这个问题,我立即出去散步了。
“走到克里斯特尔宫后,过了一个小时,在一点钟左右我才回到诺伯里。在路过那座小别墅的时候,我停下望了望那些窗户,想看看能不能发现昨天的那张怪脸。而正在这时,我的妻子恰好从小别墅里走了出来,福尔摩斯先生,你能想象出我当时的惊奇吗?
“我看到她,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妻子看起来比我还激动。原本她还想再退回别墅里面,可是当她看到这样做于事无补的时候,就面色苍白地走了过来。
“她说道:‘杰克,你不是生我的气了吧,我是才过来看看能不能给新邻居帮帮忙的。’
“我说:‘那么说来,昨晚你也是来这儿了?’
“她喊道:‘你这是什么话?’
“‘我敢肯定昨晚你是来过这里,你是如何认识这些人的,又为什么要半夜三更跑来看他们?’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我大声喊道:‘你怎敢对我说这种假话?不行,我要进去弄个水落石出。’
“她激动得无法自已,气喘吁吁地说:‘不,杰克,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进去!’她的一股蛮力竟把我从门口猛地拉开了。
“她高声叫着:‘杰克,你别这样,过几天我保证就将全部都告诉你。’她紧紧地抓我挣脱开的手,疯狂地恳求着。
“她叫喊道:‘杰克,你就相信我这一次。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全部生活,相信我,杰克,你会后悔的。’
“她的绝望的话语与诚恳的态度阻止了我,我就这样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前。
“我说道:‘只要你答应我,我就相信你,你必须保证夜里不再出来,不再做让我不能理解的事情,但你也有权保守自己的秘密。要是你答应我再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我就保证把过去的一切不快都忘掉。’
“她十分宽慰地松了口气,高声说道:‘完全照你的意思办。走,咱们回家去吧,我就知道你会信任我的。’
“从那以后的两天,我妻子很守约定,而我也一直呆在家里。但在第三天,我可以保证,她阻止不住那股吸引力,又去了那里。
“回家时,我乘了两点四十而不是乘通常的三点三十分的火车。我推开家门,女仆面色惊慌地跑了过来。
“我问:‘太太到哪儿去了?’
“她答道:‘她……散步去了。’
“一下子,我忽然疑云四起。跑到楼上,我发现她的确没有在屋里,当我不经意向窗外一看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女仆,向小别墅的方向奔去。我马上就知道我妻子又去那里了,而且她还命令女仆为她通信儿。我奔下楼,冲了出去,气得浑身发抖。所以我没有敲门,转动门钮,直接冲了进去。
“厨房炉灶上的水壶不住地发出咝咝的响声,一只大黑猫盘卧在一只篮子里,楼下是一片寂静。屋里的家具和画除了那间从窗户看到怪脸的卧室讲究而舒适外,其他的都很平常而粗糙。而当我看见那张三个月前我为妻子拍摄的全身照片时,我全部的猜疑都变成强烈而痛苦的火焰了。
“在确定没有人之前,我又在室内呆了一会儿,然后怀着异常沉重的心情回到家里。我妻子来到前厅,而我非常恼怒,径直冲进书房中,而她却也随着我走了进来。
“她说:‘杰克,我破坏了诺言,我很抱歉,但我相信你知道了事实,就一定会原谅我的。’
“我说:‘那你就把全部都跟我说了吧!’
“她则高喊道:“不,杰克,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说:‘你如果不告诉我你送照片的那个人和那别墅里住的人是谁的话,我们就压根儿谈不上互相信任了。’后来她离开了家。我从那时起就再没有看见过她。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发生争执,我十分震惊,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今天一大早,我突然想到你可以给我指明方向,所以就匆匆赶来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切就拜托你了。”
这个人十分激动,时断时续地讲着。而福尔摩斯用手托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他说道:“你能确认从窗户里所看到的是一张男人的脸吗?”
“不能,由于我每次看到那张脸时,距离都很远。”
“很明显你对那张面孔印象不是太好。”
“那张脸呆板得奇怪,并且颜色似乎也很不自然。在我走近他的时候,就猛地不见了。”
“大约何时你妻子向你要那一百镑?”
“大概两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