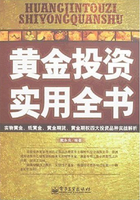更不幸的是,我隐隐发现她口中深深念叨着的那个人不是别人,竟是……慕容孤赫?
今日这一行撞到的内幕实在太多,震惊之下,我一时半会儿根本消化不完。
“就因为这些,所以你才不惜一切的想拉他下来,让北珩上位?”祁顺帝眉头紧锁,语气沉重。
“对,我就是不会让他好过!”楚贵妃直言不讳,话锋一转,突然问道,“皇上,难道皇位不该是北珩的么?当年若不是皇后那贱人使用拙劣的手段害死姐姐,她以为她还能替她儿子保住太子之位……”
“景妃……”祁顺帝嘴里轻轻呢喃着这个名字,满目苍凉,好似一瞬间老去了几岁,他斑白的两鬓已然成霜,眉眼深深中,沁满了对往事眷恋的深情。
“皇上,北珩是可是姐姐给你留下的唯一血脉啊,难道你忍心看着他一辈子被人欺压于脚下,每日活得战战兢兢吗?”楚贵妃动之以情,继续诱导道,“太子生性残暴,嗜杀成性,若有一日他继承帝位,岂会轻易放过北珩?北珩若是有个闪失,皇上又如何去酒泉之下面对我那一生悲苦的姐姐?”
“朕会在大去之前给北珩安排好往后的生活,远去西平,那里民风淳朴生活富饶,离得去争权夺利,朕也可告慰景妃在天之灵呐!”祁顺帝眉目一片平川,早已为慕容北珩铺好了退路,他的这番良苦用心,对一个帝王而言,已然难得。
“皇上真是好笑,退步那只是弱者的选择,北珩,乃至我楚家,从来都不是退缩的弱者!帝位,我们势在必得!”楚贵妃冷笑一声,满面豪气,“皇上,臣妾看您最好还是乖乖听话,废太子,立北珩,在您驾崩后臣妾也好送你去与姐姐团聚。”
祁顺帝微微侧目,脸上气色极差,隐有虚浮之感,却并不妥协,“不可能,朕虽然老了,身子骨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但心中却还是明净得很!这祁国的江山社稷,不是太子,谁都不能担起这个重担。”
“那皇上是在逼我们来硬的了?”楚贵妃见他不从,也并不恼怒,眸光微沉,令人猜不透其心中所想。
“朕现在已然一无所有,仅有的不过是一具残破的躯体罢了,这三年来朕反复想了想,祁国后继有人,死又何惧?”祁顺帝满面平静,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可能与他现在的生活,死了反而令他觉得是一种解脱。
“是吗?皇上不怕死,那北珩呢?也不怕他死吗?”楚贵妃悠然的张开五指,又将指头缓缓捏紧,“要取他性命,简直易如反掌。”
“你们……”祁顺帝被楚贵妃的话气得急火攻心,摊在椅子上手捂胸口一阵孟咳,他残破的身子本就今不如昔,现在又遭受到这种打击,他咳着咳着竟猛的呕出了一口鲜血。
“皇上,臣妾早说过了,你就乖乖立诏书吧,不要让臣妾不好做。”楚贵妃掏出手绢对着空气扇了扇,用丝绢捂住了鼻子,她恶嫌的瞥了祁顺帝一眼,“北珩是生是死,就全在你一念之间了。”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祁顺帝缓缓抬起脑袋,声音微弱似蚊,神情彷徨而凄伤,“他也是你的侄子,是你楚家人!”
“不,他不是!他姓什么?他姓慕容,是你和姐姐的孽种!”楚贵妃神情微微激动,声声全是对祁顺帝的控诉,“十八岁那年我身披红妆入宫为妃,强颜欢笑,去伺候一个与我父亲一般年纪的男人。自此,我便与我心爱之人成为名义上的母子,这一生,我注定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娶妻生子,与她人长相厮守,缠缠绵绵。”
“入宫之前,你应该将所有告知于朕,也许……”
“你以为我不想吗?以为我没有反抗过没有挣扎过吗?父亲命人关我,打我,用母亲的性命威胁我,要我为了家族利益牺牲自己,可又有谁真的了解我的心情?”
“泠容……”祁顺帝眼中隐有疼惜,像长辈对晚辈的,像父亲对女儿的,有温觅的光映在他憔悴的脸上,安定而平祥。他张了张嘴欲说些什么,可最终还是化为一声无奈的叹息。
“本以为他不会爱人,不是我,也轮不到其他人,那样,兴许我还能平静一点。可却突然来了个夏清璃,当我看见他对着那个女人笑,对这那个女人展露温柔,你们可知道,我为了那个笑等待了多少年?”
她对我的恨,原来深原于此。
“青衣白兰,太学殿外,我与他都还年少,父亲拉着我的手,指着从我身边经过一脸倨傲的少年,对我说,‘泠容,可想当未来的皇后?那便是你未来的夫君。’此一句,在我小小的心中便萌生了一个念头,那是我潜心藏匿的秘密,甜蜜又辛涩。我要嫁给他,并不是为了做皇后,而是做他的正妻。可是……”
“不要再说了,泠容,不要再说了!”祁顺帝再也听不下去,喘着粗气急声阻断,“是朕愧对你,也愧对了你的姐姐,咳咳……咳咳……可事已至此,早已无力挽回,你这样不仅不能……”
“别的不要,改立北珩为太子!”楚贵妃收起刚才的情伤,绝美的容颜上立刻附上了一层冰冷的寒霜,神色坚定,语气强硬,“若皇上真觉得对不起我,就废了慕容孤赫!”
祁顺帝没有出声,胸前因强烈的情绪波动而剧烈的一起一伏,他喘气艰难,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在忏悔赎罪与江山社稷上,他选择了后者。
“朕……没有办法答应你。”低缓的声音,微弱,却尽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