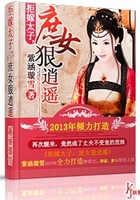“姑娘,老爷命我为你准备了一些路上用的食物和水。”老妇人撩起门帘,口中捧着一个麻袋,压低声音道。
我接过,道了声,“谢谢。”
她微笑着送我离开,临走前,我没有再见到董源生。
出了茅屋,我沿着蜿蜒崎岖的山道一路急走,暮色越来越重,黑沉沉的笼罩大地。月亮悄无声息的出来,没一会儿又躲进翻滚云层里。
我不敢放慢脚步,越走越急,走到现在几乎是连走带跑,心中的不安却在这种焦躁的情绪中却越来越强烈,脑中反反复复的回荡着临行前董源生说的那些话,突然灵光一闪,终于想到自己怪异在什么地方了!
他的声音……他的声音不就是西鹤群山密林里与漫云说话的那个老者的声音?
人说话的音调音色可以因自己某方面的刻意改变而有所不同,这也是导致我没有马上辨别出来的原因,但他说话的语气口吻却是怎么也没有办法改变的。
董源生,夏国的太傅,我的启蒙老师,我第一次开始疑问他究竟是什么人?
皓月当空,夜凉如水。
当我风尘仆仆的赶到小茅屋的前院时,四处静谧一片,宁静得几乎压抑,只听见微微夜风吹过的声音。茅屋内微弱的烛光随风摇曳,透过窗户洒出来,撩起一片蕴黄的光影。
我迟疑片刻,还是小心翼翼的潜了过去,踮起脚尖,透过窗户往屋子里看去,一盏橙黄的烛火旁,慕容北珩依然面色平静的躺在床上,睡得很深很沉。
难道,真是我多虑了?董太傅并不是故意支开我另有图谋?就在这时,远处一些细碎的声音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凝神静听,本来只是一块块碎片,但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那声音也逐渐明朗。
我听出来了,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在山路上回旋,但并不杂乱,而是很有章法,动里有静。从声音上不难辨别那些马行得极快,并且来人还不少。
马蹄声越来越近,这样大的异响也惊动了茅屋内的人,有低低的脚步声传来,我心念一动,一个闪身钻进窗户下的花丛里,探着脑袋向前望去,透过皎洁的月光,看见董源生从屋内提着一个灯笼走了出来。
他步子迈得极快,似乎很激动的样子,一直行到院前的小路上才停下来,将手中灯笼在半空中十分有规律的摇晃了几下,像是一种暗号。
难道真是他给人通风报信了?那来人会不会就是他的主子?也在找我的那个人?
一个一个疑问向我涌来,我没有时间一一去细想,当务之急,必须先带着慕容北珩离开再说,慕容北珩是祁国的王爷,落在他们手里多半是凶多吉少的。
思及此,我悄悄从窗户翻进屋里去,几步踱到床榻前,背起慕容北珩就欲开溜,我觉得自己简直被磨砺得有当女飞侠的潜质。背后那身体忽然动了动,紧接着一个温温的声音传来,“放本王下来,本王自己能走。”
我一惊,压低声音问道,“你醒了?”
他声音极轻,微微喘着气,“虽然一直昏迷,但神志尚很清醒,那个人已知道了本王的身份。”
“啊?”怎么会?我至始至终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啊!
“他拿走了本王身上的玉佩。”
我释然的点了点头,“我们快些离开,他好像给什么人通风报信了。”
我心中有些担忧,“你可还能走?”
他没回我,而是一把抱起我,‘嗖’的一下从窗户飞了出去。
呃,这家伙!
我们出了茅屋,从偏侧的花地疾奔,月光不足以让我们看清前方的路,只能凭着直觉乱跑,冷风刮面,把我原本就乱的头发吹得更乱,却怎么也比不上我此刻心中的乱。
正门前,几十个火把聚集,火光在夜风中张牙舞爪的摆动,将方圆几百米照得透亮,马儿繁重的踏地声嘶鸣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
忽的,有人发现了我们,“主子,他逃了。”
“拿箭来。”一个温雅的声音在夜里漾起,清幽幽的飘进我耳里,似一江婉丽的春水,细细流淌。这个声音,似有些熟悉。只是当时只顾于逃命的我,根本来不及多想。
下一刻,‘飕,飕,飕!’三支箭矢划破长空,气势猛烈绝然,直冲我们而来。慕容北珩失了八成功力又拖着我,根本难以身形灵活的躲闪。三支利箭带着惊人的速度从背后呼啸而来,那一刻,我几乎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然而变故却往往发生在瞬息之间,三支急速呼啸的箭矢,在距我们十米远的距离突然改变方向,其中两支偏得犹未厉害,那闪烁着寒芒的银箭带着凌厉的戾气擦过慕容北珩的手臂。血顿时涌了出来,染红白色的衣裳。而剩下的一支则狠狠扎进他左肩,鲜血飞溅而出。
看得出来,那射箭之人若想取我二人性命简直易如反掌,他下手留有余地,是因为不想慕容北珩死,而只是想活捉他。
想明白这一点,我大胆建议,“襄王,你一个人先离开,他们的目标是你不是我,再说董源生好歹是我夏国的太傅,他不会对我怎样的。”只有扔下我这个包袱,他方才有一线生机。
“说什么傻话,本王怎会弃你于不顾。”他很义气的更搂紧了我,心性执着得不行,“要生一起生,要死一同死。”
我真想对他说,大爷,您逞英雄也得分时候不是?再说了,谁要跟你一起生一起死了?你也没问问我这个当事人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