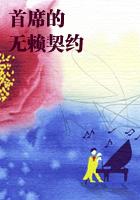“狗哥,你一定得挺住呀,胖子我救你来了。”
胖子强挺着身体的疼痛从大树的主干爬了上去,死死地拽住了狗哥缠在麻袋中的一只脚,瘦狗死命的挣扎着,乱抓乱划,胖子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抓住了他的另一只脚。
瘦狗的伤势很重,两条腿都骨折了,到底折成了多少段,就不得而知了。胖子心疼他,小心地把他扛在肩上,朝山腰上的滴水洞走去。
胖子到洞里取出了一堆木炭,红红的火苗在洞口的空地上燃烧起来。瘦狗明明知道十万两银子不在了,可还是挣扎着要自己亲自到洞里去看看。
“我说狗哥耶,钱没了可以再赚,保重身体要紧。”胖子忙扶着他躺在一堆干净的稻草上,“哥,你想吃什么,我到洞里去给你取。”
瘦狗微微地喘息着,“我要喝酒。”
胖子大感为难,山洞里只有简单的食品,只够三天吃的,狗哥是知道的。可是明知道没酒,他却要酒喝,胖子的心里一酸,怕狗哥是不行了。口中只得答应着,安慰他说,
“雨停了我就想法子弄去,狗哥你的伤不碍事吧?”胖子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银子没有挣到,身体上下又锥心地疼痛,泪水一流下来,就再也忍耐不住。
瘦狗被他这么一哭,心里也像刀绞似的难受,翻来覆去地说着,“好胖子别哭了,哥不要喝酒啦。”
北玄兰桂舫!
一楼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四个男人正默不做声的喝着酒。靠外边两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正是大内一等侍卫日蚀和月蚀。靠里边窗户坐着的,是画家甲和画家乙。
“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另外的那二十幅画没在我们两个手里,都在我那个该死的外甥手里……”画家甲有些急了。
“少废话,再啰嗦我就捅了你!”日蚀动了动桌子底下手中的短刀,悄声说道。
鹿鸣坐在二楼的栏杆旁,正密切地注视着一楼的动静。他很想知道,来和两个画家接头的,到底是什么人?两个老家伙真的是贪财不要命了,居然作了四十幅画,还分头许了两个婆家。
一楼的大门口有一个人已经来回地走了两趟了,引起了鹿鸣的注意。那是个又矮又胖的猥琐汉子,长得活像个大肉团。此人手短足短,没有脖子,一个头大得的出奇,一个酒糟鼻子又圆又大,像一只熟透了的红柿子,脚上趿拉着皮鞋。
鹿鸣感到情况有点不妙,除了酒糟鼻外,还有两三个汉子很像官府的衙役穿着便衣。今天带着两个画家来付约的目的,鹿鸣主要是想知道到底是谁导演的这场陷害皇上的闹剧?必须把主谋除掉。
两个画家手里并没有画,画家甲一口咬定画在他外甥手里。鹿鸣也不关心画在哪里了,只有把主谋抓住,那画还有意义吗?
不对了,门口可疑的人越来越多了,如果只是交易两幅画,用得着来这么多的人吗?不能再耽搁了,鹿鸣给楼下的日蚀和月蚀发了信号,一直不停地往楼上张望的月蚀马上会意。
按原计划是把两个画家带到楼上再干掉的,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十名衙役已经涌了进来,两名官员全身的公服。箫丞相不准备和这两个画家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派了手下想把他们两个直接的捉拿回去,扔到大牢里去,不信他们敢不画!还敢要银子?
日蚀和月蚀一人捂住一个画家的嘴,干净利索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只一瞬间的功夫,两个画家就像沉重的麻袋躺靠在座椅上了。
又有十多个衙役手持着铁棒单刀,手里的铁链抖得哗啦啦地乱响,乱遭遭的有人喊道,“官府有令,兰桂戒严,从现在开始,只许进,不许出,苍蝇也不许飞出去一只。”
一名衙役走到那个官员身边,“报告,有两个人刚刚被刺死在座位上!”
鹿鸣带着日蚀和月蚀已经进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从阳台上向后院望去,只见后院火光闪耀,官兵们已经点燃了火把,把后院照得有如白昼,很显然,兰桂舫已经被包围了。
老鸨叶小梅和两名官员周旋着,没想到这兰桂舫今晚比市场还乱,最关键是死了两个人呀,这要是说不清楚,生意就得关门了。
“哎呀呀,我的爷呀,这两个死鬼一定是得罪了什么人了,来我们兰桂舫的可都是良民呀。”
也没人听她啰嗦,又一帮有十多名,一看就是雇佣的街上泼皮,抡着棍,使着棒,从外面冲进来了。不一会儿,就把一楼的酒肆,茶座,各种瓷器,砸了个稀巴烂。
众兵丁在院子里齐声喊,“捉拿刺客,莫让这些反贼逃跑了!”
兵丁们已经在二楼的走廊里大声地喊叫了,皮鞋踢踏声,铁链哗啦声,吵嚷声响做一片。三个人简单地交流了一下,当务之极是要活着突围出去。两个画家已死,那流散在外边的二十幅图也就成了绝版。不知道瘦狗和胖子死了没有,无论谁活着出去了,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胖子和瘦狗,把剩余的二十幅图收回来。
就听到咚咚的踢门声,“大胆刺客,反贼,你们被包围了!”
“日蚀,月蚀,你们两个从屋顶先走,我来引开这些狗日的!”鹿鸣命令道。
日蚀和月蚀欲张口辩驳,被鹿鸣那刀子般的目光制止住了。日蚀和月蚀轻轻地跳到了阳台的阴影处,顺着滴水管爬到了三楼的屋檐上。
鹿鸣打开门,探出半个身子,“什么事这般吵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