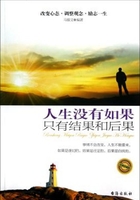白末眉目展笑,莫论真心还是假意,已经矮身半寸,行过见礼。
苏夏一步向前,望向宋楚的目光和暖。落到白末的肩上了,那一点黑钻此刻唯美意境,光色灼灼。
“真是对不住妹妹,刚刚不小心将你的衣服扯破。这钻石可是番王的?与这衣服倒也十分相衬。”
宋楚一下黑了脸,拉过白末只看不语。好像她有未完全交待的罪行,此刻正深深的刺激着他。
苏正龙一挑眉宇,兴趣盎然:“怎么回事?又如何与番王扯上关系了。”
苏夏最先笑着应声:“是我疏忽大意,下马车时不小心滑了下来。扯开了妹妹肩上的结。皇兄匆匆招见,没帮上忙。这钻石在子倾的袖口上有见到,猜想是他帮了妹妹。”
宋楚听得倒认真,只差一副耳朵就要支棱起来。明面虽是笑着,那股忍气吞声的劲在白末看来,还不如当即发泄出来。咬紧了薄唇,俊脸上出现一种恨亟灭世的冰凌之色。唇丝一线,懒懒道:“白末,你不傻,是我宋楚傻了。”
白末咬着唇干笑,深知宋楚这次的醋吃大发了。这对兄妹绝对是故意的,某些人既然用心良苦,百不应承就显得不上道了。生气的扳过他的脸,说:“宋楚,你又犯什么病了?找茬是吧?不是都与你说了么?”
宋楚拿开她的手,没什么表情:“说什么了?傻瓜啊,怎么能一点防备都没有?”
尘子倾不知何时蹭过,一脸温软绵绵的笑意。此刻御花园里掌满了灯,一张脸就隐在这片迷离四溢的灯海里,神情似笑非笑:“光天化日的,我尘子倾能把你宣王爷的四夫人怎么样?”
宋楚说:“得了,也不是认识一两天了,你什么人我宋楚还不知道?”
尘子倾心中感叹起来,是啊,别人看不通透他尘子倾,可是他宋楚却读得一清二楚。多年的朋友又岂是白做的。只怕再过很久,在他尘子倾面前,宋楚才真正的想要把她藏起来,一辈子再不见除他之外的任何男子。
苏夏心中一梗,一点眼风与苏正龙相接,眼前的一切即刻心领神会。
苏正龙被苏夏面上的那点僵硬刺伤,滑过一丝疼惜。君主该有的庄重也是一分不少:“行了,大家还是入座吧。王爷也别见怪了,番王也是一片好心。”身子率先一转,已经朝主位走去。
宋楚与尘子倾面面相觑,均伸出一侧手臂由请。白末和苏夏紧随其后,苏夏脸上的笑意永远如初,仿似无论事世怎么变迁,这笑都要一层不变一样。白末倒觉得一种情绪维持僵化太久,就不免职业化了。
这种宴会在白末看来与现代的宴会也没有多少区别,只是菜色稍显华丽一些。苏正龙摆出国君威武的样子讲两句,端起酒杯敬过众臣子。节目就已开始,丝竹之乐响意绵绵,映衬着周遭泛起的淡红光晕,这种气氛俨然用心打造过的。白末倒觉得十分引人入睡。
转首看向宋楚,一侧灯光打到他的侧脸上,神色少有的几分宁静。执着手中的杯子闲适的转动着,一举一动渗出优雅气息。只是眸子隐在一片暗影中,看不到其中光色。
苏夏坐在宋楚另一边,看他安静太久,侧首轻声唤他:“王爷……王爷……”
宋楚一转头:“何事?”
苏夏笑笑:“以为你睡着了?”样子有几分亲昵。
白末见两人矮声交谈,便转过头不看他。端起桌上的酒盏,漫不经心的抿压,心里奈何竟有些不是滋味。
眼前的舞并不好看,一群着了薄纱的女子手拿蒲扇,卖力的摆动腰肢,肩上松垮的衣服似要掉下。或许男人偏爱这一口,时有赞扬声传出。视线一偏移,越过人群,正与尘子倾目光相撞,那双眸子亦在看她,嘴角微扬,喜滋滋的冲着她敬酒。白末略一颌首,一杯酒便也如数下肚了。再斟满一杯,只待端起,就被宋楚伸过来的大掌一把按住。
他板了脸教训:“说你不懂事你还真来劲。”
白末侧首,对上苏夏含情如许的眸子,积压了一天的不爽涌现出来,心口一堵,拔开宋楚的手,一昂首,下去了。
宋楚真急了,紧绷着脸,一把将她的手按到桌下,紧紧握在掌心攥了攥:“过份了啊。”
白末暗中与他脚劲,执拗着不肯抬头看他。鼻子微酸,他的手此刻越用力,她便越觉得委屈。
苏夏盯着两人的一举一动,摆出善解人意的样子偏着脸去仔细解释:“妹妹怎么了?还为今天的事不高兴么?衣服的事当真不是故意的。”
白末扯了嘴角忽然觉得好笑,一个迷糊不清的王爷,一个永远玲珑心志的王妃,这一出是唱给谁看呢?她觉得没意思,特别没意思。再抬头笑容轻松,眉目一转,何其曼妙何其妖娆了:“王妃想多了,这点小事我怎么会放在心上呢。都是王爷的女人,谁还能治谁于尴尬境地不成。”那句‘王爷的女人’故意被她执了重色,听得宋楚眉目陡然凌厉起来。
这个小女人果然不是在生苏夏的气,她是生他宋楚的气呢。气他宋楚女人泛滥呢!
苏夏不像不识时务,更像刻意为之。看似心安的叹息:“还好番王替妹妹弄好了衣服,否则真若出了麻烦,便觉得对不起妹妹了。”
宋楚转过头盯紧她,女人的小心思他宋楚如何不懂。一双眸子映着光色泛起冰冷之色,似要将她接下的话峰扼杀殆尽。
偏偏白末的犟脾气上来了,顺招接过,是以立刻回她嫣然一笑:“是啊,要不是王妃一下疏忽,我也没有机会与番王那样俊逸的男子近距离接触。男子手巧成那样的还真是头一回见,花色比我这个女人打得还好。品味也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