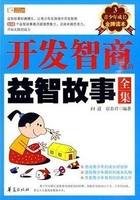浣熊正在一个小水塘里戏水,用那人手一样的小爪子摸索着什么。余下的时间,巴特都在和草翅膀,还有浣熊一起玩耍。他帮草翅膀清扫了松鼠住的箱子,给一只脚破了的红鸟做了一个笼子。卡西姆兄弟们喂的那群鸡,简直就和他们一样不服管教。母鸡在森林里到处下蛋。灌木丛中,荆棘堆里,到处都是鸡蛋。倘若这些鸡蛋不及时收起,就会变成蛇的美餐。巴特跟草翅膀一起去找鸡蛋,一只母鸡正在抱窝,草翅膀将他们收集来的鸡蛋全部放到了母鸡的肚子下面,一共十五个。
“这只母鸡是个好妈妈,她很会保护小鸡。”草翅膀对这儿的一切都很熟悉,似乎这里都由他管理。
巴特也渴望能拥有一样属于自己的宠物,草翅膀说把那只狐鼠送给他,巴特他相信,如果他要那只浣熊,也会如愿,可他不能。他有这样的经验,不能养一只好吃懒做的宠物,否则妈妈会生气。他看到草翅膀正在和母鸡说话:“好好待在窝里,知道吗?要听话,把所有的蛋都变成小鸡,这次要黄黄的、很可爱的那种,知道吗?黑的一个也不要!你如果答应我,我就每天给你送好吃的。”
他们转身向屋里走去,浣熊唧唧地叫着来迎接他们,它先是爬上草翅膀那弯曲的腿,接着爬上他的背,找了个地方舒服地蜷缩着,两只小手还搂着他的脖子,它用洁白的小牙齿咬住皮肤,假装凶恶地晃着自己的脑袋。草翅膀很是享受。他让巴特将浣熊带到屋子里去。起先,浣熊对巴特很警觉,它用一种探寻的目光打量了巴特好久,才终于接受了巴特的爱抚。
卡西姆兄弟们已经到垦地干活去了,他们有的赶牛去饮水,有的在喂马,还有两个消失在密林中。巴特猜测他们或许是去打猎了。他们人那么多,人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可做。巴特想到了自己,他几乎承包了自家垦地的所有事情,又想起了自己那没锄完的玉米地,他知道爸爸会一丝不苟地将它们弄好。想到这儿,巴特感到很惭愧,因为他将本该自己做的事情丢给了爸爸。
卡西姆爸爸和妈妈还在摇椅里熟睡。太阳已经由金色变成了红色,并慢慢落下去,黑暗很快降临到卡西姆家的茅屋上。卡西姆兄弟们陆续进入屋子,草翅膀在炉子上升起火来,去煮中午剩下的咖啡。巴特看见卡西姆妈妈睁开一只眼睛,随即又闭上。她的儿子们喧闹着将一些冷的食物放到餐桌上。她坐起来,捅了捅身边熟睡的卡西姆爸爸,一起共进晚餐。这回他们将食物吃了个精光,连盘子都舔干净了,草翅膀找不到东西喂狗,只能将一盘冷玉米面包和一些已经凝固的酸奶搅拌在一起,给那些狗送去。他因为提着重物,走起路来更加歪斜,巴特连忙赶过去帮他。
晚饭后,卡西姆兄弟们抽着烟,聊起天来。他们讨论着从这儿至西部乡村的牲口贩子们都在抱怨货源短缺。因为很多小马驹都被狼、豹和熊吃掉了,那些经常从很远的肯塔基赶着马群来的马贩子现在也不来了。他们商量着,如果能到北面与西面去贩马驹,肯定稳赚。巴特和草翅膀对他们的谈话不感兴趣,他们到一个角落里玩儿起了“拔钉子”①游戏。在家里巴特是绝对不允许玩儿这种游戏的,妈妈不会同意他将小刀插入平滑的地板中去。可在这儿就不同了,弄出一些碎木片也没人会在意。
“我知道一件事,我敢打赌你绝不知道。”正在做游戏的巴特忽然坐起来说。
“什么事?”草翅膀很好奇。
“那些西班牙人以前经常从我家门前的山林里经过。”
“哦,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呢,”草翅膀说,“原来是这个啊,我知道,我还见过他们呢。”
“你都看见什么了?”巴特紧盯着草翅膀问。
“当然是那些西班牙人了。他们又高又黑,带着闪亮的头盔,骑着乌黑的大马。”
“你肯定是看错了,那绝对不是他们。”巴特说,“爸爸告诉我,那些西班牙人早就离开了,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上哪儿去了。”
草翅膀聪明地闭上了眼睛。
“那肯定是你爸爸记错了,下次你到凹穴的西面去,注意木兰树的后面,总是有一个西班牙人骑马经过那儿呢!”
巴特知道,这又是草翅膀编的一个故事。草翅膀经常会编出稀奇古怪的故事来,他的爸爸和妈妈总说草翅膀是疯子。巴特明知道那故事是假的,可还是不由得寒毛直竖。同时他还很相信草翅膀的话,因为他确信,注意一下木兰树的后面总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睡觉时间到了,卡西姆兄弟们伸伸懒腰,将烟袋里的烟灰抖出来,然后走进卧室,解开吊带裤,松下裤子,将自己高大的身躯直接扔到了床上。每个人都有一张床,因为不论是哪一张床都禁不住他们两人同睡。草翅膀将巴特领到了自己的床边,他的房间在厨房旁边。
“这个枕头给你!”草翅膀将自己手里的东西递给巴特。
巴特接过去,然后看着草翅膀不怎么利索地脱衣服。他突然想起来,他们好像还没洗脚就跑来睡觉了,而卡西姆妈妈居然一点儿责怪的意思都没有。巴特心想,卡西姆兄弟们还真是幸福啊!不洗脚就可以上床睡觉,多自由啊,如果在家的话,估计又要被妈妈拧耳朵了。他们滚到床上去,草翅膀开始讲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冗长的故事。刚开始,巴特津津有味地听着,后来草翅膀偏题了,越说越不靠谱,巴特觉得没意思,就睡着了。睡梦中,他见到了西班牙人,他们并不像草翅膀说的那样,骑着很高的马,他们都在空中腾云驾雾。
迷糊中,他听到茅屋里传出喧闹声。巴特醒了,他以为卡西姆兄弟又在打架了,可后来才发现那声音是在召集众人,巴特还听到卡西姆妈妈加油鼓劲的动静。一扇门“砰”地被打开,好几只狗被唤了进来,一道光线从门缝照射进来,紧接着,小屋的门被打开,狗和人一窝蜂涌进来。男人们都光着身子,可能起得太匆忙,没来得及穿衣服。他们看起来瘦了些,不显得庞大了,但依然很高,都快顶到小屋的房顶了。卡西姆妈妈拿着一只点燃的蜡烛,蚱蜢一样瘦长的身体裹在一件灰色的法兰绒睡衣里。那些狗进来之后迅速冲到了床下,可是嗅了半天毫无收获,又匆匆出去了。于是大队人马也跟着狗走了出去。巴特和草翅膀目瞪口呆,他们不明白出了什么事,眼睁睁地看着这帮人在屋子里闹腾一番之后又离开。两个孩子连忙爬起来,飞速穿好衣服,去追大部队。他们两个跟在队尾,队伍经过一间间房子,那些狗在每间房子里都狂嗅一通。最后,狗们发狂似的从一个被撕破了的纱窗中钻了出去。
“它们会追上它的,它跑不了多远。”卡西姆妈妈平静地说,“这只该死的野猫!”
“妈妈的耳朵听野猫是最灵敏的。”草翅膀非常骄傲地说。
这时巴特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大半夜起来。
“那倒不是,那些野猫都快抓到我的床杆了,哪能听不见呢!”卡西姆妈妈听到草翅膀的话之后说。她说得很谦虚,可巴特还是在她的脸上看到得意的神情。
卡西姆爸爸见那些狗追出去了,拄着拐杖蹒跚地回到了屋子里。
“今晚算是被毁了,”他说,“现在我宁愿坐下来喝威士忌,也不愿意去睡觉了。”
“说的是呢!”鲍勃说,“爸,你对老鹫牌威士忌的感觉最灵敏了。”说完他走到食柜旁,拿出带着柳条筐的酒坛,递给爸爸,老人拔开酒坛塞,仰头喝了起来。
“爸爸,您悠着点,别喝醉了,这酒很烈。”鲍勃说着从父亲手中拿过酒坛,猛灌了一大口,又把坛子递给其他人。他用力在嘴边抹了几下,走到墙边,摸到了他的小提琴,漫不经心地拨弄了几下琴弦,然后开始胡乱弹起了曲子。
“你拉的什么曲子啊?”琼斯取来自己的吉他,坐在了鲍勃旁。
卡西姆妈妈进了屋子,她将手里的蜡烛放到桌上:“你们难道准备光着身子坐到天亮吗?”
鲍勃和琼斯沉醉在他们的合奏中,没有理会她。汉斯见他俩拉得起劲,也取出口琴吹了起来,他吹的是另外的曲子,鲍勃和琼斯听了一下,也加入到他的旋律中。
“真好听啊。”卡西姆爸爸又灌了一口酒说道。
那酒坛又传递了一圈。派克拿来了他的犹太竖琴①,密尔惠尔拿来了他的鼓,汉斯将他的哀怨曲调换成了一支活泼的舞曲。霎时间,懒洋洋的音乐忽而转为雄壮的合奏。巴特和草翅膀坐在地板上,夹在鲍勃和琼斯中间。
卡西姆妈妈看着儿子们:“你们不要觉得现在没什么事了,我就会上床睡觉。”她把已经封住的灶火捅开,往里扔了一些松脂,火很快旺起来。她将咖啡壶移进了炉里。“你们这些呜呜叫的猫头鹰,很快就可以吃今天的早餐了。别以为我什么也不会,我可是非常懂得怎样才能……”她看着巴特眨了眨眼睛,“一石二鸟,既能愉快地玩儿,还能把活干完。”
巴特也向卡西姆妈妈回眨了一下,他未曾有过这般经历,他感到震撼和愉悦,只是有些不明白,这群人明明这么轻松、这么快乐,为什么卡西姆妈妈会对他们感到不满?
音乐渐渐不成调了,但却有它独特的韵味,起码让人情绪激昂。音乐使巴特震撼了,好像他也变成了一把小提琴,而鲍勃长长的手指正挥弓擦过他的胸膛。
“唉,要是这地方只有我和我的爱人在歌舞那该有多好啊!”鲍勃低声对他说。
“那么,你的爱人是谁呢?”巴特有些莽撞地问。
“我的罗琳!”鲍勃的回答充满爱意。
“可她明明是保罗的女朋友啊!”巴特惊讶地说。
“你说什么?”鲍勃举起自己手中的小提琴,巴特吓得闭上了眼睛。他以为鲍勃要打他,想像中的疼痛并未落到他身上,他偷偷睁开眼睛,发现鲍勃又继续拉小提琴了,只是他的眼中冒着妒火。
“告诉你,小子,这辈子再让我听见你说一次这样的话,我就割了你的舌头!懂吗?”鲍勃恶狠狠地说。
“嗯!”巴特拼命地点头, “可能我说错了。”
“这还差不多。”鲍勃又重新回到他的音乐当中。巴特看着鲍勃,一时间,他觉得有些压抑,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保罗的事情,这种感觉稍纵即逝,因为他又被音乐所吸引。卡西姆兄弟们将舞曲变成了歌曲,所有人都来劲了,连卡西姆爸爸和妈妈,也用他们沙哑而苍老的声音加入了合唱。天亮了,模仿鸟①在栎树上唱出清脆响亮的歌曲。曙光已映进茅屋。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或许对于大食量的卡西姆兄弟而言,早餐似乎少一些。但他们不能抱怨,因为卡西姆妈妈准备这些东西已经忙活了好久。食物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男人们迅速吃完早饭,然后去洗脸,接着穿上衬衫和靴子去干活了。鲍勃给他那匹高大的花斑马装好马鞍,他骑了上去,又把巴特放到马屁股上。因为鲍勃的屁股实在是太大,即便马鞍很大,坐上去还是连插根鸡毛的地方都没有了,巴特只好坐到马屁股上。
草翅膀出来送行,他一瘸一拐地走着,浣熊挂在他的肩上,随着他走路的节奏一晃一晃。他挥舞着拐杖跟巴特道别,直到马消失在他的视线中。巴特一路上被颠得头昏脑胀,什么也顾不上想了,直到回到垦地。推开家门时,他才想起来,自己忘了注意木兰树后是否真有骑马经过的西班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