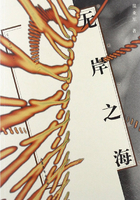扬州城内万花开,不输天下锦绣罗,只是眼下已经入了秋,零星开着的花平添了一份凄凉。扬州也是一座水做的城,捋一手的空气,里面满是水汽,柔柔的,宛如一个含羞的少女。
秋日很静,日子清闲着,人也懒了,繁华的街道此刻竟鲜有人行走,安静的很。
听到一阵“叮当叮当”的声音,本来很静的街道忽然间热闹了起来,一眼望去,远远的走过来两人两马,马脖子上的铃铛响得不停。
走在前头的是个女子,二十左右年华,一身红衣,笑靥如花,牵着一匹白马很是悠闲。跟在她后面的男子三十五六的岁数,灰色粗布麻衣,却有一种不敢轻视的气势,他牵的是一匹黑马。两匹马一白一黑,倒比它们的主人更能吸引别人的注意。
看到街上的人看稀奇般的看着他们二人,杜仲只当什么都没看到,他没准备这么招摇过市的进扬州城,可是云舒儿却很乐意这么做,还特意找来这一白一黑两匹马。云舒儿依旧笑得开心,一路走来,她还就这一刻最开心,不用过多时,估计人家都会知道有他们这么两个人进了扬州城。
云舒儿也不是有心玩乐才跑来扬州的,她本是在追查本门三圣物才来扬州的,正好在途中接到圣旨,说是让她去查上贡黄金被偷之事。既然已经在扬州城脚下了,再说扬州城还是可以和黄金搭上边的,一琢磨,她还是觉得应该进城。
牵马走在道上,云舒儿竟悠闲的哼起小曲,然后停在了一家客栈门口。杜仲见那里面已坐满人,便说再到前面看看。
云舒儿却不这么想,执意要进去,还说不进去就会后悔,杜仲无奈,只得听从。云舒儿遂将马交给马夫,径直走了进去,取出一锭银子放在柜台上,道:“给我两间上房,再送两壶酒,四样小菜过来!”
掌柜的见云舒儿如此大方,一出手就是一大锭银子,心中乐开了花,笑咪咪的领着云舒儿上楼。
不大的客栈经人巧手一布置,可以比得上京城里的大客栈了,在这样的地方呆着,实在是一件很舒心的事情。
布置精致的房中,云舒儿喝一口酒再吃几口小菜,速度不紧不慢。杜仲则是只管将酒往口中灌。云舒儿说杜仲是酒鬼,杜仲将酒往自个儿怀中一拉,一脸正经的说:“有本事你别喝!”云舒儿哪见过杜仲如此耍赖,伸手去抢,你来我往,倒不是真为了酒了。
这时外面忽然有了声响,杜仲停了手,抱着酒坛子,如风的身影闪出门去,一把剑顺势推近,杜仲一个转身擒住那人。那人“唉呦”一声叫的甚是凄惨,言语着让杜仲轻一点,杜仲怎会松懈,愣是将他提起带到云舒儿面前。
云舒儿仍在那儿慢悠悠的喝酒吃菜,顿了一会儿才饶有兴趣的问:“你的剑有他快么?”
那人怎见过这等阵势,早已吓得发抖,连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我的剑怎么会有杜大侠的快,小人也是情非得已,请云门主大人大量放了小的,小的以后做牛做马报答您!”这厮求饶倒是快得很,云舒儿知道他只是个小角色,抓到他也没什么用,可是他此行的目的云舒儿必须知道。
问了一遭,此人竟然装起傻来,说的话前后矛盾,却还理直气壮,气焰实在嚣张。
云舒儿见此人并无说出真相的诚意,不由得露出一副无奈的表情,“哎,看来你是真想见识一下杜仲的剑啊,好,杜仲,别辜负了人家一番诚意。”杜仲也做出要抽剑的动作,那人早已吓得两腿发软,连忙磕头求云舒儿饶命,云舒儿便让他将事情说出。
事情一说,云舒儿也是惊讶不已,竟是有人出一千两黄金买云舒儿的项上人头,有眼红黄金的人为了能杀掉云舒儿,就派些个探子先来探个底,估计他也料不到人会这么轻易的就被抓了。
云舒儿不免又要笑了,一千两黄金可不是小数目,自己的人头什么时候这么值钱了,而且这事儿还跟黄金沾边,说不定这幕后之人就是偷黄金的人呢。猜测归猜测,云舒儿只问到底是谁出的钱。出这么多的钱就为她云舒儿一颗人头,此人不是和自己有仇就是钱多了没处花。
可是这回那人竟然宁死都不愿再多说一字,云舒儿想了一遭,这些靠打探消息的人日子也不好过,若是泄露了雇主的秘密,这条命就不饱了,更有人因此使家人受到牵连,实在是不容易,如此一想,云舒儿竟不愿再为难于他。于是说道:“今日我且不为难你,你可以安全的离开,但若有下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那人一听,像是得到了特赦令,连连点头,连滚带爬的出去了。
经此一遭,杜仲更加觉得这个客栈不是个好选择,人多口杂,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准备来杀云舒儿的,便让云舒儿换一家客栈。云舒儿却不以为然,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安全,更何况就算是他们住到别处,有心人还是能找到他们的,既然如此麻烦,不如就呆此处。更何况探子可以这么轻易找到他们,说明这个客栈并非是看起来的这般简单,或许在这儿可以还可以得到什么对她有帮助的消息。更好的理由就是这儿的酒香菜香,何苦再去寻个住处。见杜仲还是一脸的担忧,云舒儿便提议出去走走,杜仲也不言语,只管跟上。
先前还懒洋洋的街道似乎在一瞬间舒展开了,叫卖声此起彼伏,这气势比之京城也绝不逊色,云舒儿心情也因为这样的景色而异常的好。走过一条街,云舒儿突然停了下来,问杜仲有没有听到琴音。
杜仲诧异,细听风中竟真有琴声。竟是用内力顺风而行的,这等内力着实厉害。
云舒儿提步道:“我们就先去会会这个弹琴之人。”
清风拂柳,轻絮慢摇,黑瓦白墙。
云舒儿也未曾想到扬州城内竟会有这样的独屋,不显突兀,倒如神来之笔点活一处风光。
“屋外的朋友为何不进来?”是女人的声音幽幽的传来,云舒儿感觉到了杀气,这并非是她刚才所听到的琴声,她心中思量着刚才的人为何离开了,对于屋内的提问并不作答,屋中的人急了,说是因为云舒儿不敢见她。
若论起这嘴上功夫,云舒儿是绝不会认输的,当下说道:“恐怕是你想见我,我想见的人却不是你,听得出姑娘是学过琴的,只是呀功夫还没到家。”
出乎意料的是屋内这下却没了反应,云舒儿便想去直接敲门,恰在此时一把长剑裹着疾风向云舒儿的方向而来。杜仲的剑已出鞘,却没有挥出的必要。似乎就在同一时间,一把飞刀轻巧的改变了剑的方向,“当”的一声钉在了柳树之上,剑插进了泥土中。回过神去,琴声已断,屋内也没了任何声响。
云舒儿拣起那把飞刀,仔细看了几下,便领着杜仲离开了。看来此番来扬州,要杀她的人还真不少,真不知还会冒出多少人出来。
他们已然回到街上,那把剑和飞刀都不是普通铁铺能做出来的,它们的主人也必然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现如今他们一无所知,只能做他们要做的,其他的事情便也只能顺其自然了,不过直觉告诉云舒儿她还会听到那琴声。
云舒儿回过头去吩咐杜仲让杜仲去查一下他们刚才所在的院子是何人所有,是否时有异常。杜仲离开之后,云舒儿也放慢了脚步,似乎在等什么,等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当然,她什么也么等到,悻悻然回到了客栈之中。
回到客栈时天已黑了,杜仲还未归,云舒儿倒不紧张,一觉睡到第二日,杜仲已站在门外。
云舒儿伸了个懒腰,似是漫不经心的问:“怎么样?”
“造房之人早都死了,这屋已经十几年没人住了,因为死过人,也没人敢拆。可是奇怪的是近几年每年的十月初八那儿都会传出琴声,这房子更显阴森了,所以一般人都不敢靠近。”
难道这是一间鬼屋不成?云舒儿不由得又多了几分兴趣,昨日可并非十月初八,那么又怎么会响起琴音呢?看来自己有必要再去一趟那里,说着,带着杜仲再次赶往昨日的地方。
仍是昨日的地点,却再无一丝风景。只有焦黑一片,突兀的告知着一切。杜仲不敢相信,就在昨晚他还看到这屋子好好的,现在竟然成了一片废墟,更让人惊讶的是住在四周的人都觉得这房子烧的好,说是神仙放了一味火烧死了这里的鬼,大伙儿的日子就平平安安了。
云舒儿叹气,若世间真有鬼神,她倒是会欣喜一番,只是她从不信鬼神之说,在这里弹琴的是人,今日烧了房子的也是人。鬼神亦斗,人心却难解,暗想这世间也不是什么事都能被她看透。这间屋子虽然已经成为了废墟,云舒儿却似乎可以透过它看到许多沧桑的故事。摇摇脑袋,云舒儿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她本是为了追查运送至京城的官银被盗之事才会来到扬州,没想到竟会站在这里为一间房子而伤感。正不知如何是好时,杜仲问她是否去诺风堡。
这下子云舒儿才知道自己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她竟未想到去见一见她的老朋友董成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