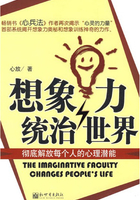“和你差不多,多丰满、多好呀!”医生的目光在她胸脯上扫来扫去,“好多人日思夜想要大一点,大一点才性感,才美啊!胸部小了,衣服都衬不起来,一点女性美都没有,有什么好?像你这样,比起港产片里的波霸小多了,算不上大,很不错的胸部嘛!”
“它……真的不大吗?”她怀疑地觑觑自己的胸脯。
“幸好我们是公家开的美容中心,要不,巴不得你送生意上门呢。你快走吧,别把自己的胸部糟蹋了!”医生挥了挥手。
“我不要它性感……”
她还想说几句,可医生不耐烦,钻进一间手术室里去了。她只好退了出来。
似乎知道了她的意图,两只胸部同时钝疼起来了。
她懵懵懂懂的,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她回到家,康有志已吃过饭,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前。
给她留的饭菜摆在桌上。
康有志说:“你怎么才回家呀?”
她不吭声,坐下来默默吃饭。凉拌海带像嚼稻草一样无滋无味。
康有志又说:“快吃完看节目吧,萨马兰奇要宣布结果,北京申奥成不成功就在此一举了!”
吃完饭,洗完澡,她坐下看了一会电视。但全没看进心里去,眼里只是花花绿绿的一片。屏幕上那个喧嚣的世界与她何干?它能让她的胸部不再隐疼吗?
她早早地躺到床上,蜷曲起身体。胸部还在作疼,在提醒她所遭受的羞辱。她不敢去碰它们。任何一种抚触,都是一种伤害和侵犯。廖组长锐利的目光仿佛还刺在里面,没有拔走。她一点不明白,男人们为何如此喜欢玩弄妇女的哺育器官,不就是两团肉么?
迷迷糊糊中,她听见窗外响起了鞭炮声,喧闹声。康有志在客厅里乱喊乱叫,接着跑进卧室,扳过她的身体:“成功了,北京申奥成功了!”
她本能地伸展了四肢。她了解丈夫,凡格外兴奋,或者格外沮丧的时候,他都要做那件事的。
果然,康有志的爪子抓住了她的胸部。她触电似的全身一麻,啪地一掌,将康有志的手打开了。
她叫道:“要来就来,不许抓这里!”
丈夫吭哧吭哧地动作时,她瞪大眼睛望着天花板,一滴豆大的泪像一只虫子,从她眼里爬了出来……
叶秋荻搭了公共汽车,去十几公里外的新农业示范园采访周雅琴。是市妇联介绍她去的,说周雅琴不仅是这个示范园的创办人,还是省妇联评出的全省十大女性创业明星之一。当记者多年,女劳模女先进之类见得多了,叶秋荻并不太感兴趣,但一听市妇联的人说,她是从性骚扰阴影中走出来的,就欣然前往了。
叶秋荻是在那个巨大的玻璃大棚里找到周雅琴的。她正在指导工人给那些奇形怪状的热带花木施肥。她一头短发,因常年受阳光照射的缘故,面庞微红,看上去非常健康,面容依然秀丽端庄,身材也相当健美,一身浅色的夏季薄工装,显得十分干练。给叶秋荻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周雅琴先脱了手套,洗过手,又用毛巾擦干,才和叶秋荻握手。
叶秋荻从这个细节看出,这个事业有成的女农艺师是个严谨、细致和讲究生活品质的人。
“欢迎你!”周雅琴矜持地一笑。
叶秋荻感受到了她矜持中的真诚,距离一下就接近了,也诚挚地笑道:“感谢你能够接受我的采访!”
“我是‘女性沙龙’的忠实读者,非常乐意和你这位主持人面对面交流,盼都盼不来呢,焉能不接受?”周雅琴一边微笑,一边打量叶秋荻的穿着打扮,赞美道:“到底是名记者,风度翩翩呵!”
来自同性的称道让叶秋荻十分受用,脸微微一红:“周大姐,您也气质不凡呀!”
“所以呀,就免不了受坏男人的骚扰,有些人对美好的事物天生就有破坏欲……哦,到我办公室去谈吧,对你来说,这儿的紫外线太强烈了。”
周雅琴领着叶秋荻走出大棚,朝一幢两层小楼走去。
“周大姐,上一期的‘女性沙龙’看过了?”叶秋荻问。
“看过了,而且看得很仔细。性骚扰这个话题你抓得很好,为女同胞做了件好事。”周雅琴顿了顿说,“过去报纸上有这种讨论就好了,我就不会那样痛苦了,至少有个说话的地方,有个排遗负面情绪的渠道。”
“其实来采访您,我是有顾虑的。您是个名人,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提及自己的遭遇和隐疼。毕竟,在别人看来,这是不光彩的一面。”叶秋荻说。
“我若不愿意,市妇联的同志就不会向你建议来采访我了。是我先有了这个意愿的。对女同胞有益的事,我非常乐意做。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我谁也不求,谁也不敢再骚扰我了——我的所谓名人的身份保护了我。我现在呼吸的是自由的空气!”
周雅琴回转身来,双手朝两边舒展,似要拥抱一下她所欣赏的空气,脸上神采飞扬。叶秋荻对她的精神状态羡慕不已,也回过身来。这时,她才发现走到了一个高坡上,整个示范园尽收眼底。青翠的山丘簇拥在四周,阳光在排列整齐的玻璃大棚上熠熠闪光。
“采访过我的记者不少,但他们大都关注我是如何创业的,投资多少,产值多少,利税多少,而很少探寻我的内心感受和心灵景象。他们似乎只在乎物质,而忽视精神。”周雅琴说。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这示范园不就是您精神追求的重要部分,不就是您心灵的外化吗?它是您精神价值的物质形式呀!”叶秋荻说。
“到底是名记者,说得真好!”周雅琴由衷地点头一笑,环视着示范园说,“说真的,它花费了我那么多心血,它也体现了我的自我价值。你知道,过去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不过是个臭气熏天的垃圾填埋场!”
“是吗?那它现在称得上是废墟上的花朵!”
“唔,废墟上的花朵,我喜欢这意象,很有诗意。”周雅琴两眼闪光。
“周大姐,您不像学农艺的,倒像是学文学的呢!嗯,报道您的文章题目,也就是它了!”叶秋荻说。
“好,闲话少说,我们现在赶紧为你的题目充实内容吧!”
周雅琴将叶秋荻领进办公室,打开空调,为她倒了杯茶,沉吟稍许,娓娓而谈:
“二十三岁那年,我从农学院毕业,分配到湖城市农业局工作……那时,大学毕业生还不多,女大学生就更少了,加上我年轻、漂亮,在农业局非常引人注目,不管我走到哪,都要吸引一大片目光……那时,我单纯得不得了,不以此为忧,反以此为喜,成天像只快乐的花蝴蝶飞来飞去。那是七十年代末,个人生活与单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光住房由公家分配,连床铺和桌椅都由单位发给,所以,我和管这个的行政科长有过几次交往。而这个人,就是我那一段痛苦生涯的起点。
这个人当时四十多岁,长得十分萎琐,一嘴的黄牙。自认识后,他就想方设法往我身边凑。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办公室,他就磨磨蹭蹭地过来,倚老卖老地把一只手抚在我头上,装出一副慈爱的样子说,小周姑娘工作很认真呵,不错,不错,值得表扬。我的头皮一阵发麻,赶紧将头一偏,躲开了他那只手。可是他立即搂住了我的肩膀,无耻地说,小周你身上的味道很香很好闻呵,你的衣服也比别人的漂亮。我挣扎着甩开他的手,可他另一只手迅速地在我胸部上抓了一下,我就像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我带着哭腔骂道:你流氓!他嘻皮笑脸,说你细皮嫩肉,真想吃你几口呢,你要是我老婆,我饭都不想吃了!我吓得心惊肉跳,赶紧跑出了办公室。
从此以后,我就有意躲着他,避免与他单独相处。有一年春节期间,不知是他做了手脚还是怎么回事,我和他被分派同值一个班。这一来,我连躲他的理由都没有了。一到值班室,他就往我身边凑,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周呀,要过年了,我要送你一样礼物,说着从包里掏出几个小塑料瓶来。你猜是什么?是几瓶洁尔阴!真是恶心死了!他是故意羞辱调戏我,我气得浑身直哆嗦,班也不敢值了,含着泪跑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