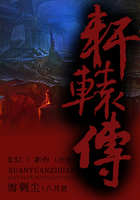告别苍雪的苍平,迅速奔向战场的方向,可是年仅十一岁的他跑起来,着实感到了力不从心,待到他爬上城头时,入眼的是大汜军惨败的景象
——城外的大汜军在做着殊死搏斗,但指挥台上早已没有活人,大汜军被长平军冲散开来,往往是百十来个长平军围住数十个大汜军,分块围歼。而城中的大汜军拼死护住快被冲破的大门,城头上的士兵们奋力放箭,阻止循着云梯杀上来的长平军……
而在城头上的苍平看来,这样没有阵势的乱攻,虽然有一时的效果,但当士兵们用尽力气的时候,也便是他们死亡的时候,现下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安全逃离?
“大王子!”同在城头的许杭看见苍平,迅速的收箭奔过来。
苍平似乎看到了希望,眼前一亮,停下吹箫的动作,说:“你有本事让我军安全撤出吗?”
“这样的情况,能保住一半就不错了。”许杭扫视战场。
“看样子,那些老将军早就带着父王撤离了,”苍平看着被长平军踩在脚下的王帐,“剩下的,只能靠我们了!”
“该怎么做?”许杭问。
“射死长平一个主将,让他们陷入短暂的慌乱,你趁机用指挥的小旗传达撤军的意思,”苍平看看手中竹箫,“我们就杀了那位‘廖老鬼’吧!”
“好。”许杭没有反驳的余地,这样的情况下,他说不出让几万大军送死,而让苍平一人离开的话,苍平也是不会答应的,“殿下,乱军之中,我们该如何做?”
“你瞄准廖风行三处要害齐射三箭,但他一定会闪躲过去,关键就在这第四箭。”苍平笑得坦然,“我会在你放出三支箭后,立刻放箭瞄准他的脑袋,他的武功招式和原将军的差不多,闪躲的路数也应该没什么区别。我们,赌的就是这个!”
“好!”许杭将从身后箭篓中取出四支三棱箭,递了一支给苍平。
苍平接过,踢开身边一具尸体,拿起一支染血的弓。两人趴在城头,瞄准下面指挥千军的廖风行。
“放!”苍平一声令下,许杭迅速的将三支羽箭送了出去。
再见,廖老鬼!
许杭松手放箭,三支羽箭越过厮杀中千军万马,直直的冲着廖风行去了。
杀气逼近,而廖风行似乎有些迟钝,低头闪过上面一支,左右两手开弓劈开两支,刚准备抬头,尾随而来的第四支箭从硬生生的斜插入了额前,贯穿了头部,疼痛感前所未有的真实。
——我就要死了……
廖风行倒下去的一霎那,眼前竟然出现了原铮牵着小师妹的手,正在冲他微笑,廖风行将手伸出去,然后,闭上了眼睛,倒在了马下。
“廖将军!廖将军!”
长平军陷入了意料之中的混乱,许杭迅速的传达了尽快摆脱纠缠,迅速撤军的意思,求生的本能在大汜军体内觉醒,纷纷开始趁着敌军的慌乱,脱离敌军的包围圈,很快,大部分人迅速集中在了苍平吹箫的城头下。
“大汜的男儿啊!长平指挥廖风行已被本殿射死!”年仅十一岁的苍平跃上城头帅座,挥弓高呼,稚嫩却又嘹亮的声音传遍军中,“进入城中,避免不了与长平军的一场近身肉搏,能活下来的,就能回家,不能活下来的,我希望你们洒尽你们最后一滴血!”
离城头较近的人听到声音,向城头看去,只见他们的王子高立在帅座上,手执弯弓,敌军将领突然消失在乱军之中,一股喜色漫上了沾满鲜血的脸:“大王子将‘廖老鬼’杀了!”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长平军闻之震惊悲切,六神无主,大汜军闻之喜上眉梢,趁机砍杀。
许杭突然爬上了城头,沙哑着嗓子大喊道:“活下来,活下来!回家,回家!”
——是,我们要活下来!我们要回家!
“看,公主!”突然军中又出现了一阵骚动,大汜众军像骚动处看去,竟是大汜公主一袭红衣出现在城中最高的六角塔上高歌。鲜红的衣裙与喷溅的热血交相辉映,刺激了将士们的感官。
“大漠连天,惶惶夕阳;遍体鳞伤,终是不忘……”
“策马奔腾,纵横疆场;你我所望,得还家乡……”
“月光苍凉,世末风光;鲜血流淌,挥剑张扬……”
“故国红墙,洗尽铅华;在等待,等待,归来荣光……”
苍平望着六角塔上的妹妹,将手中竹箫凑上嘴边,运气丹田,以内力吹奏,战场上飘起了悠扬的箫声,两处声音绵长在高空中流汇到一处,竟是如此的铿锵有力,响进了每个大汜士兵的心里。
顿时,群情激愤,失了首领的大汜军看见在两处以歌声与箫声遥相呼应的王子与公主,感觉突然有了灵魂,士气大振,刀上仿佛注入了神力,砍得越发的有劲了。
“各营长听令,迅速整编军队,听我的指挥,撤离!”许杭代替吹箫的苍平发号施令。
苍雪一曲毕,苍平也停下奏箫,和许杭说了声,我去找阿雪,便跃下了城头……
这一找,便是数年……
弘济二十五年,荒城街市,八月初八。
“快去看,快去看!”一个粗衣年轻人往街市口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喊,“云池馆的瑞雪搭台子跳舞了!”
粗衣年轻人的话似乎在闹市中放了一颗响雷,大家开始骚动起来,一个卖笔墨的小贩丢下了手头上的生意,刚想往街市口的方向跑,占个好位置,却被一人拉住:“这钱怎么算?”
“公子,今儿个您运气好,白送了,白送了!”那小贩忙着脱身,甩开拉住他的人,头也不回,连珠子般的蹦出这么几个字。
“哎,哎!”那绿衫书生喊不住他,只好罢手,将挑的笔墨包好,也向着人群涌动的地方走去。
大多数摊贩,不论男女,都放下了手上的东西,实在停不下的,也是不自禁的将头往那方向探探。那绿衫书生看着这些摊贩的神情,不由得对远处的表演产生了些兴趣。
绿衫书生走到那舞台附近时,舞台已经被围了里三层外三层,舞台周围的道路水泄不通。舞台后方一红衣女子赤纱掩面,坐在椅子上,而舞台前,那吆喝着来客的正是荒城云池馆的老鸨金妈妈。
“又是一年八月初八,咱们云池馆瑞雪姑娘搭台子跳舞的时候了!”金妈妈看着台下的人如潮涌,笑得都快合不拢嘴了,“这算来,咱们瑞雪这是第几次搭台子啦?”
“第五次!”台下围观的人都甚是激动,一个个脸上都笑得像开了花儿。
“弘济二十年第一次搭台子到今天,已经是第五次了!”金妈妈手绢一挥,伸出戴了两只宝石戒指的左手,“还多谢各位爷的赏脸,闲话不多说,咱们就请瑞雪姑娘为我们舞上一曲吧!”
“瑞雪!瑞雪!”台下的人越发的激动,呼喊着瑞雪的名字。
那坐在椅子上的瑞雪却不甚在意,只轻轻将桌上杯盏拿起,轻掀面纱,将茶水送入口中,任凭下面呼喊声愈烈。
“这位小哥,”那青衫书生拉住近旁的人,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您是外地人吧,”那人打量他两眼,“这瑞雪可是咱们荒城的宝啊,她的舞是荒城难得一见的美景,除了这每年八月初八搭台子表演可以看见,便只有去云池馆中才能瞧得!”
“哦,桓某今天赶得巧了,正是个八月初八。”青衫书生在人群中站定,抬头望向台中。
金妈妈看着台下的人喊了有一会儿,便挥手示意乐队奏乐,瑞雪放下杯子,走上前,轻轻弯腰施礼,台下霎时静了下来。
瑞雪赤色长裙,宽衣广袖,红色腰带紧紧缠在细腰上,更显得身材窈窕,一头长发被尽数束在头顶,挽成发髻,赤珠步摇左右对称,辅以银饰耳坠,整个人顾盼生姿。
乐曲刚起,两袖先右后左向左侧甩出,身体前躬弯腰,右手长袖刚点地便急速收回,身体由前躬转成侧弯,仅露出的美目扫视台下,左手也顺次收回,双脚灵活的变换交替,就这样弯着腰以长袖触地,由舞台的左侧转到了舞台右侧。
“好!”不知有谁率先鼓掌喊起,台下叫好声被带起,掌声一片。
面纱下的嘴嗤笑一声,美目更添风情,瑞雪将坠地右手长袖也收至后方,划出一条长红,双手在身后交叉相叠,双臂微使劲将长袖带到前面,却又在半途分至两边……
“不错,长袖善舞……”绿衫书生点头微笑。
——只是,这身影好熟悉啊!
绿衫书生蹙眉紧盯台上轻盈舞蹈的女子,希望能捕捉到一丝线索,因为他想到一种可能性。
北边天气风沙较多,女子舞动之时面纱难免会被掀起,绿衫书生试图在拥挤的人群中往前移几步,想将女子面目看清一些,但几次三番都没能上前一点,反而吃了别人不少白眼。忽地一阵风吹过,台上女子动作并未停止,那面纱也未被风掀起,只是更加紧紧的贴在了瑞雪的脸上。青衫书生眯起眼睛隐约见得真切,心中一惊,已然打定主意。
瑞雪的表演从辰时到巳时,约莫两个时辰都是瑞雪一人在舞,长袖翻飞,脚步轻盈,纤腰灵活,玉手葱指与绯色的衣服相映成辉,身体的各个部分,就连衣角,朱钗,也与乐曲配合默契,一摇一摆都带上了节奏。
表演结束时,也将近午饭时间,金妈妈一脸笑的数着看客们赏的银子,瑞雪则是不在意的收拾收拾,招呼身边丫头准备离开。
“瑞雪姑娘请留步!”不知何时,那青衫书生爬上了表演的台子。
“你是什么人啊?”不待瑞雪回答,金妈妈就已经拦在了瑞雪前面,“想和我们瑞雪说话,得要这个。”
金妈妈一边说,一边挥挥手中的银钱。青衫书生并不理睬,只将身侧别着的竹箫拿出来,后退两步,面上微笑,然后箫声流溢。
瑞雪听见箫声,面上的惊讶已是无法言说,缓缓提起嗓音,和着箫声唱起来:“蓝天碧水,我望归。层叠山路,绕川回。阵风落英,满地泪。黄泉碧落,永相随!”
一曲毕,两人皆是热泪盈眶。
瑞雪急急绕过金妈妈,看着面前的青衫书生,轻声叫道:“哥……”
“阿雪……”青衫书生张开手臂,抱住了绯衣女子。
这相拥在舞台正中的男女正是当年沉暮之战中的苍平和苍雪。
“你们这是干嘛呢,干嘛呢!”金妈妈看不过去了,“大庭广众下这样搂搂抱抱的,以后还做不做生意了!”
两人被强行分开,金妈妈将瑞雪拽到自己身后,然后瞪着这个青衫书生,骂道:“你是哪儿蹦出来的!不给钱就占瑞雪的便宜吗?瑞雪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抱的!”
“哦,在下桓平,是瑞雪的同胞哥哥。”青衫书生做个揖,微笑道。
“我们瑞雪从来没什么哥哥,你还是……”金妈妈话说了一半又吞回了半句,原来是瑞雪将手上玉镯褪下,塞在了金妈妈手里。
“妈妈,我可以和我哥单独聊聊吗?”瑞雪面纱未除,但眉目里是一股期待与……威慑。
“去吧去吧,早点儿回来啊!”金妈妈收了玉镯,眼睛眯成了一条线,看都不看他们。
二人散步至云池馆附近小茶馆,在二楼靠里的角落坐下。
小二送上几样小菜,一壶清淡的茉莉花茶。
“我以为你回去了……”瑞雪摘下面纱,讷讷开口。
“没有,”桓平为两人倒上茶水,花香四溢,“我在荒城找了你八年……”
“这八年,你是怎么过的?”
“帮别人做小工,抄书,卖画,后来有人请我去做了先生,教私塾的孩子念书,直到现在。”桓平面色忧愁,“当年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这些年又是怎么过的?怎么流落到了这种风月之地?”
瑞雪喝了一口茶水,淡淡道:“当年你把我关在地窖中,我心生不祥之感,便开始奋力撞地窖的门,希望能出来。后来真被我给撞开了,一出来,就听见你的箫声。我想到你那里去,可是越往城墙处跑,士兵就越多,我分不清长平军和大汜军,看见士兵就躲开,于是就绕到了六角塔上,一口气爬上了顶,从上面看下去,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是火。我知道大汜军没有胜的希望,但我希望他们能在这场杀戮中活下去,于是,我唱起了歌。可是长平军闻声赶来,气势汹汹,我慌忙逃窜之间,被散落在地上的尸体绊倒,便晕倒在尸堆中;
醒来的时候,我在一处破旧的房子里面,床是冰冷的,我看到一张令我终身难忘的脸——惨白如纸的脸上,半边长满了麻子一样的肉红色疙瘩,接近黑色的厚唇,眼睛似乎没有黑的部分,像是死人一般。我不由的坐起了身,他对我说,我是他从尸堆里挖出来的,这条命就是他的,从今天开始,他让我往东,我就不能往西!他最喜欢训练小孩子来偷盗欺骗,我无法反抗,被逼着迎合他,但我从来不偷别人的钱财,所以时常没有东西吃,那时候每天都睡在比地还要冰凉的床上,几个孩子挤在一起取暖,吃的也是粗粮米面,直到后来被偶然来访的金妈妈要了去;
金妈妈和这贼人似乎有金钱上的勾搭,贼人那时刚好欠了金妈妈钱,金妈妈便将我带回了云池馆,起先让我接客,可我总是搞砸,她便不再让我接客,觉着我身姿不错,差人教我跳舞,后来渐渐舞出了名头,也不需再接客,就成了现在这样。”
“哥哥没用,只做了个教书匠,没有钱为你赎身。”桓平愤怒的捶向桌子。
“这怨不得哥哥,阿雪命该如此,”瑞雪叹息,“况如今金妈妈待我甚好,我过得尚安稳。”
“我住在世末山中的那个茅庐里,有空便来看看吧!”
“阿雪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