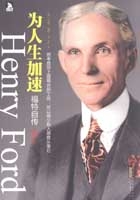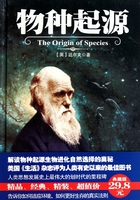等到宋神宗即位,知谏院的吴充也上疏言道:“衙前征用差役这天,官吏来到门前,他们将怀里抱的舂米的木棒和吃饭用的餐具都记录在册,计算为财产,定为分数,以此来应付官府的需求。以至于有的人家财产已经枯竭,拖欠的赋税和债务却还没有了结,子孙都已经没有了,而担保的邻居仍然要抓起来。这样一来,民间为了躲避繁重的差役,有土地却不敢多耕种,骨肉也不敢团聚,都是害怕成为人丁较多的上等户,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了,请求朝廷早日制定乡里衙前差役的标准,以便施行。”
三司使韩绛也说过:“危害农民的弊端,没有能超过差役的。最沉重的负担是衙前,常常使人破产;其次是州役,也需要花费很多钱。我听说过京城的东边有父子二人,将要到衙前服役去了,父亲对儿子说,我准备去死,这样才能使你免除劳役之苦。结果父亲上吊自杀了。又听说江南有人嫁其祖母,并与母亲分居以逃避差役的。这种事完全违背人情事理,几乎不忍心再听下去。还有卖田产给富户,田地归了不必服役之家,而差役还归于本等户,还有一些戕害农民的情况,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希望朝廷内外的官员,都能上疏讲明实际情况,并委托朝廷上的官员一起讨论,参考古代的制度,作出决定,使得差役不致产生这么严重的祸患,让农民都知道为了生活去赚钱,并拥有一份乐于工作的心情。”
所有这些上面谈到的情况,恐怕还不到真实情况的十分之一,尽管如此,千年之后读到这些文字,仍然使人浑身战栗、痛哭流涕,止也止不住。当时遭遇这种厄运的那些人,他们还有人生的乐趣吗?这里所说的衙前服役,不过是所有差役中最苦最累的,还有很多自己设置的名目,多得难以计数。大约衙前服役主要是为官府出力,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催赋税,耆长、弓手、壮丁负责抓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县里的曹司至押录、州里的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稻等,多得不能完全记录下来。各地都根据乡里农户的等级制定服差役的天数,特别规定官员、军队将领、政府中的职员,以及和尚、道士都可以免除劳役。聪明的人投靠这些人家,做他们的用人奴仆,也可以随之免除差役。百姓把得到官府承认出家当和尚视为脱离苦难,和尚身份证的价值,比地契的价值还要高。
而普通百姓和地位低贱的农户服役的次数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困窘,我们看前面摘录的那些奏议就知道,当时的国民经济已陷入困顿之中,情况非常危险,一天都过不下去了。但史书仍然称赞仁宗的时代家家丰衣足食,这就是孟子要发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感叹的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没有比差役制度更严重的了。在这之前,范仲淹认为,全国设置的县过多了,所以造成了差役泛滥,百姓贫困,于是第一次废除了河南府的一些县,准备陆续推广到其他的州府,后来,这个办法受到了旧党的攻击,很快就废除了,那些县也就恢复了。韩琦曾经提出丈量核准每一乡土地的阔狭,以此为依据规定差役的多少,但这些办法只能弥补这个制度的一些缺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司马光说,衙前差役可以实行招募制,其余的差役还是要征用农民,这只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招募就要有报酬,这笔开支从哪里出?司马光想都没想。等到神宗继位,王安石做了宰相,才排除一切干扰,进行改革,开始推行募役法。《文献通考》卷十二记载了大致的情况: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神宗下诏让制置三司条例司宣讲新的役法。条例司讲道:考察综合大家的意见,役法还是以百姓出钱,官府招募服役的人,最为便利,这就是先王曾经实行过的,用百姓的钱,养官府的官员差吏。下面就把具体的执行标准发给将要分赴各地的官员,请他们提出意见,都说可以。于是,又与诸路逐条讨论:衙前已有的费用,重新计算查点是很难的,凡是以前由官府承包给承包商(买扑人)的酒税征收权,他们所缴纳的保证金仍有各地官府支配,和免役钱一起计算用于官府雇人充役。其中,城镇的盐铁专卖税收机构,过去是专门用于奖赏衙前的费用,不能让民间插手,就按照过去制定的数额,仍然作为衙前服役之人的奖赏。还有运送官府物资以及主管仓库、公使库、场驿、税收等工作,过去都曾烦劳当地官府,为之筹划,今后这笔费用就可以省了。
承符、散从等过去从事最苦最繁重差役的人,要补偿他们的亏欠,并改革役法,革除弊端,使他们不再被差役困扰。凡是有产业,有能力,过去不用服役的人,今后要出钱助役。这些都是其中的条目。过了很久,司农寺的人说:如今设立的役法条文,宽厚优待的都是乡村里不能自己表达其愿望的贫苦农民,裁度取用的都是官宦或豪强富户,他们都有控制舆论的能力。如果制度定了下来,那么,地方的官吏也就没有了营私舞弊、巧取豪夺的机会,所以,新法的实行,一定会遇到许多的阻力。如果做事没有主见,缺乏计划,一会儿听这个,一会儿听那个,最终将一事无成。希望根据司农寺郑重说明的这些情况,先从一两个州府开始,等到它做出了成绩,证明新法很有效果,再让其他州府仿效实行。如果这个役法真能有益于百姓,应当特别奖励制定这个法令的人。神宗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提点府界公事赵子几就把他这个府界所要实行的条例报了上去。神宗又下诏给司农寺,并且让邓绾、曾布再详加讨论。
邓绾和曾布上奏说:本地的农户根据财产多寡贫富不同,分为上下五等,坊郭户分为十等,每年夏秋两季,按照等级交钱,其中农户自四等、坊郭户自六等以下不交免役钱。两县中有产业的,上等,各随所在县分开计算交钱;中等则合在一处计算缴纳。分家另立门户的,按分开的产业计算等级,降低户等。官户、女户、寺观和未成丁户等,一律减半缴纳。这些免役钱和助役钱就用来雇用三等以上税户代役,根据役事轻重不同,付给不同的薪俸。开封县有两万两千六百多户,每年的免役钱和助役钱约有一万两千九百贯,代役的薪俸用去一万零两百贯,还能结余两千七百贯,以备荒年灾年歉收。其他县大致相同。既然免役钱或助役钱是按照等级收取,有多有少,那么,过去的户等划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许多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按照这种等级划分收取免役钱或助役钱,显然是不公平的。
为防止户等划分的偏差,宋神宗于是诏令各个郡县,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坊郭三年,乡村五年,在农闲的时候,集中众人,考察他们的贫富情况,清理其中造假作伪的行为,将所有户等重新划分一遍,该升的升,该降的降。有故意不按实际情况划分的,一律以违法论处。被招募的人,要有三个人作保,衙前服役还要有物产作为抵押,受到损失时好索赔;弓手要测试武艺,典吏等要考试书法计算,防止有人滥竽充数。被雇用的人,每三年或两年一换。新法已经完成,张榜公布一个月,老百姓没有疑义的,就定为法令,颁布于天下,正式实施。全国各地风俗不同,差役轻重也不一样,百姓的贫富情况,也有差异,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变通法令。凡是应该服役的人家按照等级交的钱,叫做免役钱。那些坊郭户,以及女户、单丁、未成丁户,还有寺观和官品之家,按照旧的役法,他们是不服役的,他们交的钱,就被称为助役钱。所有这些要收取的钱,先看本州本县招募代役之人需要多少费用,并分配到各户。用于招募代役之人的费用充足了,再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二分,作为水旱荒年的备用。虽然可以增加,但是不能超过二分,叫做免役宽剩钱。
啊!我读条例司和司农寺拟定的役法条目,感叹王安石和他的那些下属,真可以说是体大思精,可以成为立法家的模范了。差役制度对百姓的伤害,既然已经像前面说的那么严重,再不进行改革,绝对不行了。不过,此前的各种差役,固然有繁杂苛细应该免除的一方面,却也有治理国家所必须而不能轻易免除的一方面。如今的熙宁新法,对于其中可以免除的,已经免除了,其中还有不能免除的,但又不能继续让百姓服役,更不能以不再役使百姓为理由,这些工作也不做了。这就需要由国家招募百姓中愿意做这件事的人来做,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但既然是招募,又并非义务的性质,而是带有契约的性质,如果没有报酬,谁肯干呢?而且,国家并非哪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如果有所需求,只能取自老百姓。这样的义务,人民本来已经负担几十年了,只是因为立法不善,所以,贫弱的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而那些狡猾的豪强富户却往往可以幸免。如今按照它固有的义务加以改善和明确,使徭役变成了赋税,这其实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事物的性质,但和前面的法令比起来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增加。这正是免役钱合乎道理的地方。
它的征收,是以财产的多少分出等级,有钱人征收得就多些,贫困的人征收得就很少,最贫穷的那些人,官府还会免除他们的赋税。这与如今许多文明国家所得税的法律正好相同。各国收取所得税,凡是人民中收入很少,只够维持其基本生活的人,是不纳税的,只有当他有了额外收入的时候才纳税。而且他们的纳税,是按照规定好的等级比例累进计算。这其实是非常公平的课税之法,是各国财政学家最为称道的。王安石在数百年前各国尚未发明这种税法的时候,所制定的募役法竟与当代的所得税法殊途同归,比如,核定每家每户的资产,按照贫富上下分出等级,根据等级纳税交钱。农户自四等以下,坊郭户自六等以下,可以免税,豪强大族以及僧侣,也不必纳税和服役,而国家的一切负担,都加在这些软弱无力的平民身上。这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弊政,而法国大革命和近百年来的欧洲各个国家的革命,其动机多半都在这里。
王安石痛心疾首于这种不平等的政策法令,不怕得罪那些豪强大户,依然要求这些人也要缴纳助役钱,这是欧洲各国经过亿万人流血才得到的结果,王安石却能巧妙谋划于朝廷之上,顷刻之间指挥若定,就把事情办成了。他的立法如此完善和周详,已经像前面我们讲过的一样,但仍不敢过于自信,还要张榜公布一个月,老百姓没有疑义了,再定为法令,颁布于天下,正式实施。即使这样,仍不敢过于急躁,而是先在一两个州府试行,等到它有了成效,再推广到其他州府。
所谓勤劳谦虚的君子是一定会有好结果的,不是吗?自从实行了这个法令,此后虽然屡有变迁,但始终不能被废除,直到今天,人民不再知道还有徭役这样的事,说起这个词,往往不能理解,这是谁做的好事?就是王安石啊!此公之举,将尧舜三代以来的弊政一举扫除了,实在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有名气的社会革命。我辈生于今日,已经把这件事淡忘很久了。试看当时人们所说旧社会颠沛流离、困苦不堪的情形,又考察欧洲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见其封建时代的豪族僧侣剥削贫民的事实,可以两两相互印证。而对于王安石,我们该如何崇拜甚至顶礼膜拜啊。但是,数百年来,一犬吠形,百犬吠声,至今还在说他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执拗的人,苛刻残酷的人,甚至说他以权谋私,是个奸邪小人。啊,我们的国民不知感恩的陋习,充分地表现在这里了。
当时制定法令的人说过:如今新法宽厚优待的都是乡村里不能自己表达其愿望的贫苦农民,裁度取用的都是官宦或豪强富户,他们都有控制舆论的能力,看到新法的实行对他们不利,阻挠新法的人一定很多。果然是这样,当时一些所谓士人君子都先后起来攻击新法,他们所持理由,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苏辙说:“服役的人不可不用乡户,即农民,犹如官吏不可不用士人,即读书人。”
苏轼说:“自古以来,服役的人一定要用乡户,犹如吃饭必用五谷,穿衣必用丝麻,水上行走必用舟船,陆地行走必用牛马,虽然在这中间也许会有替代物品,但毕竟不是人们经常用的。”他又说:“士大夫抛家舍业、背井离乡到四面八方去做官,效力之余,也希望能有一些乐趣,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厨房都如此的萧条简陋,就好像一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连饮食都变得很粗劣,这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
神宗曾与他身边的大臣讨论免役的利弊,文彦博说:“祖宗的法制都在,没有必要加以改变以至于失去民心。”神宗说:“役法的改革,在士大夫中有很多人不高兴,但老百姓有没有什么不便利呢?”文彦博说:“因为你是和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并非和百姓一起治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