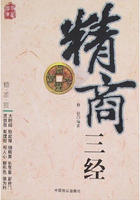有人问:“韩琦、欧阳修二位先生所说既然已经切中他的弊端,王安石却仍然不肯觉悟,虽然都说他性格执拗,但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我想不是这样。当时这些人攻击新法,有问题的地方他们攻击,没有问题的地方他们也攻击,就像王安石所说,他们的意图不是针对新法的。如果为王安石打算的话,只有一件事都不办,什么事都装作看不见,与他们同流合污,似乎也就免去他们的指责了,但这显然不是王安石所希望的。而且,青苗法既然是个很好的法,那么,它的弊端表现在哪里呢?应当说,不是法有弊端,而是人有弊端。就说这个青苗法吧,王安石在鄞县实行是有效的,李参在陕西实行也是有效的,假如每个县都能有一个像王安石这样的人担任县令,那么,每个县都是鄞县了。即使做不到这一点,就算各路都能有一个像李参这样的人担任转运使,由他按照制定好的法令监督下面各个县令,那么,也能出现每一路都和陕西一样的局面啊。
根据条例司核定的人物,全国一共设置了提举官四十一人,以当时有贤德的人才那么多,要想找到四十一个像李参这样的人,应该不难。而且,王安石又不是不想和这些人合作共事,和这些人完全不同。他们听说有个建议是王安石提出来的,都掩耳不听,也不问他提的建议是什么内容;发现有个诏书是王安石拟的,就闭目不看,也不问他拟的这个是什么诏。如果要求他们施行,那么,不是自视道德高尚或倚老卖老来抗拒,就是投下一个弹劾他的奏折离去。诸位君子既然不屑与他合作,他又不能伤天害理一事不做讨好这些人,更不能一个人把天下所有事都承担起来,于是,一定要在这些人之外去寻求愿意帮助他的人,怎么能得到呢?何况,这些人不帮助他也就罢了,他们还在一旁煽动、挑唆和阻挠,私下里庆幸它的弊端越来越显著,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小,这样一来,青苗法本来可以顺利施行而没有弊端的,就因为这些人的缘故,想要它没有弊端,又如何做得到呢?其他的事也和这件事差不太多。
由此说来,我所说的青苗法虽然很好但不一定能够实行,是可以想见的了。假如能使每个像王安石这样的人都做县令,那么,这个法是可行的;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不可行的。没有办法而求其次,那么,假如每个像王安石这样的人能做提举官,似乎也是可行的,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可行的。没有办法再求其次,假如每个像王安石这样的人都能做执政官,那么,在不可行中还有实行的可能性,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不可行的。
然而,青苗法的弊端果然像当时诸位君子说的那样吗?王安石的良法美意,老百姓就一点好处也没有尝到吗?我想,事实不是这样的。历史是诽谤王安石的那些人写成的,他们就是要张扬他的恶行而隐瞒他的好处。凡是可以表现王安石功绩之处,删除务尽,唯恐有不彻底的地方,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完全删除。王安石的《与曾公立书》就记载了“开始以为没有人贷款,实际上前来贷款的人堵也堵不住;后来又担心人们不能按时还贷款,结果还贷的人多到几乎无法应付”的场面,当时民众欢欣鼓舞的情形从这里是可以想见的。他在《上五事札子》一文中写道:“过去,贫苦的农民向富户豪强借债付息,如今,贫苦的农民却向官府借债付息了,官府把利息定得很低,解救了老百姓的困苦。”这是青苗法实行数年之后所获得的成效。他在《谢赐元丰敕令格式表》中写道:“开创新法于其他人之前,获得成功却在反对意见兴起之后。”这就是说,王安石罢相之后,新法的效益才显现出来了。
当然,也可以说,这些都是王安石自己的看法,不一定令人信服,我们再看看旁观者是怎么说的。河北转运司王广廉入奏时说:“老百姓都欢呼感念这个德政呢。”李定来到京师,李常见到他,问道:“你从南方来,那里的百姓对青苗法怎么看?”李定告诉他:“百姓感到很便利,没有不喜欢的。”李常对他说:“整个朝廷如今都在议论这件事,你千万不要乱说啊。”李定说:“我只知按照真实情况发言,不知道京师的规矩。这里是那时的舆论中心,有人想封住别人的嘴巴,其实是不可能的。”这样说有人也许还会认为,你列举的这些都是依附于王安石,想从他那里获得宠信的人说的话,并不可信。那好,我们再来看看王安石的反对派是怎么说的。朱熹在《金华社仓记》中写道:“根据我所看到的前代知名人士的论述,对照今天发生的事情来说,青苗法的立法动机,并没有什么恶意,出发点还是很好的。”程颢也曾谈到,他后来有些悔恨自己先前的过于偏激。
这说明程颢先生晚年已经认识到他先前攻击青苗法是不对的,而且,朱熹还写诗歌诵青苗法。苏轼在《与滕达道书》中写道:“我们这些人在新法实行之初,总是不肯放弃自己的偏见,这才有了与王安石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们也是一片忠心,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但说了许多错话,其中很少有符合事理的。如今皇上圣明,国家充满了新的气象,社会风气也明显好转,回过头去看看我们所坚持的,更感到离正确很远了。”这是苏轼晚年对自己行为的一种深深忏悔,感叹社会风气的转变。他的这段话与王安石获得成功在反对意见兴起之后的说法其实是一致的。这里所谓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大概指的就是新法的实行,而青苗法正是新法中的一种。像程颢、苏轼,都是当时反对新法最卖力的人,他们都这样,如果不是真有成效,他们会这样说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与程颢、苏轼同样“深自忏悔”的人还有很多,只不过,他们没有把自己想说的话留给后人。
还不仅仅如此,元祐初年(公元1086年),宋哲宗刚继位,就将新法全部废除了。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废除青苗法。同年三月,范纯仁就以国家的经费不够用为理由,请求恢复青苗法。八月,司马光也上奏称,实行青苗法对百姓是有利的,只是不能强迫他们借贷。这些都是写在奏折公文中记入正史的。像司马光、范纯仁都是当时最早出来反对青苗法的人,也是攻击王安石最用力的人,为什么十八年后,却又对青苗法这样津津乐道呢?由此也可看出,青苗法在当时是卓有成效的,而且,老百姓已经在它的浸润中享受很久了,尽管有人一直想要掩盖它的成效,其实是不可能的。然而先前的那些骂声,又是为了什么呢?有一种说法,对于普通百姓,不能和他们谋划事情的开始,只能和他们享受成果。然而,那些正人君子,他们是普通百姓吗?即使我辈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仍然觉得青苗法是很难实行的,但王安石当时还是实行了,虽说它的弊端是不可避免的,但其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于是更加佩服王安石的才能是没有人可以赶得上的,那种诋毁当时奉行新法的人都是小人的说法,我始终不敢相信。
以更加平常的心态来看青苗法,它不过就是个银行业而已,希望它能抑制兼并,其功效大概是很小的。银行作为一种产业,它的性质是适宜民办,不适宜官办的。如果国家能够制定出详细的条例,使借贷的人和要求借贷的人都能受益,而没有理由相互埋怨,国家再设立一个中央银行,以此来协调各家私立银行,不必直接贷款给老百姓,那么,银行的核心价值就算是得到了。王安石做这件事,有点像替关公耍大刀,很容易伤了自己的手。当然,这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说这番话,事实上,当时的人民既没有设立银行的能力,而且,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各行各业都受困于资金的短缺,呈现出衰败的景象。王安石能够洞察其中的原因,创造了这个办法来救治,没有超过一般人的见识和胆略能做到吗?中国人中知道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命脉的,从古到今,只有王安石一个人。
后来,也有事实上实行青苗法而避开不用这个名称的,像朱熹搞社仓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他的方法也是利息十取其二,夏天发放而冬天收取,这与青苗法有什么区别吗?朱熹在崇安县推行这种方法收到很好的效果,就想推广到全国去;就像王安石在鄞县实行青苗法很有效,也想推行到全国去是一样的。朱熹平时痛心疾首地诋毁王安石,认为他非常急切地鼓动大家谋求财富,使得天下所有人都变得非常浮躁,而丧失了生活的乐趣。等到他发起社仓的倡议之后,有人问他,以前不是指责王安石这样做是不对的吗?他就很激动地说:“王安石只有青苗法这一件事是对的。”王安石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急切地谋求财富吗?王安石果然只有青苗法这一件事做对了吗?他说你对就是对罢了。
第三,均输法
均输法也是一种惠民政策。它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地方对京城的物资运输,如何减少盲目性,使其更加合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写了《乞制置三司条例》一文,其中写道:
我观察先王制定的赋税法,在国都的周边地区,征收的赋税实物,有精品,也有粗货,等级标准是以一百里为限来划分的,而那些离国都比较远的诸侯国,就根据他们各自出产的货物来进贡。同时,又规定可以灵活变通,以货币或实物进行贸易也是允许的,对于市场管理,货物的流通,原则上是没有的使它有,有害的就从市场上清除出去。那些在市场上卖不出去,滞销在民间的货物,就由政府委派官吏收购下来,以备临时要买的人,所有这些都不是对货物的垄断。
作为一个君主,聚积起天下的百姓,就不能没有财物;管理天下的财物,则不能没有原则和办法;以一定的原则和办法管理天下的财物,安排转运输送物资的工作,就要注意劳逸的均衡;费用或多或少,就需要相互沟通;资金或有或无,也不能不加以控制;而物价的高低、货物的收购或卖出,管理好这件事,也不能没有一套办法。
如今,天下的财政和物资供应已经到了非常窘迫的地步,主管的官员却死守着不合理的制度,朝廷和地方相互之间不通气,赋税收入有盈有亏,也不能互相弥补。每一路上缴的贡品,年有定额,遇到丰年或路途近便的,本来可以多运送一些,却不敢多收;碰到荒年物贵的时候,很难将贡品准备充足,他们也不敢减少。远处上缴贡品要花几倍的运费,但在京城却只值一半的价钱。三司转运使只知道按照规定的额度和期限来收取,不敢有任何的增减调整。碰到国家有重要的军费开支或皇帝的郊祭大典,只能派官吏四处搜刮,洗劫一空。各级政府管理财政的官吏,往往隐瞒真情,不说实话,尽量为自己多留一点应付临时开支的本钱。他们还担心一年的预算不够用,往往采取改变缴纳赋税地点的方式,勒索缴纳赋税的农户多交运输费。农户为了缴足赋税的额度,往往要花费比原来规定多出一倍的财物,而且,朝廷需要的物品,总是求索于不产这些物品的地区,或不产这些物品的时节,那些富户或投机商人就乘公私急需的机会,操纵市场和物价。
我们认为,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赋税收入,他的职责就是管好茶、盐、矾的税收,军事储备和国家行政开支,很多都要靠它们来供给,朝廷应该拨给专款,作为周转的经费,使他们能够全面掌握东南六路的财物赋税的情况,以便灵活调拨。凡是收购赋税上缴的物品都应该避开价格高的地区,而去价格便宜的地区,到离京城近的地区,不到远离京城的地区。京城仓库储备情况以及每年支出的数目、现存的数量和所要供应的数量,都要让发运使预先知道,有所准备,以便随时处理所掌握的物资,等待上面的调用。这样,朝廷就可以逐渐掌握市场的控制权,调配物资的有无,做到便利地转运输送,节省费用和劳役,革除沉重的赋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国家财政或许从此能充裕起来,百姓生活财用也不再感到匮乏。
《宋史·食货志》记载了均输法施行过程的始末:
王安石亲自撰写的《乞制置三司条例》已经上报,皇上也已经下诏批准,不久,就作为均输新法,正式颁布实施了,并委托江、淮、两浙、荆湖六路发运使薛向总领六路发运与均输平准事宜。朝廷还从内藏库拨款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担,作为营运资本,由薛向全权支配。曾有议论担心有人干扰他的工作,薛向既总领其事,于是请求设置所属官吏,报朝廷备案。神宗允许他自己选配官吏。薛向于是聘请了刘恍、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其部属,又要求地方官吏报告六路每年应当上缴的数额、京城每年的支出,以及现在仓库中的储备等情况,凡是应该预先规划的,都提前向有关官员汇报,他们都按照要求去做。其后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知谏院范纯仁、谏官李常等都屡次上疏批评均输法,并且弹劾薛向,宋神宗一律不予采纳,还下诏奖励薛向。然而,均输法并没有贯彻施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