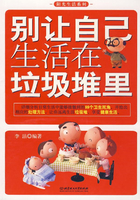66.我们的作者说:“教育人服从君主的规条是用‘孝敬你的父亲’这句话来表达的,就好像一切权力本来就都在父亲身上一样。”但我想,这规条也同样表达“孝敬你的母亲”这句话中,就好像一切的权力本来就都在母亲身上一样。我请求读者考虑一下,这一方的论证是否和那一方的论证同样有道理,因为在《新约》和《旧约》中劝诫子女要孝敬服从的内容中,都是把“父亲”和“母亲”相提并论的。其次,我们的作者还告诉我们说:“‘孝敬你的父亲’这一诫命授予治理之权,并使政府的形式成为君主政体。”对于这话,我的回答是,如果“孝敬你的父亲”这句话是指要服从官长的政治权力,那么它便不涉及我们对自己生父应尽的责任。
因为依照我们的作者的学说,我们的生父已经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因为全部权力都应当归于君主;他们与他们的儿女一样都是臣下和奴隶,虽然是生父,也不能享受那含有政治隶属意味的“孝敬和服从”的权利。如果按照我们救主的解释(见《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及上述其他各处),“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是指我们对我们的生身父母应尽的责任,这种解释显然是对的,那么它便与政治服从无关了,而只是对那些既没有资格享受统治权,又不具有像官长支配臣民那样的政治权力的人应尽的一种义务。因为个人具有的父亲身份,与最高官长享有的服从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因此,这一诫命涉及的必然是我们的生身父亲这个个体,必然是指我们对生父应尽的职责,它不同于我们对官长的服从,即使是极端专制的君主权也不能解除这种职责。那么这种职责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应讲到它时再加以考察。
67.我们的作者假设亚当有“绝对无限的统治权”,因此,此后的人类从一生下来就都是“奴隶”,绝没有任何自由的权利。对于他提出来的看似可以作为论据的一切东西,我们终于全部考察过了。但是,如果上帝的创造只是给予了人类一种存在,而不是把亚当创造成“他的后裔的君主”;如果亚当(《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八节)没有被确立为人类的主人,也没有被赋予一种除了能支配他的儿女外的“个人的支配权”,而只是被给予人类子孙共同享有的支配土地和下级动物的权利和权力;如果上帝(《创世记》第三章第十六节)没有给予亚当支配他的妻子和儿女的政治权力,而只是使夏娃服从于亚当,以此作为一种对她的惩罚,或者只是预言了在有关家庭共同事务的处理上女性的从属地位,但并没有因此给予作为丈夫的亚当生杀予夺之权,这种权力必然是属于行政官长的;如果父亲们并不能因生育儿女而取得对他们的支配权;如果“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一诫命也没有授予他这种权力,而只是责成儿女对双亲应尽同样的责任,而不管他们是否是臣民,并且对母亲也要与对父亲一样。
如果上述诸点都是对的——在我看来,根据上面所说的论证,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不管我们的作者怎样坚决地予以否认,人类也确实具有一种“天赋的自由”。这是因为一切具有相同的天性、能力和力量的人从本性上说都是生而平等的,都应该享受共同的权利和特权,除非有人能指出,作为万物之主并永受祝福的上帝用明白语言所表达出来的选任,用以显示某一特定个人的优越性,或者应拿出一个人对他的上级表示服从所作出的承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就连我们的作者自己也承认说:“王权的有力拥护者约翰·黑沃德爵士(Sir John Heyward)、布莱克伍德(Blackwood)和巴克利(Barclay)三人都不能否认,而异口同声地承认了人类天赋的自由和平等”,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我们的作者认为,“亚当是绝对的君主”,因此“人类不是生而自由的”,但他所提出的任何论据都远远不能证明他的伟大主张,甚至同他的主张自相矛盾。所以,用他自己的论证方法来说,“最初的荒谬原则一旦失败,这个绝对权力和专制制度的庞大机构也就随之坍塌”,因此对于他在如此荒谬和脆弱的基础上建立的一切理论,也就没有更多的必要给予答复了。
68.但是为了省去他人的麻烦,在必要时,他又不惜用其自相矛盾的说法来显示自己的主张的弱点。亚当的绝对的和唯一的支配权是他一直说到并一直以此为根据的论点,可是他又告诉我们说:“亚当既然是他儿子的君主,那么他的儿子们因此也对他们自己的儿子有支配力和权威。”按照我们的作者的这种计算方法,亚当凭借其父亲身份所享有的这种无限和不可分割的统治权,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并且只存在于第一代;一旦他有了孙儿,罗伯特爵士的说法便讲不通了。他说,亚当作为他的儿子们的父亲,“对他们拥有的绝对无限的王权,因此,对于他们所生的孩子,以至世世代代都有支配权”,可是他的儿子们,即该隐和塞特,也对自己的儿女享有父权,因此他们同时既是“绝对的主”又是“臣民”和“奴隶”。作为“他这一族的祖父”,亚当拥有一切权力,然而他的儿子们作为父亲也有一份权力。亚当因为生育了他们,就对他们和他们的后裔享有绝对权力,但是他的孩子们根据同一资格也应当对他们自己的子孙有绝对的权力。
我们的作者说:“不是这样的,亚当的儿子们在他之下有权力支配他们自己的子孙,但仍须从属于最初的父母亲。”这种区分听起来很不错,但可惜没有什么意义,与我们的作者的话也不一致。我完全可以承认,如果亚当对他的后裔有“绝对的权力”,他的任何一个子女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得一种委托,使其享有对其余全体或一部分人的权力,因而这也是一种“从属的”权力。但是,那就不可能是我们的作者在这儿所说的那种权力。这种权力不是一种由授予或委托而来的权力,而是他认为的一个父亲对儿子们应有的自然的父权。
原因有三:第一,他说:“既然亚当是他的儿子们的主宰,所以在他之下的儿子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孩子也有支配权。”那么,他们依照同样的方式,并且根据与亚当同样的资格,即凭借生育儿女的资格和父亲的身份,同样也是他们自己的孩子的主宰。第二,我们作者的意思很明显是指父亲们的自然权力,因为他把这种权力限制在“他们自己的孩子”的范围内,而委托的权力是没有这种限制的,它除了对自己的儿女们以外,还可以支配别人。第三,如果它真的是一种委托的权力,它一定会出现在《圣经》里,但在《圣经》中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实亚当的孩子们除了自然的父权外,对于他们自己的孩子还拥有任何别的权力。
69.但是,他在这里的意思只是指父权而不是指其他权力,这从他在随后进行的推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么,我不晓得亚当或其他任何人的孩子们,是怎样可以免去对他们父母的从属的。”由此可见,我们的作者在这里所说的一方的“权力”和另一方的“从属”,只是父子之间的那种“自然的权力”和“从属”。因为每一个人的子女应当忠于的权力,不可能是其他权力,就连我们的作者也常断言这种权力是绝对的和无限的。我们的作者说,亚当对于他的后裔享有自然“权力”,这是父母对于他们的孩子应有的;我们的作者又说,这种父亲支配孩子们的权力,当他在世时他的儿女们对自己的儿女们也同样具有。
因此,亚当根据父亲的自然权利,对他的一切后裔都拥有绝对无限的权力,而在同时,他的儿子们根据同样的权利,对自己的后裔也有绝对无限的权力。于是这里就同时出现了两个绝对无限的权力,我倒希望有人能把它们协调起来,或使之符合常识,而他却插入“从属”这个词语来区分,这只能使他的话变得更不合理。让一种“绝对的,无限的”,甚至是“不可限制的权力”,去从属于另一个权力,这件事显然矛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亚当是绝对的君主,因父亲的身份享有支配其所有后裔的无限权力。”那么,正像我们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的一切后裔,都绝对是他的臣民,是“他的奴隶”。“儿子们和孙子们同样处于这种从属和奴隶的状态之中”,但我们的作者又说,“亚当的孩子们对他们自己的孩子们享有父权(绝对的、无限的权力)”,用简单的话来说,这就是,他们在同一政府中,既是奴隶又是绝对的君主,即一部分臣民会因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利享有对另一部分人绝对无限的权力。
70.如果有人为我们的作者解释,认为他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本身从属于自己父母的绝对权力之下的人们,对于自己的孩子们仍然保有一些权力。我承认,这样的说法比较接近于真理,但这不会对我们的作者有任何帮助,因为我们的作者一说到父权,便总是指绝对无限的权力,除非他自己对这种权力加以限制,并指出它所能达到的限度,否则我们无法设想他会有任何其他的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广泛的父权,这从下面紧接着的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说:“孩子们的从属是一切王权的根源。”既然他在上面说“每一个人对他的父亲的从属”,那么也就包括亚当的孙子们对其父亲们的“从属”,而这些都是一切“王权”——我们作者所说的绝对的、不可限制的权——根源的从属。
这样,亚当的儿子们对自己的孩子们就享有“王权”,但同时他们又与自己的孩子们同样是臣民大众,他们也是其父亲的臣民。但是,他喜欢怎样解释,就让他怎样解释吧。很显然,他让“亚当的孩子们同其他一切父亲们一样享有对自己孩子们的父权”,这就必然会导致下面两种情况之一:要么是亚当的孩子们在亚当在世时就和其他父亲们一样——他的用词是“根据父亲的身份,对自己的孩子们享有王的权力”;要么是“亚当根据父亲身份的权利而不享有王的权力”,因为对于那些具有父亲权力的人来说,父权不是给予他们王权,就是不给予。如果它确实给予王权的话,那么,凡有“父权”的人都有“王权”,于是,按照我们的作者的父权制政府论,有多少父亲,就会有多少君主;如果它不给予的话,那么,亚当就不能因父亲的身份而成为统治者,别人也不能如此,这样一来,我们的作者的全部政治学说便立刻崩溃坍塌了。
71.因此,他到底确立了怎样的君主制,就让他和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考虑吧。君主们当然有很大的理由感谢他的这种新政治学,因为这种政治学意味着在每一个国家里有多少父亲就可设立多少君主。依照我们的作者的原理来立论,这是不能避免的,但谁能因此而谴责我们的作者呢?因为,既然把一种“绝对权利”交给了“因生育权而取得身份的父亲们”,他就很难决定孩子们对自己的孩子所享有的这种权力应当是多大。结果,就像他所做的那样,把一切的权力授予亚当,而当亚当在世时,他的儿子们已做了父亲的时候,又要让他们享有我们的作者无法否认的一部分权力,结果这就成了一桩非常难办的事情了。这种困难使他在用语上非常模糊,并在把“父权”这种绝对自然权安置在何处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诸多情况。有时:只有亚当一个人享有这种权力。
有时:“双亲”都享有这种权力,而“双亲”一词经常不是单指父亲一人的。
有时:父亲在世时“儿子们”享有。
有时:“家族的父亲们”享有。
有时:泛指的“父亲们”享有。
有时:“亚当的嗣子”享有。
有时:“亚当的后裔”享有。
有时:“先祖们,挪亚的一切儿子们和孙子们”享有。
有时:“最年长的双亲”享有。
有时:一切的王享有。
有时:一切具有最高权力的人享有。
有时:“最早的祖先——他们最初是全人类的生身父母——的嗣子”享有。
有时:一个选王享有。
有时:治理“国家”的人们享有,不管其是少数几个人,或是一群人。
有时:能够攫取这种权力的人——一个“篡位者”享有。
72.就这样,依照罗伯特爵士的见解,这个享有一切权力、威力和治理权的“新的乌有先生”,也就是这个用以指定和确立人民必须服从的君主和君位的“父的身份”,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归任何人所有。按照他的这种政治学的结果是,他可以把王权给予民主制度,也可以使篡夺者成为合法的君王。如果他的政治学竟能起到这样奇妙的作用的话,那我们的作者和他的信徒们便是依靠他们万能的“父的身份”,做出了大大的贡献。因为除了把世界上一切合法的政府推翻、摧毁,并代之以动乱、专制和篡夺以外,这个“父的身份”是没有任何别的用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