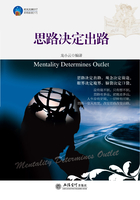为了理解该发展的必然性,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政府设立的动机了,应该去考察政府实际上采用的组织形式,以及它随后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因为这些弊端使政府的设立和腐败成为必然。我们不需要去考虑斯巴达的情况,因为那儿的法律主要关注的是儿童的教育问题,而莱格古士为他们开创的风气让法律本身成了多余。作为一种规定,法律自身的约束力弱于人们本身的欲望,它能做的只是限制人们而无法改变人们。不难证明,任何一个政府如果能够像它成立之初那样一成不变地走下去,杜绝任何变革或者腐化,那么这个政府本来就没有成立的必要了。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假如任何一个人都不触犯法律,并且任何一个官员也都不滥用权力,那么在这个国家,无论是法律,还是官员,其实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政治上的差别必然会导致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而官员同民众之间不平等的扩大也必然会导致民众之间不平等的产生,而且,不平等还会因欲望、才能,以及环境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官员们通过篡夺非法权力来提拔一群走狗,并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分给他们。同时,人们在盲目野心的驱动下,甘愿受别人的压迫,他们不会向上看,相反却是向下看,比起当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来说,他们更热衷于压迫别人,他们之所以甘做奴隶正是为了反过来去奴役其他人。你很难让一个没有野心控制别人的人去服从别人,即便是最精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让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屈服。
然而,不平等却可以轻易地在懦夫和野心家那里横行,这些人时刻在等待时机,随时都做好了冒险的准备,不管是统治别人还是服从别人,对他们来说,这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而,必然会降临这样的一个时代,到那时,人们的双眼已被完全蒙蔽,只要统治者对他们中间最卑微的一个人说:“让你以及你的子孙后代都成为贵族吧!”这个人便立即在众人面前尊贵起来,甚至连他自己也会认为自己很尊贵。并且年代越久远,他的后裔就会越显尊贵,而他们家族成为贵族的原因也会越来越模糊不清,越难以确定,这个身份所产生的效果就会越强。也就是说,在一个家族中无所事事的人越多,这个家族就越显赫。
如果这儿是探究细节的地方,那么,我会很乐意解释,为什么即使在没有政府的干预的时候,人们之间也会产生声望和权威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一旦结成社会,人们就会开始相互比较,并且在与邻居们持续不断的交往中,发现他们之间的种种差异。这些差异有几种主要类型,主要通过财富、地位(或等级)、权力还有个人品质来相互评价。我可以证明这几个方面之间的和谐或者冲突是判断国家制度好与坏的最可靠的标志。另外,我还可以指明,在这四种不平等之中,个人品质之间的不平等是其他所有不平等的基础,而财富上的不平等则是最终的不平等。因为财富直接指向人们的幸福,而又最容易转移,财富还可以用来购买其他的一切东西。通过以上的观察,我们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一个民族距离原始状态的远近,还有这个民族在走向衰败极点进程中所处的位置。而借助这一点,我便能解释追求声望、荣誉还有地位的普遍愿望是怎样激起了所有人的热情,怎样锤炼并使他们不断较量着彼此的力量和才能。同样,我也能解释它是怎样刺激着我们的欲望,令我们的欲望迅速膨胀。它把无数野心家置于同一个竞赛场上,开启了人们无处不在的竞争和对抗——也可以说是敌对,从而造成了不计其数的成功、失败和混乱。
人们具有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欲望,出人头地的冲动。我可以证明,正是人们的这些欲望和冲动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恶,还有少量的善,也给了我们最骄傲和最可鄙的东西:美德和恶习,科学和谬误,哲学家和征服者。总之,我能够证明,因为强者只珍惜那些弱者没有的东西,没有弱者悲惨的命运,强者就感觉不到自己固有的幸福,所以始终只有小部分富有而强大的人能够站在命运塔顶的光环中,而大部分人只能是缺衣少食,默默无闻。
只是对上述观点进行一些详细阐述便足以写出一部巨著了,我们还可以通过与自然状态的对比,把各种政府的利弊拿来比较一番。同时,我们还可以揭示,由于政府的不同性质以及由于时间的发展而不可避免产生的变革中,那些已经产生的不平等以及在未来数世纪中将会产生的不平等的各种表现形式。我们能够看到,为了反抗国外压迫者,人民大众所作的所有努力最终却压迫了他们自身;我们能够看到,统治者的权力在无限地扩张,而被压迫者却丝毫不能看到这种压迫在何时才能停止,更不知道他们能有什么合法的方式可以用来反抗这种压迫;我们能够看到,公民权利和民族自由正在逐渐地消失,而弱者的所有不满、抱怨以及要求都被视作叛乱的怨言;我们能够看到,政治将保卫公众利益的荣誉仅赋予人民中的那一小部分吃皇粮的官员;我们能够看到,赋税随之产生,悲惨的农民不堪苛捐杂税的压榨,他们即便在和平年代也不得不抛弃田地,扔掉犁铧,举剑而起;我们还能够看到,各种混乱荒唐的荣誉法则出现了,而国家的保卫者迟早会变成人民的敌人,最终只会将他们的利剑插入同胞的胸膛;到最后,这样一个时代将会降临,人们会对他们的统治者说:
“你命令我将利剑刺入父亲的胸膛,
刺入怀孕妻子的腹中,
我终将执行你的命令,
尽管我的双手始终坚持反抗。”
从财富与地位的极端不平等中,从各式各样的欲望与才能中,从那些无用却有害的技术与无聊的科学中,产生了大量的偏见,这些偏见同时还违反了幸福、理性还有道德。我们可以看见,掌权者费尽心机来破坏民众的联合,不断在民众之间制造分裂。他们制造一切能引起分裂的争端,然而,在表面上,他们却又维持着社会和谐,他们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与权利对立起来,促使各阶层的人民彼此猜疑、相互敌对,趁机加强他们自己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动荡和混乱中,暴政逐渐抬起了它那罪恶的头,吞噬了整个国家里一切健康完整的事物,最终也践踏了法律以及人民,在共和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它的统治。暴政建立之前的那一个时期,必然是动荡且充满灾难的时期。但是最终,一切都会被这个恶魔吞噬,到那时人民不再有首领,也不再有法律,他们剩下的只有暴君。从这时起,世间再也没有品行和道德可言,要知道,在暴政肆虐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从忠贞那里得到一些什么,也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主人。只要暴君一声令下,正义和职责就会黯然失色,而奴隶能够拥有的唯一美德只有盲从。
这便是不平等的终点,是一个圆圈的封闭点,至此,一切又都与开始的起点重合。此时,每一个个体便回到了最初的那个平等的状态,因为此时的他们同样一无所有。除了君主的意志外,臣民们不再拥有任何的法律,除了自己的欲望,君主不再受别的限制。所有的善良观念和公正原则重新消失了。此时的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强者法则,回到了一个全新的自然状态中。这个全新的自然状态同原初的自然状态有所不同:原初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纯粹的状态,而现在这种全新的自然状态则是极度腐化的结果。但在其他各方面,这两种状态的差别都十分小,而且政府契约已经被暴政破坏殆尽了。因此,只有当暴君是一个国家最强者的时候,他才算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一旦他被驱逐,他便连抱怨的权利都没有。民众发动暴动杀死或是推翻君主,这些行为,就像国王前一天处理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一样合法。国王通过暴力建立了政权,同样地,他的政权也会被暴力推翻。这样一来,一切便又会根据自然秩序行事,所以,无论频繁而短暂的革命会带来哪种后果,都没有人可以抱怨别人做事的不公正,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埋怨自己的不幸或过失。
假如细心的读者想发现并追溯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之间,人类所经历的那些已经被人所遗忘的过程,依据刚才我所描述的那种中间状态,细心地重现了我由于时间仓促而不得不舍弃的讨论,或者由于我的想象力所限而尚未揭示的那个部分,他必定会惊讶地发现,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巨大!假如读者追寻到了这种极其缓慢的过程,他便能解决许多哲学家们都不能解决的政治伦理问题。他将会发现人在不同的时代是不同的,他就会明白,第欧根尼之所以找不到“人”,是由于他是在他的时代中寻找以往时代的人。他就会了解,加图之所以和罗马及自由同归于尽,是因为他生错了时代。假如他能够早生五百年,那么他一定统治了罗马,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伟大的人一定会让世界震惊。总之,借助于这样的分析,读者便可以解释人的精神和欲望是怎样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他们的自然本性,为何我们的需求和兴趣的对象都发生了改变,以及为什么在原始人渐渐消失的时候,社会却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由做作的人与肤浅的欲望组成的集合体。而这个集合体是所有新产生的联系的产物,它在自然状态中完全没有任何真正的基础。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都被观察所证实,在内心深处和行为倾向上,原始人和文明人都如此不同,以至于为其中一者带来许多快乐的东西对另外一者来说却是绝望的深渊。原始人呼吸着自由和宁静的空气,他们只愿过一种闲散的生活,即便是斯葛多派的淡泊也远远比不上他们对身外之物的冷漠。而文明人却是整日奔波,劳心劳力,他们似乎只是想让自己更加劳苦,因而一生劳作,至死方休。为了生存,他们往往会面临死亡的危险,或者会为了追求永生而自绝于世。文明人对自己憎恨的权贵和鄙视的富翁也会大献殷勤,而且会一刻不停地追求为这些人服务的荣耀;他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的卑贱以及别人给他的庇荫,他以做奴隶而感到自豪,同时他们还以轻蔑的言辞嘲笑那些不能享受这种荣耀的人。试问:一个加勒比人会怎样去评价欧洲大臣繁重而令人羡慕的工作?这个悠闲的原始人宁愿经历多次残酷的死亡,也不会愿意过那样的一种生活,即使这种生活中有行善的乐趣,也无法让他感到高兴。如果想让这个原始人了解这一切热情的来源,他首先就必须知道“权力”和“荣誉”这两个词的真正含义。
除此之外,他还应该知道有一些人重视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的看法,这些人的幸福和满足更多地来源于别人的评价,而非仅仅根据自己的感受。实际上,原始人和文明人之间存在差别的根源在于:原始人只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而文明人则是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外,他们只知道按照别人的意愿来生活,以至于似乎只有通过别人对他的评价才可以体现出自己生存的意义。在这里,我不想追究为什么尽管有如此之多讨论道德的漂亮文章,人的这种品性仍然产生了对善恶观念的冷漠;也从没打算致力于探明为什么一切事物都简化为表象,甚至友谊、荣誉、美德以及罪恶本身都只剩下了矫揉造作,而从这种矫揉造作中,我们终于学会了吹嘘的秘诀。总之,我并不打算追问,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问别人自己是什么,却从来不敢问自己这个问题。在众多的哲学道理、文明、人性以及高尚的道德箴言中,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拥有的就只是轻浮、虚假的表象而已:拥有荣誉却失去了道德,会思考却不能拥有智慧,耽于享受却追寻不到幸福。我不想去追究这些问题,我只需要证明,这些绝不是人类的自然本性,而是社会的精神还有社会产生的不平等改变和破坏了我们原本拥有的所有自然品性。
我已经追溯了不平等的发展和起源,还有政治社会的建立过程及其必然会产生的种种弊端,我都是尽量只靠推理,从人类的本性中将这些推演出来,丝毫没有受到神圣教义的影响,因为这些教义从一开始就赋予君主以神圣的权威。从本文的说明可以知道,在自然状态中,几乎不存在任何的不平等,现在所盛行的一切不平等都是来源于人类能力的发展与思想的进步,这些不平等还会随着此二者的发展而逐渐加深。最终,在私有制和法律确立之后,不平等被确定为永恒的合法现象。另外,只由实在法确立的精神不平等在与生理不平等相抵触的时候,它便会与自然法则相冲突。这两种不平等之间的差异足以让我们确定,在对待一切文明国家之中的那种不平等时应该持有怎样的看法。不管人们是如何定义不平等的,傻子命令智者,儿童指挥老人,少数权贵挥霍无度,而民众却由于缺少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忍饥挨饿,这些显然都是违反自然法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