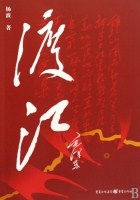除此之外,既然这样概括出自己的思想来的艺术,是人类理智最艰难而又最迟缓的一种运用,那么,人类的共同点是否就永远也无法从这种推论中得出自己行为的准则了呢?并且,当一桩具体行动需要请教公意时,一个用心良好的人有多少次在运用上或者在准则上犯错误,自以为服从法则却只不过是在追随自己的倾向呀!可是,他将谛听内心的声音吗?他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不会犯错误呢?但是人们说,那种声音无非就是根据社会内部的判断习惯和感觉习惯形成的,因此就不可能有助于它们确定。
然后,又必须是在他的内心里并没有涌现出任何类似的热情,其声调竟淹没了他那怯弱的声音并高出于良心之上,从而让哲学家们能够坚持认为那种声音不存在。他将咨询成文的权利原理、各个民族的社会行为、人类敌人的默契约定本身吗?我们终归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难题上,而且它不外是我们依据自己的想象而抽绎出其观念并且在我们中间奠定的那种社会秩序罢了。我们对普遍社会的设想是根据我们对特殊社会的理解的,小共和国的建立让我们梦想着更大的,而我们都仅仅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开始变成人的。从中我们便可以看出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些所谓的世界公民了。他们用自己爱全人类来证明自己爱祖国,为了可以有权不爱任何人,他们自诩爱一切人。
在这方面,推理向我们所指明的已全部被证实;只需略微回顾一下远古时期,我们就很容易看到,对人人所共有的博爱以及对自然权利的健全观点,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开始传播的,并且因为它们在世界上进展得异常缓慢,以至于仅仅到了基督教时代才得以充分普及。我们在查士丁尼的法律中也发现,古代的暴力在许多方面都是得到认可的,不论是对已经被宣布的敌人,还是对不属于帝国臣民的一切人,所以罗马的人道也并不比他们的统治权普及得更远。
正像格老秀斯所指出的,事实上,人们长时期都相信自己可以去掠夺、盗窃、虐待异邦人尤其是野蛮人,直至把这些人变为奴隶。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总要问陌生人是不是海盗或贼匪,会不会冒犯他们,因为这种行业在当时被看做是荣誉的,远不是不光彩的。最早的英雄们,如德修斯和赫居里士,是在向贼匪作战,因此自己才不肯盗劫;而希腊人则常是把那些压根并不处于交战中的民族所订的条约称为和平条约。对许多古代民族而言,甚至于对拉丁人而言,敌人和异邦人这两个名词长期以来就是同义词。西塞罗说:Hostis enim apud majores nostros dicebatur,quem nunc peregrinum dicimus.(“凡是曾被我们大多数人称为陌生人的,现在就被称为异邦人。”)所以,霍布斯的错误在于他对人类假设了那种自然状态,并且把本来是罪恶的结果当成了罪恶的原因,并不在于他在独立的但已变成了社会人的人们中间引发了战争状态。
但是,虽然他们成为社会人的时候变得十分不幸而又作恶多端,虽然人与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和自然的社会,虽然平等和正义的法则对那些既生活于自然状态的自由之中而同时又屈服于社会状态的需要之下的人们而言,全都是空话,也不能说我们就不会有幸福和德行了,我们已经无可救药地被上天遗弃,被人类给腐化了,哪怕是从坏事里面,我们也要努力汲取出能够医治补救的办法吧。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要以新的结合来纠正普遍结合的缺点吧。但愿我们言辞激烈的提问人能够以成就来评判他自己。
让我们向他指出所谓幸福的那种状态的全部悲惨、所谓健全的那种推论的全部谬误吧;让我们用完美的艺术来指出艺术开始给自然所造成的灾祸的那种补偿吧。但愿他在和他的同类分享自己的生存和福祉时,能学会成倍地增长它们吧;但愿他从更美好的体制里,能看到对坏事的惩罚、善良行为的报酬以及正义与幸福那种可爱的一致吧。让我们以新的情操、新的知识来温暖他的心灵,来开导他的理性吧。如果我的热诚并没有使我盲目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有了正直感和强劲的灵魂,那个人类之敌最终便会放弃他的错误及仇恨,引他误入歧途的思想会重新把他带回到人道上来;他就会变得善良、有德、明智,他就能学会喜爱自己已经很好地理解到的利益远胜于自己的表面利益,最终就会形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最坚固的支柱,就会打造出一支他渴望形成的剽悍队伍。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献给日内瓦共和国的致辞
光荣的、尊贵的、至高无上的执政者们:
我深信祖国只接受高尚的公民呈上的敬礼,所以,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非常努力地工作,希望使自己获得这种荣幸,向您表达崇敬之情。这种荣幸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我努力的不足之处。我向来认为,赋予我这种荣幸的是我内心的热情,而不是权力。我有幸出生在这里,因而在我思考人们所创造的不平等和自然赋予人们的平等之时,不至于忽视其最高的智慧:在这个国家,这两者配合默契,完美地结合,以最有利于社会和最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式来维护公共秩序和保障人民福祉。在我研究了良知能为政府建制提供的最优法则之后,我为这一切都已经存在于你们的国家里而震惊。就算我没有生活在这里,我仍认为有必要把我描绘的这幅人类社会的图景献给你们,因为你们的政府在拥有了所有其他政府已经有的那些优点的同时,还能巧妙地避开它们的弊端。
假如我能选择我的出生地,我会选择一个面积与人们的智力相称的国家,这样它有可能治理得更好。在这里,人们彼此熟悉,无论是密谋犯罪还是谦恭美德都会得到人们的检视和裁决;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胜任自己的职业,而不必将自己的职责托付于他人。人们彼此相知的那种愉悦风气使得人们不是将热爱领土而是将热爱公民当做爱国。
我愿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人民和执政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一切政府行为都是致力于为公众谋幸福的,而这只能在执政者是人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我希望生活在英明的民主政府的管理之下。
我愿自由地生,自由地死。这意味着,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每个人都遵纪守法,都甘受这种光荣的约束。这种有益而且舒适的约束,就算是最高贵的人也愿意加诸己身,因为在它之外,他们不必再受任何其他的束缚。我希望,在这个国家外部,没有人能够命令这个国家屈从于他的权威;在国家内部,也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不管一个政府因何而设,在它的管辖范围内,假如有人不受法律约束,那么,其他所有的人就必然会受到这个人的任意支配。假如国内有一个统治者,国外也有一个统治者,那么不管他们如何分配权力,也不可能得到适当的服从,国家也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我不愿选择一个新成立的共和国,无论它的法律有多么卓越,新政府很有可能与当时的环境所需不符合,或是与它的新公民不相容,或是公民对它不满意,国家就存在刚一成立就发生动荡抑或被毁灭的危险。因为,自由就像那些营养丰富的食物和醇酒一样,对那些不适合它们的体质虚弱的人,就会摧毁他们的身体或者让他们沉醉,而对适应它们的强壮的人,则可以增加他们的营养,强健他们的体魄。人们一旦适应了主人就很难离开他们,即使已经挣开枷锁,他们也只会离自由更远,因为他们误把那种与奴役对立的过度的放纵当成了自由。
因此在革命之后,他们往往耽于享乐,他们身上只会被这些人套上更沉重的枷锁。即便曾是自由民族的榜样的罗马人,他们在脱离了塔尔干王朝的统治之后也没有自治的能力。因为奴隶制的压迫和塔尔干王朝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繁重劳役,使他们最开始时也只不过是一群暴民。只有最伟大的智慧才能管治他们,让那些曾在暴政下磨灭意志甚至变得冷酷无情的人们,逐渐习惯于呼吸健康自由的空气,培养英勇的精神,逐渐形成严格的道德约束,最终成为令人敬仰的民族。我愿为自己选择一个幸福而宁静的祖国,它以往的陈腐制度已经在久远的历史中磨尽;它所经历的动乱有助于显示和加强人民的英勇和爱国之情;它所有的公民因为长期习惯于独立决断,不仅值得拥有自由,而且已经是自由的。
我愿为自己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幸运之处在于它并不强大,不会产生残酷的征服欲望。更幸运的是,它处于的这种地位,能够摆脱被别国征服的困扰。它自由地生存在几个国家之间,每个国家都有兴趣保护它免遭其他国家的侵犯,而且不会有兴趣侵犯它。简而言之,这个共和国能在需要的时候合理地得到邻国的援助,却不会引起它们征服的野心。这样,这个共和国除了自身的发展之外没有其他的担忧,从而能安然度日。人们即使操练武器,也不是因为有保家卫国的需要,而是为了保持自由人所应拥有的英勇精神,和保持他们追求自由的品格。
我愿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立法权可以为所有公民共享,因为没人能比他们更清楚,在什么样条件下他们可以在一个国家里更好地共同生活。这并非是指我主张实行罗马的那种全民投票制,在那个国家,反而是有志于保卫国家的人和执政者被排斥在制定防卫政策的会议之外,并且因为种种荒唐的矛盾政策,地方法官反而不能享有普通人的那些基本权利。恰恰相反,我认为为了防止考虑欠周和牟取私利的政策,以及最终毁掉雅典的种种危险的革新,并非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地提出法律;应该只有地方法官专有提出法律的权力。在提出法律时,地方法官应慎之又慎,人民在认可法律时应三思而行,在公布法律时还应该郑重其事。那么,在新法把国家搅乱之前,人们就应该有充足的时间来确信,现有的法律不仅仅是因为历史悠久才具有神圣性,被人们尊崇。人们很快便学会了鄙视那些朝令夕改的法律,而政府一旦任由自己以改革为借口无视旧制,就往往会因小失大。
我应当特别避免选择一个治理混乱的国家,在这样的共和国中,人们要么相信他们不需要官员,要么只给官员一些不确定的权力,而由他们自己轻率地执掌法律,管理国内事务。这是雅典共和国衰落的另一个原因,这种形态的国家或许是刚刚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的原始政府的粗糙建制。我愿选择这样一个国家,人们乐于有权通过法律,在执政官的提议下,他们集体讨论重大的公共事务,建立高贵的法庭,认真划分行政区域,每年都选举最正直、最有才干的公民来掌管司法和治理国家。简而言之,在这个国家里,每个阶层都互相尊重,法官身上体现着的是公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