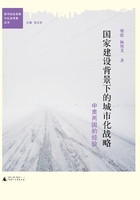因为一般来说,任何公共职务都不会执行得太坏,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需要像对一些部门中的高级官员强加以特殊职责那般为它规定巨大的个人责任。凡是不通过某种公开竞争的形式就任命的下级公务人员,应在各大臣直接负责的情况下选用。除了为首的大臣外,各大臣当然均由为首的大臣来选任;至于为首的大臣本人,虽然事实上是由议会指定,但在一个王国政府中就应由国王正式任命。有任命权的官员应当是唯一有权将应该予以免职的下级官员免职的人。绝大多数的官员,除开个人行为不端的原因之外就不应当被免职。因为,假如那些负责处理公共事务的所有细节,对公众来说其所具备的各种条件一般地比大臣本人要重要得多的人们,可能轻易地并非因为他们自己过错而随时被免职,大臣可以任命别的人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或者增加自己政治上的利益,那么要期望这些人为他们的职业献身并获取大臣往往必须依靠的那种技能和知识,就将是徒劳的。
对于不应当按照人民的选举来任命行政官员这一原则来说,共和政府中的行政首脑是否应该成为一个例外呢?美国宪法规定每隔四年由全体人民重新选举总统,这是否是一个好的制度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像美国这样不用担心政变的国家里,在宪法上使行政首脑独立于立法机关,从而让政府的这两大部门,在它们的职责和起源方面同样地得人心,同时又互相进行有效的牵制,毫无疑问具有某种好处。这一办法是为了设法避免大量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上,这是美国联邦宪法的一个显著特点。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好处是用高出对它的价值的任何合理估计的代价换取的。在共和国里,行政首脑公然由立法机关来任命,就像在君主立宪国家里,行政首脑事实上是由立法机关任命的一样,似乎要好得多。首先,这样任命的人必定是一个更加卓越的人。议会中掌控着多数的政党一般会任命它自己的领袖;他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站在最前面的人之一,并且往往就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与之相反,自共和国创建者的最后残存者在舞台上消失以来,美国的总统几乎一直要么是不出名的人,要么是在政治之外的某个领域有较高声望的人。如我以前所讲到的,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这种形势的必然结果。在遍及全国的选举当中,一个政党的著名人物向来不是该政党最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一切著名人物都结下了个人的政敌,或者做过某些事,或至少发表过某种见解,这就引起了社会某个地区或别的重要部分的不满,也许会对选票数目产生致命的影响;相对应地,一个没有什么经历的人,除声言信奉党的纲领之外,他人对他毫无所知,因而就容易获得该党全体的投票。
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不间断地为选举而奔波带来的巨大坏处。在国家的最高职位要通过每数年一次的普选来决定时,两次选举之间的全部时间实际上就将耗费在竞选运动当中。总统、政党领袖、各部部长和他们的追随者们都是参加竞选运动的人:社会的全部注意力都只集中于政治人物身上,每个公共问题的讨论和决定考虑的是它对总统选举所产生的预期影响,而不是问题本身的优缺点。如果要设计出一种制度,从而使党派精神成为所有公共事务中行动的支配原则,并诱使人们不但把每一个问题当成党派问题,而且为了给政党提供依据而提出问题,那就很难想出比这更符合这一目的的手段了。
我不想肯定地说,像英国的首相那样,行政首脑是完全由议会中的投票来决定这一方式在任何地点和时间都是值得期望的,而且没有不便之处。如果人们觉得最好避免这一点,那么行政首脑,虽然仍由议会任命,但可以不依赖议会的投票表决来产生,而在固定的期限内任职,这样一来,它就可以成为美国的制度,但却不包含普选和它的害处。还有另一种方式能赋予行政首脑对议会的很大独立性而不至于与自由政府的各要素产生矛盾。如果他像英国首相那样,事实上拥有解散议会和诉诸人民的权力,他就不会不恰当地依赖于议会的表决。要想不被敌对的表决赶下台,他就只能选择辞职或者解散议会。
在我看来,解散议会的权力是他应该拥有的权力,即使对他在确定时间内的任期有保障的制度下也是这样。不应当有在议会和总统之间爆发一场争吵后出现政治僵局的任何可能性,任何一方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都没有除掉对方的法律手段。要度过这样一段时期而双方或者任何一方都不策划政变,就必须要有很少国家曾表明可以做到的那种自我克制的习惯和对自由的热爱。即便除开这种极端情况不说,要期盼这两个权力机关不让彼此的行动陷入瘫痪中,就相当于假定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将始终渗透着互相妥协和忍耐的精神,保持镇静并不为最尖锐的党派斗争的激情所动。也许这样的精神是存在的,但是甚至在这种精神存在的地方,对它的考验也过于轻率。
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使我们期望国家中的某个权力(它只能是行政权)应当拥有在任何时候任意决定召集新议会的自由。当对究竟争执的双方哪一方拥有更多的支持者产生疑问时,最为重要的就是应该有一种宪政手段立刻进行检验并停止纷争。在这一点没有确定之前,就没有可能对其他的政治问题加以适当的注意。在这段时间内就行政或立法方面的改革来说,大多就是一种空白,因为对于自己的力量,任何一方都缺少足够的信心去作那些可能导致对现在的斗争有任何影响的人们所反对的事情。
我还未考虑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大权集中于行政首脑手上,而人民群众对于自由制度又没有足够的热爱之情,这样他就有可能在篡夺最高权力和破坏宪法的尝试中获得成功。在这种危险存在时,就不容许存在不能通过议会的一次表决就把他贬为平民的行政首脑了。在给这种对委托的破坏提供各种鼓励的最为大胆放肆的事态下,甚至宪法上的一切依赖关系也仅仅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保障而已。
在全部政府官员中,最不应该经人民选举产生的便是司法官员。尽管对所有官员的专业的和特殊的条件,群众都同样适合作出评价,然而在绝对公正和各派政客或不同政客产生联系方面,却没有任何官员能像司法官这样重要。有些思想家(包括边沁先生的)的意见是,尽管法官最好不由人民选举产生,但是在具有足够经验后,他们所属地区的人民应当有权罢免他们的职务。不可否认,受有重托的官员是不能被免职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无益的。人们非常不希望看到,一个没有能力的法官或者坏法官,除了因为他自己应对刑事法院负责的行为不端外,就没有办法将他免职,此外,一个关系重大的官员应该感到除了受他自己的良心和舆论的约束外就不需担负任何责任。但是问题是,从法官的特殊地位来看,假如采取了所有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保证对他的公正任命,那么仅使他对公众和自己的良心负责,整体说来,是否比对政府或公民投票负责更有希望保持他的行为端正呢?对行政部门负责这一点,经验早就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就对选民投票负责这一点来说,情况也是一样的。在选民的良好品质中,并未把对法官特殊要求的那些品质(即公正和冷静)计算在内。
幸好,在作为自由所不可或缺的民众选举中,这些也不是一定要具备的品质。甚至于公正的品质,虽然对一切人是必要的,从而也对所有选民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决定民众选举的因素。正如人们之间的任何交易一样,选举一个议会议员无须公正不偏。选民对任何候选人有权获得的东西无须作出裁决,也无须对竞选人的一般优点进行判断,他要做的只是宣布最得到他个人信任的是谁,或者最能代表他的政治信念的是谁。法官有义务像对待其他人一般来对待他最了解的人或他的政友;然而,如果一个选民这样做,那就会是愚蠢可笑和未尽到责任了。
和其他所有官员的情形一样,舆论对法官的道义裁判所造成的有益的影响,并不能成为任何论点的根据,因为即使在这方面,对法官(在他胜任司法职务时)的审判程序真正实行有效控制的,并不是(除在政治案件中偶尔的情形外)社会一般的舆论,而只是那部分能对他的资格和行为作出适当评价的公众——他自己法庭上的有关人们。我并不是想说一般公众参加司法是不重要的;相反,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以哪种方式来参加呢?应该是以陪审员的身份事实上履行一部分司法职务。人民直接地和亲自行动比假手于他们的代表更好,这是政治上极为少见的情况之一;这几乎是行使权力的人可能犯的错误比起让他对错误负责产生的后果更能忍受的唯一的一种情况。
假如法官可以由民众投票免职,那么但凡希望取而代之的人将为此目的利用法官作出的所有判决;只要他觉得可行,就将不按照规定程序把全部判决放在完全无能力的公众面前,因为公众没审理过案件,或者因为缺乏审案所必要的公正或警惕;他将利用民众可能会有的偏见和感情,或者尽所有力量激起这种偏见和感情。从这个角度而言,倘若案情引发人们的兴趣,而他又不辞辛苦,除非这个法官或他的朋友起来应战,从另一方对民众进行同样有力的呼吁,否则他确实会获得成功。到头来,法官们将感到在能引起公众普遍兴趣的案件上,他们所作出的每一个判决都可能使他们冒着失去职位的危险,并且他们会觉察到,对他们而言,最要紧的不是考虑哪种判决是公正的,而是考虑哪种判决最能得到公众的赞同,或者最不会留下恶意曲解的余地。美国某些修正的或新的州宪法所采用的由人民定期重新选举司法官员的做法,我担心会成为民主政治所犯的最危险的错误之一。倘若不是美国人民从未彻底抛弃的实际良知据说正在产生一种反作用,可能不久就能使这种错误得以消除,那就能够有理由认为它是现代民主制衰败中的大倒退的第一步了。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