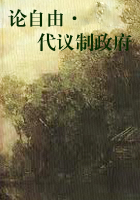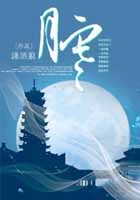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有天才的人,比其他任何人更不能适应社会为了省去其成员形成个人性格的麻烦而准备下的那些少数模子而不感到有伤害的压束,因为他们在字义的命定下比任何人都有较多个性。假如他们因怯懦而成为那些模子中的一个,听任其在压力下不能扩展的一切个人部分不予扩展,那么社会也不会因有他们而变好多少了。如果他们的性格太强,将身上的枷锁打碎了,他们就变成社会要压为凡庸而没能成功的一个标志,就像有人会埋怨尼亚加拉河(Niagara),怪它不像荷兰的运河受两岸的约束而平静地流去一样,以严正警告的意味指斥这些打碎枷锁的人为“野人”“怪物”以及诸如此类的称号。
我这样强调坚持天才的重要性,坚持必须让它在思想上和实践上自由舒展的必要性,我深知实际上几乎每个人都对它漠不关心,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人会否认这个立场。人们想,天才如果能使人画出一幅好画或者作出一首动人的好诗,那的确是很好的东西;但是一说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首创性,一说到它的真义,几乎每个人心里都在想,没有它,我们也能干得很好,即使没有一个人明说那不是什么可赞美的东西。不幸的是,这一点太自然而不足为怪了。无首创性的心灵是不会感到首创人生的用处的。他们看不到首创性会为他们做些什么——他们怎么能看到呢?假如他们能看到首创性会为他们做些什么,它也不成其为首创性了。把他们的眼睛打开,是首创性为他们服务的第一件事;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们便有机会使自己成为有首创性的人了。同时,人们都要记住,现有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首创性所结的果实,没有一件事不是由某一个人第一个做出来的;既然如此,那么就请大家都以足够的谦虚来提醒自己,自己愈少意识到缺乏首创性就愈多需要首创性;还请大家也以足够的谦虚来相信,这里还剩有一些事情要由首创性去完成。
说句清醒的真话,现在满世界中的事物的一般趋势是把平凡性造成人类间占上风的势力,不论怎样宣称对实在的或设想的精神优异性予以崇敬,甚至实际予以崇敬。无论在古代历史上,还是在中世纪间,以及以逐渐减弱的程度在由封建社会到当前时代的漫长过渡中,个人自身就是一种势力;如果他具有宏大的才智或者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他就将会是一种可怕的势力,但是现在,个人却在人群之中消失了。在政治上,若还有人说现在统治着世界的是什么公众意见,那他说的就几乎是废话了。只有群众的势力,或者是作为表达群众本能或群众倾向的机关的政府的势力,才是唯一实称其名的势力。这一点,在公众事务中和在私人生活方面的道德关系及社会关系中是一样真实的。有些人以公众意见的名义实施自己的意见,而这些公众并非总是同一类;在英国,他们所谓的公众主要是中等阶级;在美国,则只是全体白人。但他们却永远是集体中平凡的人们。
还有更怪的怪事,现在群众并不从公认的领袖那里或者书本当中,也不从教会或国家的贵人那里形成自己的意见。一些和他们很相像的人来代他们思考,那些人借一时的刺激,以报纸为工具,以他们的名义发言或者向他们发言,我并不是在埋怨这一切。根据一般的规律进行推论,我并不能肯定地说任何较好的事物都可以和现在人心的这种低下状态相容并立。但是那并不足以阻挡平凡性的统治成为平凡的统治。除非最高统治阶级中的多数人能接受具有较高天赋并有较高教养的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指导(他们在自己最好的时候总是这样做),否则一个民主制或多数贵族制的政府永远不会升高到平凡性之上,不论在它所培育的意见、品质以及心灵情调方面,或者是在它的政治行动方面。凡一切聪明的或高贵的事物最初也必出自某一个人,且其发端也必出自一些人。一般人的名誉和光荣,他能够从内心对那些聪明和高贵的事物有所反应,并且在清醒的状态下被引向它们,就在于他能跟随这个发端。
我决不是在鼓吹那种“英雄崇拜”,奖励有天才的强者以强力抓住世界的统治,使世界不顾自身而唯他之命是从。指出道路的自由是他所能要求的一切。至于强迫他人走上那条道路的权力,与一切他人的自由和发展相矛盾,并且对这个强者自己来说也足以使他腐化,看来,在当前这种一般群众的意见已成为或正在成为支配势力的情况下,平衡这种倾向的力量和矫正它的方法,就在于使那些在思想方面处于较高层面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发挥其断然的个性。在这种环境中,那种突出的个人应当受到鼓励去做,而不应当受到吓唬不去做与他人不同的行动。在其他时候,他们这样做,不仅要与他人不同,而且还要比他人好,才算有些益处。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仅仅是不屑苟同的一个例子,拒绝向习俗屈膝,就是一个贡献。怪僻性已经被意见的暴虐当成了一个谴责的对象,所以为了突破这种暴虐,人们的怪僻才更为可取。怪僻性在性格力量丰足的时候和地方同样丰足;在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与天才异禀、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一般成正比。表明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正是今天敢于独行怪癖的人如此之少。
前文讲到为了随时可以看到不合习俗的事物中有哪些事物宜于转成习俗,要尽可能给予这些事物以最自由的发展余地,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蔑视习俗以及独立行动之所以值得鼓励,不是说只有具有确定的精神优异性的人们才可以正当要求按照自己的道路生活;也不是只因为它们能够给较好的行动方式以及更加值得一般采纳的习俗提供脱颖而出的机会。没有理由说一切人类存在都应当在某一种或少数几种模型中构造出来。一个人只要保有一定数量的常识和经验,他自己所规划的存在方式就总是最好的,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是最好的。即使是羊,也不是只只一样而无从辨别的,况且人并不像羊一样。
一个人除非量了自身的尺寸来定做,或者有满满一堆栈的货来供他挑选,否则他是得不到一件合身的外衣或一双可脚的靴子的;难道说与给这个人一件合适的外衣相比,给他一个合适的生活更容易些,或者说与人们彼此之间在脚形上的相同比,人们彼此之间在整个物质的和精神的构造上的相同会多些吗?就像给他一个合适的生活比给他一件合适的外衣还容易些吗?只是人们具有多种不同的嗜好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不能试图用一个模子来铸造他们。而这不亚于各种各样的植物不能健康地生存于同一物质的空气和气候之中,不同的人也不能健康地生存于同一道德的空气和气候之中;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条件来发展其精神。一些事物,对于一个人在培养其较高本性方面是障碍,而对于另一个人则是助益。同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一个人会成为徒乱人意的负担,足以停滞或捣碎一切内心生活,而对于另一个人则是一种健康的刺激,足以使其行动和享受的一切官能得到最适当的应用。
人类中在痛苦的感受性上,在快乐的来源上,以及在不同物质的和道德的动作对于他们的作用上有如此多的不同,所以人类在精神方面、道德方面和审美方面就不能成长到他们本性能够达到的体量,也不能获得其公平的一分愉快,除非在其生活方式方面也相应地有如此多的不同。
这样看来,专就公众情操来说,有些生活嗜好和生活方式由为数众多的依附者强要他人勉从,为什么宽容还应当仅仅施及它们?当然,除了在某些僧院组织中,没有哪里会完全不承认嗜好的分歧:例如一个人可以爱好划船、抽烟、音乐、体操、下棋、打纸牌等事物,或是研究什么东西等,并不会受到什么责难,这是因为爱好和不爱好以上这些事物的人都为数太多以至于无法压倒。但是有些能被指控不为“尽人之所为”或是为“尽人之所不为”的男人或女人——女人尤其如此——仍然是众所贬议的话题,贬议的程度就好似犯了某种严重的道德过失一样。人们需要拥有品位(或他人对于品位的看法)上的某种标志,或者拥有一个尊号,才能稍稍为所欲为但是不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对于稍稍为所欲为,我重复一句,因为不论何人若多有一点那种为所欲为,就要遭受到比贬词还厉害的危险——他们竟处于可能被判定精神错乱而被夺去财产,并将其财产交付给他们的亲属的危险境地呢。a
当前公众意见的方向中有一个特别适于使它不能宽容个性的任何显著表现的特点。人类中的中材一般在智力和意向方面是平庸的:他们并不希望做些什么不平常的事,因为没有足够强烈的嗜好或愿望驱使着他们,因而他们也不理解有那种嗜好和愿望的人,而径直把那种人划归到他们向来鄙视的野性难驯和不知节制的一类。现在,我们只需在这个普遍的事实上面,再设想插进来一个旨在改进道德的强烈运动,而这明显是我们所必须期待的。在这些日子里,果然插进来了这样一个运动,它已经实际在加重挫折行为过度性、行为规则性的道路上作出了很多成绩。而同时为了实施一种慈悲为怀的精神,与改进我们同胞的道德和智虑这件事相比,自然没有别的事更能招徕它了。公众比在以前多数时期中更加倾向于指定行为的普遍规律,并力图使每个人都适合于被认可的标准,这一切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趋势。而这个标准,不管是不言而喻,还是明言昭示,其目的都是要对任何事物都不存强烈的欲望。其性格的理想是要没有任何显著的性格;是要用压束的办法,斫丧人性中每一点突出特立的部分,把在轮廓上显有异征的人都造成平庸之辈,就像中国妇女裹脚一样。
既然理想常把可取的事物一半排除在外,那么现在的嘉奖标准就只能对那另一半产生一个更次的模仿。这个嘉奖标准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微弱的情感和微弱的精力,而在良心意志有力控制之下的有力情感没有了,在有力理性指导之下的宏大精力也没有了,这当然就能保持表面上合乎规律而内在没有任何意志的或理性的力量。富有精力的人物在任何宏大的规模上都已经变成仅是因袭性的了。精力在现在这个国度里很少有什么出路,而生意则刚好相反,花费在它上面的精力还可以说是很可观的。这样某种日常爱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