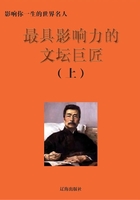反对暴政的人,只要还有家庭情感就一天也不会孤立无援,他的周围有他的近亲、世交和追随者。就算没有这种支持,他的后代也将接替他的事业,他也会感到祖先在督促他前进。然而,当种族的差别不久就要消失,祖传的家业日益分散的时候,又到哪里去寻找家庭情感呢?
在一个不断改变面貌或已经完全改变面貌的国家,假如它的一切暴政都有先例可援,一切罪行都是例行公事,现存的古老事物消亡而没有人感到惋惜,凡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新鲜事物人们都敢去尝试,那么,它的习惯法还有什么力量呢?屡遭践踏的民情又能提供什么抵抗力呢?
当没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阶级、一个自由结社可以代表和鼓动舆论时,当没有一条共同纽带将这么多人联系在一起时,这个舆论又还能有何用呢?
当每个公民都一样无能,一样贫穷,一样孤立无援,且仅能以个人的软弱去对抗政府的有组织的暴力时,舆论又会有何用呢?
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预见到的是国家在某些方面是否会出现类似局面。也许我们应当回顾可怕的罗马暴政时代,追溯古代的史实。在那个时代,意志动摇,传统中断,习惯腐败,风气颓废,自由被法律破坏而无容身之地,人性被人玩弄,公民不受保护也不能自保,君主不再开恩而是强迫臣民逆来顺受。
在我看来,只有那些神志已经不清到了极点的人才希望复兴亨利四世或路易十四的君主政体,至于我,当我预见一些国家将要达到的状况和看到许多欧洲国家的现况时,我就情不自禁相信它们很快便会作出抉择:不是走向专制者的暴政,就是走向民主的自由。
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假如面对这项抉择的社会统治者不是逐渐将群众提高到他们的水平就是让公民降到人的水平之下;假如人们将来不是全部自由就是全体被奴役,不是全都拥有平等权利就是权利全被剥夺,那么,只要坚定信心,战胜疑虑,教育每个人自愿作出巨大的牺牲,这不就已经足够了吗?
所以,难道不应当认为逐渐发展民主的民情和政治制度,是使我们自由的唯一而且最好的手段吗?其次,假如不喜欢民主的政府,又怎能把它作为医治目前社会弊病的最好和最适合的药剂而加以利用呢?
让人民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非常难,而让他们拥有管好国家的意识和积累管理的经验则更难。
我承认,民主的意向是常变的,它的法制还不完备,它的执行者还不精干。然而,假如在独夫的压迫和民主的统治之间确实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与其自暴自弃地屈从于前者不如倾向于后者,并且,如果我们必然最后变得完全平等,那么,让自由把我们拉平比让一个暴君把我们拉平要更好。
假如读过我的这本书之后,有人断定我写此书的意图就是让已经具有民主社会情况的国家仿效英裔美国人的民情和法制,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读者没有认识到我的思想的实质,而只注意到外表。我的目的是以美国为例来说明:法制,特别是民情,能让一个民主的国家保持自由。可我不认为我们应当照搬美国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照抄美国提供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一个国家的历史和自然环境,同样对它的政治制度会产生某种影响;并且,假如自由要以同样的面貌出现于世界各地,我还认为那是人类的一大不幸呢。
可是我觉得,假如我们不向全体公民灌输那些使他们首先懂得自由和随后享用自由的思想和感情,不逐渐采用并最后确立民主制度,那么,不管是贵族还是有产者,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谁都无法独立自主,暴政就将统治所有的人。我还能够预见,假如我们不及时建立绝大多数人的和平统治,那么我们迟早会陷于独夫的无限淫威之下。
注释
[1]虽然美国还没有大的首都,却已有一些很大的城市。1830年,费城已有居民161000人,纽约已有居民202000人。居住在这些大城市的下层人民,是比欧洲的贱民还要危险的一群人。这群贱民大部分是被解放的黑人,法律和舆论都将他们看做卑贱和世代贫困的居民。其中也有很多由于运气不好或行为不轨而被赶到新大陆的欧洲人,他们将我们欧洲的一些恶习带到美国,也不想放弃这些恶习。定居在这片国土时,他们没有公民资格,因此准备为所欲为,以便从中捞到好处。所以,从某个时期以来,我们便看到费城和纽约时常爆发恶性的暴乱。然而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这种暴乱,这便没有让社会感到不安,由于城市的居民到现在还不能对乡村的居民产生任何影响。然而,我认为美国某些城市的豪华壮丽,尤其是这些城市居民的性格,是对新大陆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未来构成威胁的真正危险;而且我敢预言,除非政府建立一支随时准备支持多数的意旨,能够保护城市居民的自由并能镇压他们的暴力行为的武装力量,某些地方的民主共和制度便将会因为这一危险而寿终正寝。
[2]在新英格兰,土地就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分散在农户手里,然而已不能再往小分割了。
[3]下面是1831年8月23日《纽约旁观者报》对此事的报道:“切斯特县(属纽约州)民事法庭,几天前斥退了一位宣称自己不相信上帝存在的证人。法庭的庭长指出,在没有作证以前,他就说他不相信有真上帝存在;如此的声言等于对法庭上的所有证言的惩罚,而且他也清楚,在信奉基督教的我县,不允许不相信上帝存在的证人为案件作证。”
[4]不包括他们大部分人在学校里担任的职务。美国的大多数学校是由神职人员建立的。
[5]见《纽约州宪法》第七条第四项。见《北卡罗来纳州宪法》第三十一条。(托克维尔所引系1776年宪法)见《弗吉尼亚州宪法》。见《南卡罗来纳州宪法》第一条第二十三项。(1790年宪法)见《肯塔基州宪法》第二条第二十六项。(托克维尔所引系1799年宪法)见《田纳西州宪法》第八条第一项。(1796年宪法)见《路易斯安那州宪法》第二条第二十二项。《纽约州宪法》有关的条文如下:“鉴于神职人员以服务上帝和拯救灵魂为主要职责,且不得松懈,所以任何教派的神职人员或教士……都不得或不能在州里出任任何文职或军职。”(1821年宪法第七条第四项)
[6]我曾乘坐过一种两轮无棚的马拉驿车,去过美国的部分边远地区。在无边无际的林海里,我们开辟出的道路上,驱车疾驰了一个昼夜。我们的向导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燃起一束松枝,用火光引导我们继续赶路。在走了很长一段路程之后,我们才遇到一所位于森林深处的木房。这是个驿站旅店。邮件押送员卸下一大包信件,放到这所孤零零的房屋门口。我们便又继续登程,让这附近的居民来取他们最期盼的东西吧!
[7]1832年,法国诺尔省平均每个居民支付的邮费为1法郎4生丁(见《1833年法国政府决算》第623页)。这一年,佛罗里达州平均为1法郎5生丁,密歇根州每个居民平均支付的邮费支为1法郎22生丁(见《1833年美国大事记》第244页)。然而,在这一时期,密歇根州的人口密度每平方里约为7人,佛罗里达州为5人,而这两个州的实业和教育却不如美国大部分州发达,可是在法国工业最发达和文化最高的省份之一的诺尔省,每平方里约则有居民3400人。
[8]在这里,我烦请读者回想一下我所说的“民情”一词的一般含义。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我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