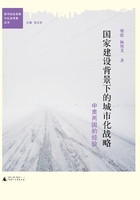任何力量越被集中使用于一个方向,它的效果就越大。这条普通自然规律已经被实验向观察者证明,而一些微不足道的暴君,也利用他们的比实验更为可靠的本能,一直感到这个规律在发挥作用。
在法国,报刊兼有两种不同的集中。
首先,报刊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个地点上;其次,可以说是集中在几个人手里,因为它的机构数量很少。
用这种方式在一个人人多疑的国家建立起来的权力,就会产生接近无限的影响力。它一般与政府为敌,政府或许能跟它达成或长或短的休战协定,但要和它长期共处却是很难的。
我方才提到的两种集中,在美国则一个也不存在。
美国不存在大城市,人力和物力在广大国土的各处呈分散状分布,人类智慧之光是在各地交互辉映,而不是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向四外散射。在任何方面,美国人都没有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的习惯。
这一切表现都要归因于美国的地方环境,而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法律在这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在美国,既不要求报刊进行注册,又不向印刷业发放执照,更不知保证金是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里创办报刊既简单又容易,只要有不多的订户,就足以应付报刊的开销,因此美国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种类多得令人不敢相信。一些很有教养的美国人,认为这种出版力量的过度分散就是导致报刊影响力小的原因。所以,美国政治学有一项原理:增加报刊的样数是冲淡报刊影响的唯一办法。我真不明白,如此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为什么还没有在我们法国推广?我很容易理解,那些想凭借报刊进行革命的人,要使报刊界只存在几个强大机构的意图。然而,为什么现存秩序的官方维护者和现行法律的天然支持者,他们会相信把报刊集中起来就可以减弱报刊的影响力?这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了。我认为,欧洲各国政府用来对付报刊的办法好像和中世纪骑士对付敌人的方法一样:它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集中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而它们把武器提供给自己的敌人,就是为了在对抗敌人时取得更大的光荣。
在美国,基本上每一个小镇都有自己的报纸。在这么多的斗士中间,要想建立秩序和统一行动是不可能的。结果现状就是,每个人都独树一帜,各显本领。在美国,不会出现所有报纸联合起来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情况,而且它们在攻击政府和为政府辩解时总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报纸在美国很难汇成能够冲击或冲垮牢固的大坝的洪流。报刊力量的这种不集中,还带来了另外一些十分明显的后果:一方面,在美国办报很容易,因此人人都可以办报;另一方面,因为存在竞争,任何报纸都很难获得巨大的效益,致使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在此类事业面前止步。最后,即使办报是生财的方法,然而因为报刊的数量过多,有天才的文人也不容易致富。所以美国的报人基本上地位都不高,受的教育较低,思路不敏。众所周知,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多数决定一切,由多数制定每个人应该遵守的行动守则。把这些共同习惯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宗旨。于是就因此产生了律师业的宗旨、法院的宗旨等。在法国,报业的宗旨是,用猛烈的,然而又高尚并经常是雄辩的方法探讨国家大事。偶尔没有经常这样坚持下去,那只是证明所有的规律都有例外。而美国报人的宗旨是,用粗暴的、十分朴实的、直奔主题的方式刺激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情感,而不用道理让人悔悟,甚至不惜攻击人家的隐私,揭露他们的弱点和毛病。
我们应该对这样滥用思想自由的做法表示惋惜。我以后还有机会来谈报纸给美国人民的爱好和道德造成的影响,但我现在的题目是只谈政界,因此对这种影响只能顺便说一下。必须承认,对出版界采取这种放任态度的政治效果,曾对维持公共安宁有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为了避免失去他们为了自己利益而去鼓动大众激情的最强有力武器,已在同胞们的思想里占有地位的人都不敢在报纸发表文章[1]。从这可以看出,报上发表的个人意见,在读者的眼里通常是一点都不重要的。读者想从报纸看到的是有关事实的报道。只有在报道改变或歪曲真相时,撰稿人的观点才会发生某种影响。
虽然报纸只能做到这些,然而它在美国依旧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权力。它使政治生活的信息在这个辽阔国家的各地传播。它常常瞪着眼睛不断地对政治的秘密动力进行观察,使搞政治活动的人被依次推上舆论的法庭。它会把人们的注意力集结到某种主义或学说的周围,并给政党树立了旗帜。它令那些彼此对话,却没见过面的政党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从而能够不断接触。当大量的报纸行进在同一道路上时,久而久之,它们的影响就会变得几乎无法抗拒,即使一直被另一个方面控制的舆论,最终也会在它们的打击中屈服。
在美国,每一家报纸都各有一点权力,而期刊的权力比报纸的还大,仅位于最有权威的人民之下。(A)
在美国出版自由的环境下形成的见解往往比在其他地方受检查制度影响形成的见解更坚定
在美国,政坛新人永远不断地出现并被民主制度推出去管理国家事务,因而政府的施政难以始终如一和按部就班。然而,该国政府的总方向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却显得更为稳定,而支配社会的主要舆论同样比其他国家持久。当一个思想占领了人们的头脑之后,无论它是否合理,再想把它从头脑里赶走就很困难了。
同样的事实在欧洲的英国也出现过。在过去一百多年中,这个国家曾存在过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大的思想自由和更牢不可破的偏见。
在我看来,这个现象应该归咎于那个貌似有责任阻止这个现象产生的事实,即出版自由。在实行这种自由的国家,高傲和自信对见解的影响程度完全相等。人们会喜欢一种见解,是由于这一见解在他们看来是正确,并且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会支持一种见解,不只是由于它是真实的,更是由于它是属于自己的。
此外还有另外的几个原因。
一位伟人讲过:无知处于知晓的两端。不过如果说自信处于两端,而怀疑居于中间,也许更为正确。事实上,人类的智力发展可以被认为有三个总是前后相连的不同阶段。
这三个阶段表现为:一个人先是对某事坚信不疑,此时他往往是由于没有深入调查便接纳了它;当异议产生时,他便会产生怀疑;最后,他一般会克服所有的怀疑,从而又开始相信。而他在后一次去认识真理时便不是随随便便和马马虎虎的,而是切切实实地去考察真理,并紧随真理之光行进[2]。
当出版自由发现人们位于智力发展的首个阶段时,它不得不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听任他们遵循自己不经深思熟虑就坚信不疑的习惯,只能试着渐渐地改变他们轻信的对象。所以,在整个智力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只能一次认识一点地往前发展,然而被认识的那一点也在不断改变。最早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正值爆发革命的时期,于是,他们就要有点苦头吃了!
不久之后,一批新的思想又紧接着出现。人们因为有了以往经验,便在怀疑和普遍不信任中探索。
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总是停留在以下两个阶段之一:一个是相信却不知道是为什么,另一个是不能确知该信什么。
只有很少人有能力达到拥有来自真知的深思熟虑的自信,能够冲破怀疑的干扰,并主宰这种自信的那个阶段。
然而,也有人曾经指出,在宗教狂热鼎沸的时代,人们还可能改变他们的信仰,但在人们普遍怀疑的时代,人人却对自己的信条坚信不疑。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出版自由盛行时的政治中。在互相质疑和轮番角逐的所有社会理论中,如果有一个被人采纳并给予保护,也只是因为人们不相信会有比它更好的,而不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好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不会轻易为自己的见解付出生命,然而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见解。所以,殉道者和变节者都一样少见。
再给这个理由增加一个更加强而有力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时,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比见解更容易看到、感觉到,也更能持久,所以人们最终总是要通过自己的本能和物质利益来判断。
民主制度的治理与贵族制度的治理相比,究竟哪个好?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民主制度会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而贵族制度则会使另一些人受压迫。你富了,我就穷了——这是一个真理,并且它自行成立而且无须讨论。
注释
[1]他们只会在向人民呼吁和表达自己的见解的极少数情况下,如在答复恶意的诽谤和解释事实的真相时,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2]不过,我还不知道这种深思熟虑的自信和对这种自信的主宰,是否曾经通过理性信念的鼓舞把人的热心和信心提高到一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