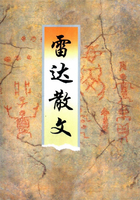寻找遗体
我和中士侦探里托尔坐在厨房里,里托尔小口喝着咖啡,我生硬地对他说:“我是公民,是纳税人,你们破坏性地搜查我的财产,必须原封不动地给我恢复原貌。”
“放心吧,华伦先生,政府会把一切摆得像苹果馅饼一样整齐的,”他微笑着说,“无论找到与否。”
当然,他要找的是我妻子的尸体。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找到。
“中士,这可够你们花大功夫修理的了。你的人实际上已经把我的花园掘了,前边的草坪就像被犁翻过一样。显然你们是在拆我的房子,一点一点地拆。我看见你的人已拿着气锤到地下室去了。”
他仍然满怀信心地说:“美国的领土是三千零二万六千七百八十九平方英里,包括水域。”
里托尔在这样的情况下准确记忆起了这个数字。
我尖刻地问:“包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吗?”。
他没有生气,镇静地说:“我想不包括。正如我之前所说,美国总面积是三百零二万六千七百八十九平方英里,包括高山、平原、城市、农田、沙漠、河流。当一个人杀害了他的妻子时,他一定会把她埋在自己的私有领域之内。”
我想:这当然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把妻子埋在树林里,一些调皮的童子军在挖箭镞时就一定会发现她。
里托尔又一次笑了笑问道:“你的这块地多大?”
“六个英尺宽,一百五十英尺长。没看出来吗?我利用好多年的时间把我花园的土壤改造得多么肥沃。现在被你的人翻动了,能看到到处都是一片片的黄土。”
他已经来了两个小时,仍然坚信自己能成功找到尸体:“华伦先生,恐怕还有比花园土壤更让你担心的事情。”
通过厨房的窗户能够看到后院,八九个民工在警察的监督下,正在把平地挖成一道道的地沟。
里托尔看着他们说:“我们干得很彻底,我们将分析你烟囱中的烟灰,过滤你火炉中的炉灰。”
“我用的是油炉。我没有杀害我妻子,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 我加了些咖啡。
里托尔也给自己加了些糖:“那你如何解释她的失踪?”
“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夜里,爱米莉简单地整理了一下行李箱就走了。你不是也看到了吗?她的一些衣服都不在了。”
“我怎么知道她有哪些衣服?”里托尔看了看我提供给他的我妻子的照片,“没有什么恶意,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和她结婚?”
“当然是为了爱情。”我说。
显然这样说很可笑,中士也不会相信。
“你妻子投保一万美元,你是受益人,是吗?”
“是的。”保险金当然是她死亡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我最初的动机。我抛弃爱米莉的最真实的原因是我再也忍受不了她了。
我是有苦难言,和她结婚时我处在高度的痛苦之中。我相信自己步入结婚礼堂,主要是因为自己屈服于一种从众心理,认为过久的单身就等于犯罪。
爱米莉和我都在马歇尔造纸公司工作,我是高级会计师,她是个没有任何前途的打字员。
她朴素、寡言、温顺,不知道如何打扮自己,谈话内容从来没有超出过对天气的寒暄,每天依靠阅读报纸来增长些见识。
简单地说,她觉得婚姻必须依靠安排,她自己不可能成为浪漫的人的理想的妻子。
但最令人惊奇的是,婚姻竟将一个朴素、寡言、顺从的女人变成一个十足的泼妇。
“你和你妻子相处得如何?”
我说:“我们各有各的特点,难道人人不都是如此吗?”但实际是我们相处得很糟。
“据你的邻居们说,你和你妻子总是不断地吵架。”看来中士已经从周围人那里了解到了许多高级机密。
邻居,他指的肯定是福勒德?特立勃夫妇。自从我有了一块土地后,他们的房屋是我隔壁紧挨着的唯一的房屋。我怀疑爱米莉的声音是否会传到花园和小路那边的摩利森家,应该不可能。
“特立勃家能听到,你和妻子几乎每天晚上都吵架。”
“只有当他们停下他们自己家的尖叫,专心来听的时候才会听到。他们说听到我们俩吵架,这一点不符合事实,我从来没有提高过嗓门。”
“最后一个见到你妻子活着的目击者说是星期五晚上六点三十分,当时,她走进了这所房子。”
是的,她从超级市场回来,带着冰冻晚餐和冰淇淋,这些是她仅有的一点对烹饪艺术所做的贡献。我自己做早餐,在公司咖啡店用午餐,到了晚上我要么自己做晚餐,要么吃些需要花费四十分钟才能做成的东西。
我说:“那是其他所有的人见到她的最后一次,不过我那天晚上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我们就寝的时候。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就发现,她已经收拾行李走了。”
楼下,气锤已经开始破坏水泥地板,噪音太大,我不得不关上通往地下室的门,我问中士:“除了我,到底谁是最后一次见到爱米莉的人?”
“福勒德?特立勃夫妇。”
威尔玛?特立勃和爰米莉十分相似,她们在婚后都变成了大女人,脾气如悍妇,心眼似针尖。福勒德?特立勃是一个小男人,两眼总是泪汪汪的,或者说他本来就是这样,或者说婚姻将他这磨成了这样。但是他棋下得非常好,并且非常欣赏我天生的固执与坚强,因为这是他所缺少的东西。
里托尔中士说:“就在那天深夜,福勒德?特立勃听到从这座房子里传出了可怕的惨叫声。”
“可怕的?”
“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平静地说:“福勒德?特立勃在说谎,看起来他妻子一定也听到了?”
“那倒没有。她睡得很死,但是惊醒了福勒德。”
“这所谓的可怕的惨叫声惊醒了摩利森一家吗?”
“没有,他们也睡着了。他家离这座房子相当远,而特立勃的家离这里仅有十五英尺。”里托尔装满一斗烟,接着说:“福勒德?特立勃想叫醒妻子,最后却决定不叫她了。似乎她脾气不好。但是他却无论如何再也睡不着了,早上两点钟,他听到你的院子里有动静,就走到窗子旁。趁着月光他看到你在花园里掘地。最后他起了床,紧张地叫醒妻子。两个人都看到了你。”
“这两个可耻的间谍,你们就是这样了解的情况?”
“是的。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箱子?”
“我只有这一个,但无论如何也不够一个棺材的尺寸。”
“特立勃夫人整个星期六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当你告诉她说你妻子出去旅游了,过一段时间才会回来时,她终于肯定你是把妻子的尸体装进一个袋子掩埋了起来。”
我又给自己加了点咖啡:“好啦。你们找到什么没有?”
他仍然有些尴尬:“一只死猫。”
我点点头,说道:“所以我是犯了埋葬死猫的罪行。”
他微微一笑:“华伦先生,你很会找借口。一开始你不承认自己埋过什么。”
“我觉得这和你们的事无关。”
“我们找到死猫后,你宣布它属于自然死亡。”
“当时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猫是你妻子的宠物,很明显头骨是被敲碎的。”
“我没有验猫尸的习惯。”
他吐了一口烟,又说:“根据我的理论,你杀掉你的妻子之后,又杀了猫。可能是因为它的存在使你忘不掉你的妻子,或者可能是因为这只猫看到了你处理你妻子尸体的情况,可能会把我们引到……”
“讲下去,中士。”我说。
他脸一红:“众所周知,动物会到处去挖寻埋葬它们主人尸体的地方。通常,狗就是这样,我承认。难道猫不是这样吗?”
我事实上也这样想,难道猫不是这样吗?
里托尔听到一阵气锤的响声:“当接到报告说有人失踪了,我们通常的程序是通过寻人公司发出寻人启事,然后就等待。过上一两个星期后,失踪者一般总会回到家里。一般都是在他花光钱之后。”
“那么你们究竟为什么不对这个案子那么处理?我确信爱米莉几天后就会回来。据我所知她只带了一百元左右,我知道她非常害怕自立和无助。”
他微微一露牙齿,说:“当我们听说有人丢了妻子,又有人听到了惨叫声,两个证人在神秘的月光下看到有人在花园里掩埋什么,于是我们就确认这是犯罪,我们当然不敢怠慢。”
我也不敢怠慢。因为,爱米莉的尸体不可能长久保存,所以我就杀了那只猫,尽量让人看到我在掩埋一个箱子。我尖刻地说:“于是.你立即就抓把铁锨来破坏我的私人财产了?我警告你,如果有一根柱子、一块砖瓦、一块石子、一片土没有按原样放好,我就起诉你。”
里托尔镇定自若地说:“但是在你客厅的地毯上有血迹。”
“告诉你,那是我自己的血迹。我不小心摔碎了杯子,刺破了手。”我再次让他看了看痊愈的伤口。
他没有被此话打动:“我看你是为了掩饰那些血迹而进行自伤。”
他说得很对,当然是这样。不过我还是想让地毯上的血迹少—些,不引起警察的搜查。
这时我看到福勒德?特立勃倚在栅栏上看着里托尔的人在搞破坏。于是我站起身,我要去和那些畜生们谈一谈。里托尔也跟着我走了出去。
我沿着土堆走到栅栏旁,对他说:“像你这样的也叫做好邻居吗?”
福勒德?特立勃长出一口气,说:“阿伯特,我并不想中伤你。我不认为你真的那样做了,不过你知道威尔玛那个人,她充满想象力。”
我瞪着他:“以后咱俩再也不要下棋了。”
我转脸对着里托尔说:“是什么叫你如此积极,认为是我杀害了我的妻子。”
里托尔将烟斗从嘴上挪开:“还有你的车,星期五下午五点三十分,你开车到慕雷大街伊格尔加油站,将车子加了油。工作人员把通常的标记条贴在车门内侧的门边上,表明何时加油,表明里程表上的里数。你的里程表上增加的里数只有十分之八里。那是从加油站到你家车库的确切距离。”他笑了笑,“换句话说,你直接开车回到家里,并没有在星期六去上班,而今天是星期日。自星期五以来你的车没有动用过。”
我一直希望警察们能注意到那个标记,如果他们没有注意到,我还打算以某种办法来诱导他们注意。我淡淡地一笑:“你想没想过有这样的可能性,我把她转移到附近的某块空地里埋掉了她。”
里托尔宽容地咯咯—笑:“最近的一块空地距这儿也有四个街区那么远。你能背上她的尸体在深夜里穿过大街走那么远?简直不可想象。”
特立勃把眼光从我花圃中的那些人们身上移开,说:“阿伯特,无论如何你的大丽花是要被挖掉的,我用我的琥珀巨人换些你的大丽花,怎么样?”
我向后一转,走回屋子。
下午的时间被一点一点地糟蹋了,当听了人们的汇报后,里托尔脸上的自信也不见了。
天色黑下来,六点半的时候,地下室的气锤停下来。
奇尔顿中士来到厨房,他又累又饿,看起来很颓唐的样子,裤子上全是灰土:“下边什么也没有,绝对什么也没有。”
里托尔拿下烟斗,说:“你敢肯定各处都搜到了吗?”
“我拿我的生命打赌,如果这儿有尸体,我们肯定会找到的。外面也彻底搜查了。” 奇尔顿说。
里托尔瞪着我:“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你杀害了你的妻子。”
我有点悲哀,一个平日里很聪明的人竟然退却到要凭直觉办事。但无论如何,在这个案子里,他的直觉是正确的。
“我想,今晚要给自己做鸡肝炒洋葱吃,”我兴奋地说,“好久没吃过了。”
从后院来了个巡逻兵:“中士,我刚刚与他的邻居特立勃谈过话。”
“有什么情况?”里托尔焦急地问。
“他说华伦先生在本地区拜伦县的—个湖畔有—套夏日别墅。”
我差一点把正从冰箱里取出来的一袋鸡肝掉在地上,这个喜欢泄密的傻瓜!
里托尔睁大眼睛,幽默不见了。他咯咯一笑:“好的!我就说他们总是要把尸体埋在自己的领域内。”
可能我的脸色是苍白的,我吼道:“你胆敢踏上我的地盘。我买下那座房子后花了两千元的装修费来装修,绝不能让你们去糟蹋它。”
里托尔哈哈一笑,说道:“奇尔顿,去找些泛光灯来,集合全体人员。”他又转过身对我说:“现在,看你如何解释?”
“我坚决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你知道,我不可能去那儿。你忘记了,我车上的里程表表明,自星期五下午以来我的车没有离开过车库。”
他越过这一障碍:“但是你可能把里程表倒了回去。你的别墅位置在哪儿?”
我抱着双臂:“我拒绝回答。”
里托尔微微一笑:“你没有必要拖延时间。还是你想在今天夜里亲自溜到那儿去,把她掘出来.再换个地方埋起来?”
“我没有那样想。我坚持自己的合法权利,什么也不会说的。”
里托尔用电话通知巴拜县的警官开始行动,在四十五分钟内他准确地定位了我的别墅位置。
他最后一次放下电话时,我马上说:“我告诉你,你不能像在这儿一样把我那个地方也搞得一塌糊涂。我现在就给市长打电话,看看能不能解你的职!”
里托尔很幽默,他搓搓手,很实际地说:“奇尔顿,明天派一批人来,把一切按原样整理好。”
我跟着里托尔走到门口,还在不停地争论:“要是伤了我一株花,一根草,我就叫我的律师给你好看。”
那天晚上,我对鸡肝炒洋葱不感兴趣。
到了八点半,后边有敲门声,我打开门。是福勒德?特立勃,他看起来很后悔:“对不起。”
“你到底是怎么提起别墅的?”我生气地问。
“我只是在谈话,谈着谈着一下说漏了嘴。”
我难以控制胸中的怒气:“他们要去破坏那个地方,我刚刚费力地开辟了一块草坪。”
我本应继续大发一通脾气,但是我说服了自己,问他:“你妻子睡了吗?”
福勒德点点头说:“她到早上才会醒来,从来没在夜里醒来过。”
拿起帽子和上衣,我们到了邻居福勒德家的地下室。
爱米莉的尸体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上面盖着一块帆布。我觉得这是—个相当好的临时藏尸处。威尔玛除了在洗衣服的那天,其余时间从来不到这儿来。
福勒德和我把爱米莉的尸体移回到我的房子,搬进地下室。这地方看起来像个刚打完仗的战场。
我们把爱米莉丢进最深的一个坑,盖上了一尺半厚的石土和垃圾。我们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福勒德看起来有点担心:“你确信他们不会找到她?”
“当然找不到,最好的藏物处就是有人找过的地方。明天就会有人来填平所有的地坑,整平所有的地面。”
我们上楼来到厨房。
“我还得再等一年吗?”福勒德直截了当地问我。
“当然,我们不能再引起怀疑。过一年左右,你就杀死你的妻子,然后我把她放到我的地下室里,等着你的房屋被搜查后再移回去。”
福勒德叹了口气:“还得和威尔玛在一起等那么长时间,不过,我们掷了硬币,猜正反面时你赢了。”他清清嗓子又说,“阿伯特,你刚才说的不是真话吧?”
“什么真话?”
“你说再也不和我下棋了?”
一想到警察此时很可能正在破坏我的别墅和花园,我就想告诉他那是真话。
但是,他看起来的确有点可怜,有点内疚。于是,我叹了口气说:“当然不是。”
福勒德红光满面地说:“哈哈,我这就去拿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