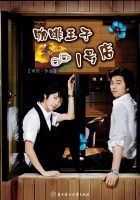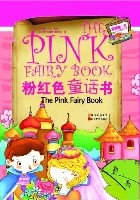“女人的心事是装在透明玻璃瓶里的水,明明满满的,却好像什么都没有。”
“唐漪,我拜托你,在他走之前,告诉他吧。”BASRUI咖啡吧里,陆希娅搅拌着一杯清苦的巴西咖啡。咖啡杯上印着经典的意式花纹图案,高雅而纯粹。
“告诉什么?”唐漪皱着眉,蜷缩在咖啡吧的沙发里。她面前的咖啡一口没动,咖啡上面浮着的奶泡,细腻而轻盈,却在慢慢冷掉。
“告诉他你喜欢他,留住他,不让他离开。高考都结束了,你不用再找专心学习当借口了。”
“陆希娅,如果失败,我会活不下去。”
“有多少人,是因为害怕告白的失败,而错过了本可以相伴一生的爱情。”
“他父母在国外,他迟早会离开。”
“你真的不准备去跟他告别吗?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见到他,可能再也见不到了,真的没关系吗?”
“我去不去,都改变不了结局。”这句话伴着唐漪厌世的眼神和悲春伤秋的语调,在咖啡吧的爵士乐中,显得尤为无奈和世态炎凉。
“你总是给自己放狠话,也就只敢给自己放狠话。”
“狠话,也许是良药呢。”
“没准你得的是绝症。”
“真没良心。”唐漪把身子换了一个看不见陆希娅的方向。
“唐漪你知道吗,你在我面前没提过第二个男人。”
“或许,他不过是颗……闪着耀眼光芒的流星。”咖啡匙碰到了瓷杯,唐漪笑得毫无感情。轻轻抿了一口咖啡,冷冷的、苦苦的、酸酸的、说不出的味道。“我会铭记他的。”她终于得以把想说的话吐露出来,然后自顾自地点点头。
放学后篮球场上的穿着帽衫的他,江桥上认真写愿望的他,烛光前瞳孔闪烁着温柔的他,每一个他都定格在那张熟悉却模糊的、蛮横却充满稚气的脸上,时光再久也不会改变。有时我看不清他的脸,却能清楚地感觉他的存在,在我身边的每一刻,我的呼吸都乱了节奏。我们是如此贴近过,现在,也这般遥远陌生了。
他不在我身边,这就是全部答案。
谁没有一段悲伤的曾经呢。以后想起来,会笑着说那时候的唐漪是个不折不扣的痴情狂。然后呢,然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再也没有见面。以后的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记不清他的模样了。这大概,就是我们要走的路径。
唐漪拿出手机,“潘灏辰,无论涂潇林什么时候走,请不要告诉我”。
发完短信,唐漪把手机甩到一边。
我鄙视自己的自私,可我更害怕得到你离开的消息。如果我知道了你离开的时间,我怕自己会不顾一切地奔向你,然后看着笑容满面的你毅然地转身离去。不想去送你,因为我害怕会难过的只有我自己。就让我认为你随时会离开吧。不知道你确切离开的时间的我,也许日子能过得不那么艰难。
唐漪把手机举在空中,传出一条简讯。
—不如,我们见面吧。
—见面?
—我最近很难过。
—唐漪,我喜欢你,很久了。相信你有感觉。
—对不起。
唐漪很久,才回了一条“对不起”。
—为什么这么快就给我答案?
—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人。
—然后呢?
—他没有选择我。
—然后你没有选择我。
—我的心都被放空了。希望你能体会。
—你我都是一片流云,过去了便不再有痕迹。
—有的人,偏偏是布满城空的乌云。
—一场雨过后,他便也一无所有。
唐漪扔掉手机。
我们一直都一无所有,除了我们臆想中欢愉的爱情。
表面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是一环扣一环的人情债,我们都没勇气前进,也没办法回头。被人弄伤了再去伤害别人,是根本不懂爱情是什么的我们最幼稚最愚蠢的举动。
从空洞的体腔滑出漫延上来的潮湿眼泪,诉说着那一场风花雪月的记忆。迂回的风送来脊背的清凉,唐漪用手指在眼前画着空虚的未来。
在那之后,唐漪断掉了手机短信的联络。他们的最后一次联系,唐漪收到了一句“我喜欢你”。
2006年4月30日
陆希娅责怪我为什么拒绝短信中的那个人,我抱怨着说:“为什么他不是涂潇林,如果他们两个结合一下多完美。”她骂我贪心,说我想要的男人还没生出来。我却总是自私又可怜地妄想,该如何惩罚自己的贪念?奢求太多,幸福就太少。
陆希娅告诉我说她知道这样一个大学,考入之后,学校有一种培训考试,考试过关的学生可以公费出国留学两年,提供的国家有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韩国,还有瑞士!
我说,好的。
涂潇林,想起你时,我觉得你是个浑蛋,却漾满激动。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最初没有相遇……
如果曾经换个选择……
如果当时不曾了解……
如果那年,我们都视而不见。
我们总爱说种种如果,做着毫无意义的假设。
每个人心底,总有隐隐之中念念不忘的人,一天、一年抑或一辈子,只是时过境迁的我们,踏在那些曾经烧融的日子时,已经体味不到当年的滋味,也不再亢奋地翘首以待那一无所知的未来;喜欢恶作剧的我们,已经把心底最纯净的感情,埋藏在永不可能再回转的春温秋素的曾经里。
但那些曾经,却在接下来现实的生活中变得扑朔迷离。
唐漪灌了一口冰凉透心的水,桌上的台历显示,出国倒计时,三天。“三”这个数字在唐漪的心中滋长出可怕的孤独的异乡处境。尚未准备好的出国的心情,怎么就要逼自己离开?是不是到了国外,我可以把你忘记?为什么你的回来,让我如此不想离开?
她用笔从中国到瑞士画一条细而弯曲的线,8000公里,这就是我们的距离。
秋风送来了凉爽,让人有逃课去亲近自然的念头,于是唐漪背起她的帆布大包。麻软的布袋,挂在纤细的肩头,帆布包的流行,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复制感。每个人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城堡,咒语是我们辨别方向的音符。我们带着赤裸裸的信念,坦荡荡地前进,在布满荆棘的时光里。
唐漪先到了“品尝瑞士”,店里很静,学校旁边的蛋糕店在上课时间多没什么客人。A place nearby,唐漪还是钟爱能让人安静下来的调子。
“唐漪你太过分了,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马瀛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打破了唐漪正沉浸其中的平静,那种平静是如此的哀怨。
唐漪一脸无辜:“我怎么了?”
“她是在生气,你后天就出国了,到现在都不告诉我们。”吴霈诗坐了过来。
“我以为多惊世骇俗的事呢!对了,遥可街最近上了很多新款衣服,蛮不错。”
“你还真能打岔。”乔熠昕端着一块蛋糕走来,“你们要不要去点块蛋糕?蛋糕也出了新款。”
“亏我们还跟你一个寝室这么久,这一年算是白住了!”
“嘿嘿,我知道你们不舍得我离开。”唐漪眯起眼睛。
“一脸欠揍样。”
“涂潇林刚从瑞士回来,你就要去啊?”
“你俩到底怎么回事啊?以前很少听你提起这个人。现在却觉得你们似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是不是在追你啊?听他的口气,你们是不是曾经在一起过?”吴霈诗奶声奶气地问。
“难道是旧情人?”乔熠昕突然紧张起来。
“真想一口芝士蛋糕喷你脸上腻死你,我们没在一起过,他更不是在追我。别做你的春梦。”
“可是唐漪,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你在看他时的眼神,带着心事。”吴霈诗握起唐漪的手。
唐漪把手抽了回来:“只能怪他长得忧伤。”
没有人回应,三个人都沉默地望着唐漪。
唐漪看着吴霈诗,“吴霈诗,你是多么的幸运,无论以前你和他有怎样的波折,至少现在,你们又相遇在同一座城市,我是那么羡慕你,因为你们终究会有交集。即使他顽劣,他不够成熟,即使他任性他不懂是非,可你依然可以看着他,陪在他身边。没有什么能经得起时间的感化。他的心,在一个你未到达的地方等着你,你要勇敢地走过去。我必须衷心祝福你,你只能幸福,你必须幸福”。
我祝福你,也祝福不幸的自己,谁都不知道两年以后我再次回到中国,我们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在上大学之前,没有人与我彻夜长谈过,所以我以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和我思想一致地生活着。直到遇见了你们,这是我最爱的寝室,是大学里我最亲密的朋友,虽然我还未来得及告诉你们,我深爱着涂潇林。
晚上唐漪一个人回了家。
“唐漪你在家吗?我在楼下。”潘灏辰拨通了唐漪的手机。
“好,我下来。”
深秋也带着初冬的凉气,唐漪穿着单薄的衬衫跑了下来,潘灏辰站在被绿光灯照得斑驳的梧桐树下。
“唐漪,对不起。你明天离开的消息,我还是告诉他了。”
唐漪微微颔首,出乎意料地平静。
“潘灏辰,我想说……谢谢你。我很想见他,但我却……没有勇气告诉你。说起来,自己就是个矛盾。”犹犹豫豫、摇摆不定、优柔寡断,天秤座的特质在唐漪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你的心里,总是藏着那么多秘密。”
“不说我了。你的家里还好吗?”
“凑合。”潘灏辰憨憨地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平时的领袖气质就悄然不见了,像个带着腼腆和羞涩的孩子,这是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我们这一代,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大概多数来自家庭。
“和妹妹的关系有进步吗?”
“她叫凌夏。”
“对,凌夏!”
“是个调皮的女孩儿,转眼也要上高三了。”
秋日的梧桐树下,散落着绝望的枯槁树叶。风吹动刘海儿扫过额头,我们的高三,被风吹向了哪里?
这里的秋天,已脱去盛夏翠绿的色彩。城市数公里外的机场,提供的一切服务,只为离别与相聚。唐漪努力告诉自己,离开也不代表离伤。她穿着白色连衣裙,白色的鞋子,长发绾成一个清爽的髻,嘴唇涂着柔和的橘色唇彩,左手腕戴着一块白色的女士皮表。她今天是那样的清淡。换牌、托运,一切都安静而有序地进行,不焦急也没有慌乱,从她的表情中,看不出欣喜或悲凉。
唐漪告诉陆希娅,必须让这一切都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
“唐漪,积极对待那边的生活,你很快就会回来。”陆希娅抱着唐漪。
也许除了我,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认为去瑞士学习是一件要消极对待的事。这一刻唐漪的身体,那么无力,仿佛不稳稳地抱住她,就会瘫倒在地。陆希娅挽着唐漪手臂,给唐漪坚定的力量。
“我曾经以为,我的这次旅行能带来一次相聚,结果反而又是一场离别。”唐漪清苦的面容,渗不出一丝微笑,她是那样希望在涂潇林面前可以表现得轻松、毫不在意。
“‘离别’是为‘重逢’而铺垫。这次旅行,只是把你们重逢的时间拖久了一点。”
亲爱的,我已开始想他。
涂潇林走近唐漪,伸手缓慢温柔地抚着唐漪额前的头发,然后拉起唐漪的左手,用拇指摸索着唐漪手腕上的手表,眼神中闪着若有若无的内心深处的怅然与凄清,一年半以后,她的手腕上依然垂着那块手表,他依然有送她手表时的忧伤。
他欲言又止。
唐漪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迅速塞进涂潇林的手里,然后深深地拥抱。唐漪抿着嘴,咽下所有她想表露的语言。她朝涂潇林微微笑着,闭上眼睛,向后转动自己的身体。
如果现在我能说出来话,我一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再紧紧地把你抱住,请求你带我离开。转身而去的那一刻,我该如何纪念又该怎样等待未来的两年里继续消失的你。我要把那个拥抱,完整地刻入记忆,怀里的淡淡清香和温柔的气息。涂潇林,你能不能体会得到,我是多么不想和你道别。
失去缘分的人,即使在同一个城市里也不会相遇。时间让爱情面目全非,亦或许,那根本不是爱情。直接走掉,头也不回,伪装潇洒总比抹着眼泪更让自己欣慰。没有人必须为我们停留,我们也不会为任何人停留,想清楚了,就不会再有任何怨言。
涂潇林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洁白的速写纸。没有文字、没有笔迹,只有细而深的折痕,空白的纸印证着空白的思念。涂潇林明澈的眼神中,浮现一层层的忧伤。一张空白的信纸,在涂潇林看来,却写满了唐漪的挂念。
唐漪离开后,涂潇林的心情也变得沉闷。那张空白的信纸久而安静地躺在涂潇林家中的书桌上。他小心翼翼地拿起信纸,品读现在自己无奈的悔意和思念的苍凉。说不定,现在的我们本应恰巧在洛桑的街边偶然相遇,我的眼里充满惊喜,你的眼里充满暖意。是我打破了你既定的美好,还是我们注定不会在同一个世界里相遇?
潘灏辰在电话留言里说,潇林,你在哪?我家今晚没人,来我家玩游戏。
涂潇林穿上外套,带上房门,留得屋里一片死寂。
潘灏辰给涂潇林开了门。进了门涂潇林发现一个女孩儿从房间里走出来,涂潇林一眼便认出她是潘灏辰的妹妹。
“潇林哥哥,你好!”
其实她想说的是,潇林哥哥,我是个乖巧,懂得讨人喜欢的女孩。
“你好!灏辰有你这么可爱的妹妹多幸福啊。”
“我哥她可不这么认为。听说潇林哥刚从瑞士回来。”
“有一段时间了。”
“你来啦!”潘灏辰刚刚出现。
“那潇林哥的英语一定超好喽。”
“洛桑说的是法语。”潘灏辰轻盈地拍了凌夏的脑袋。
“但是会英语也是很必要的啊,外国都通英语的,是不是潇林哥?”
“呃,英语比汉语要好用一点,但欧洲不一定。”涂潇林抿嘴微笑。
“潇林哥,那你做我的英语家教,好不好?”
“你不是刚找了个英语家教吗?”潘灏辰质疑,打断凌夏和涂潇林的对话。
“那个老师不好啊!”
“她几乎是我能找到的高中英语老师中最棒的一个。”
“可是她给我讲课我听不懂啊,也不愿意听。再说潇林哥哥还可以顺便教我法语啊。”凌夏奶声奶气地耍起小女孩脾气。
“你又打什么算盘?上大学之前,先乖乖地把你的英语学好。”
“潇林哥,当我的英语家教行不?”凌夏转过头侧向涂潇林。
“受宠若惊,可是我……”涂潇林一时还不知应不应该答应此事,却又碍于是朋友的妹妹,难以推脱。
“你一定可以的,试试嘛!”凌夏眯着眼睛,摆出胜利的笑容。
涂潇林征求潘灏辰的意见,潘灏辰只耸了耸肩,再没了下文,于是做凌夏家教这事就算是潦草地定了下来。潘灏辰拍着涂潇林的肩膀,说家教费放心,不会少给的。涂潇林推开潘灏辰的手,说根本没打算收什么家教费,就是来帮潘灏辰的忙,打发自己的无聊。
进入10月的瑞士开始使用冬令时,整个城市也换了节奏。唐漪蜷缩在广场一座灰色欧式雕塑下,天幕的琥珀色已经开始放暗,她却不知道可以向谁求助。荷叶滚边的长裙搭在地上,唐漪抱住双膝,这座城市在她的眼中已经进入了严冬。瑞士人衣装随性而休闲,金发碧眼中少见喷上去一整瓶发胶的各种花式的高盘头。她们有精巧的淡妆,不用睫毛膏刷就卷翘且根根分明的浓密睫毛和耐人寻味的表情。他们在相对拥堵的城市找到了可以自我安慰的闲情,因为这里不是讲求黄金与气宇轩昂的世界。广场对面的酒吧门口放着悠扬的爵士音乐,闪烁的灯光炫耀地告诉唐漪,她不属于这座城市。
支撑唐漪来瑞士的理由早已称不上理由,到瑞士要找的人已经在离开中国之前回到了中国。悲伤的情绪就在唐漪踏上洛桑土地的时刻急速扩张膨胀,填充着心脾一起向下坠落的空间。没有了爵士乐,没有了闪烁灯光,也没有了漫步街头说着法语的行人。广场的灯渐渐亮起,衬托着已经渐晚的天色。灯光再亮,依然无法温暖唐漪的心。昏暗的光衔着灰尘缓慢地卷过来,唐漪深深地吸了一口傍晚冰凉的空气,双手紧紧握住裙摆。
身边的行李被移动,唐漪拉开行李,一只棕黄卷毛不知品种的小狗正用两只前爪用力扒着行李包,小狗突然停下来,两只滚圆的眼睛毫不避讳地盯着唐漪,闪着泪光,他大概饿了好久。唐漪突然记起包中的香肠。她迅速打开包裹,取出香肠,扒开外皮,用指甲把香肠掰成小块,丢在脚边,小狗直接扑了过去,头也不抬地专心吃起来。
“好吃吗?这是从中国空运过来的香肠哦!你吃得惯吗?”唐漪伸手缓缓地抚摸小狗有些干涩的棕毛,“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没有家,也没有人可以帮忙?”唐漪眼睛里充盈着泪水,“狗狗,你会不会想家?”
“请问,你是……中国人?”
唐漪惊愕地抬头,在这座陌生而无法读懂的城市,出现20小时前还能听到的熟悉的语言是多么让人温暖的事。一个面相清秀的黑发男生站在一步之外的不远处。他的黄色皮肤和黑色眼睛,像张可以被信任的名片。
“是的。”唐漪脱口而出并不由自主地站起来。
“刚刚看到你用中文和你的狗狗说话,我路过时正巧听到。”
“它,它不是我的狗,只不过,我们同命相怜,是这座城市的‘弃婴’。”唐漪苦笑了一下。
“你刚来洛桑吗?”男孩注意到唐漪身边大包的行李。
“是,我刚从中国来,来之前我已经申请宿舍,但似乎没有申请下来。刚去了学校才知道,现在还没有我的宿舍。”
“这里的公寓很紧张。”
唐漪耸了耸肩,指着行李:“所以你就看到我和我的行李流落街头了。”
“那么你打算……”
“之前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在洛桑,但在我来之前,他回了中国。”在想起涂潇林的时候,唐漪不是没想过涂潇林跟她说过,如果有困难可以来找他父母。但一想到见到他父母时尴尬陌生,或被嫌弃的画面,还是认为自己在街头被冻死来得比较舒服。
“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
“洛桑大学。”
“我们同一所学校。”
“我们同样来自中国。”
“看来我帮助你是义不容辞了。”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但你不必为难自己,我可以再想办法。”
他没有回答,掏出手机走远几步,拨了个电话。唐漪的心忽而温暖起来,却依旧充满落寞和无助的不踏实感。他挂掉电话,笑盈盈地朝回走。
“我想我可以帮你找个住处。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唐漪已经分不清此刻是开心、是惊愕、是害怕,还是忧伤。
“我可以暂时帮你找个住处,离学校不远,10分钟的路程,环境不是特别好,不过价格还算公道。”
仍然犹豫。
“是我朋友的女友原来的住处,现在他们住在一起,那个房间闲了下来。”
唐漪低头看着脚边还在吃香肠的小狗,拿不定主意。
“好吧,即使我是骗子,也不至于欺骗同胞,在瑞士碰到个中国人还真是不容易的事。我中文名字叫那可布。”男孩伸出右手,以示友好。
“那可不?好特别的名字。”唐漪扬起嘴角,“好吧,只身国外,反正也没有比我现在更糟糕的处境了。我叫唐漪。”唐漪伸出右手接应,她告诉自己,现在不是考虑那么多的时候。
那可布代唐漪联系了公寓的雇主。公寓离学校确实不远,从窗户可以眺望到校园。宿舍不算太大,类似国内很多城市都有的单身公寓。屋里的设施一应俱全,上个女孩布置的摆设还在。那可布帮唐漪把行李简单归位,便拉她出去吃饭。天已大黑,他们走进附近的一家牛排馆,在靠窗的桌边坐下。
“你也在洛桑大学读书吗?”唐漪充满了好奇,肚子里早准备了一筐问题。
“以前在这读书,现在是艺术系老师。”
“你怎么那么厉害能留校?”
“可能因为作品获奖吧。或者纯属我运气好。”
“那你来瑞士很久喽?”
“在瑞士待了6年了,之前在法国学习过两年。”那可布像服务员示意点了两份套餐。
“离开中国这么久,你的中文记得还蛮牢的。”
“那是我的母语啊。”
“你很久没回国了吗?”
“一两年回一次,不固定,也许某一天想回国做事了,就会放弃这边的一切。”
唐漪看不出那可布是个怎样的人,但她能感觉到那可布的真诚,毫无欺骗。
“我的法语名字……”
唐漪冲那可布摇摇手:“我没必要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就用中文名字好了。何况我还挺喜欢‘那可布’这个名字。有创意,够别致。”
“你明天忙什么?”
“明天去学校报到。”
“后天呢?”
“后天是……周六,还不知道。”
“快点吃吧,牛排别凉了。”那可布把摆在桌子中间的菜往唐漪那边挪了挪。
周末的清晨,那可布把他的奥迪TT停到唐漪公寓楼下。唐漪在睡梦中被屋内的电话铃声吵醒。
“下楼,我在楼下。”
“我在睡觉。”唐漪睡意正浓。
“那就快点起来。几点了还在睡觉?”
“瑞士人不都很悠闲懒散的吗?”
“你要勤奋,你是来上学的。”
唐漪打了个哈欠,果然是个老师,怎么瑞士的老师也擅长不停地唠叨。
“去哪里啊?”唐漪在床上转了个身。
“去写生。”
“我不会画画啊!简笔画都画不好。”
“唐漪,下来吧,我带你去转转。”
唐漪揉揉眼睛答应下来。简单地梳洗后,她跑下楼推开公寓的大门,奥迪车灯的闪动吸引了她的注意,唐漪看到车里坐在驾驶位置的那可布,穿着条纹衬衫,正微笑地下车去给唐漪开车门。唐漪脚步轻盈地走过去,坐进跑车。
“我带你去买些东西,然后去办电话,你没有电话怎么行。”
“没有人找我的,这里的人我都不认识。”
“以后就会认识了,你还要联系家人呢。电话能给你带来安全感。”
“谢谢你。”唐漪感到不好意思。她仔细想了想,到底谁可以联系呢?涂潇林是禁忌,父母时常冷漠的态度让唐漪提不起打电话的欲望,只能给陆希娅打打电话。或者寝室的姐妹,却也是潦草几句。
“我只是看在,你在洛桑只认识我一个人的分上。”
“不,我现在认识两个人了。因为我昨天晚上认识了隔壁的AMY。特别巧,她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看来你很有成就感。”
“那当然。开这么拉风的跑车,你是很有钱人吗?”唐漪前后看了看。
“在瑞士平均两个人就有一台车,不算什么。”
“哦,是这样!我原本想夸赞你是个又有钱又好心的人,看来现在我只能说你是个好心人。”
“谢谢你的高度赞扬,不过你现在应该想想你的公寓里都缺什么,我们一会儿去买齐。”
“那的东西挺全的,有简单的厨房,有冰箱,有空调。”
“我是说,厨房、冰箱里少点什么?”
“那……少的就多了。”唐漪放低音调。
那可布转头看了看唐漪,然后继续开车。
他们买了几大包的东西放进后备箱,冬天用的被子、各种食物和日用品。唐漪还特意挑了她喜欢的棉布窗帘。随后去办了手机卡。唐漪拿着那可布给他挑选的手机哈哈大笑。
“好丑的手机。”
“这里的手机都差不多的,你刚才也看到了。”
“看来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审美不太相同。”唐漪摆弄着手机,法语的显示屏幕真让她有点不适应。唐漪对着手机,发呆好久,类似这样的不适应,都会让她想起家,想到中国。
那可布抢过唐漪的手机:“一个手机,有什么好看的,除了丑一点,其他和你在国内用的手机都差不多。记得晚上把你的号码告诉你的家人。我们出发去莱芒湖。”
“莱芒湖?”
“去看我画画,免得一个人对着手机乱感慨。”
“你会画画吗?”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唐漪坐在车里,感受到车外的冷空气顺着车窗划过她的侧面。这一路的风景让唐漪目不暇接。莱芒湖与阿尔卑斯山的烘托下,洛桑城充满法国式的浪漫。中古建筑鳞次栉比,处处保留着古老历史的辉煌象征。罗马时代的遗址及中古时期的建筑在这里依然可以寻到,高耸入云的圣母大教堂守护着老城的宁静安详,庄严肃穆的钟塔还坚守着“守夜报时”的千年习俗。或许只有在深夜聆听钟塔上传来的报时声,才能体会到这里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执著和坚持。唐漪自认不是一个懂得艺术的人,在中国那点艺术思想,拿到瑞士根本就是班门弄斧,因为瑞士早已透支了你所有欲望。
“你知道瑞士让人大开眼界的几个特点吗?我也是在书上看到的,到了瑞士才发现,还真是那么回事。”那可布看唐漪发呆,就找话题聊了起来。
“瑞士人使用四种语言,但却没有瑞士本国人的语言。”
“是哦,还有呢?”唐漪侧过身,饶有兴趣地看着那可布。
“瑞士由四个民族组成,但却没有瑞士族人。”
“你说的瑞士族人,就好比中国的汉族喽?”
“瑞士国家元首任期只有一年,但却能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瑞士是“永久中立国”,但它却拥有军队;瑞士虽国小,各种资源都不富足,但人民生活水平却极高;瑞士各州的教育制度内容各异,但培养出的人才却比比皆是;瑞士虽未加入联合国,但联合国的前身国际总部却设在瑞士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总部、国际劳动组织总部也设在日内瓦。”
“这么神奇的,我以前怎么都不知道?”唐漪听了哈哈地笑,对于瑞士她了解得很少,她来的一切当初都是为了涂潇林。
“慢慢你会发现更多呢。你来瑞士是为了什么?”
“我啊,我……为了一个人。”
那可布是个绘画造诣很深的人。在他的画中,你能品出瑞士的味道,尽管那斑驳的石板铺在狭窄的街道,看不到洛桑最经典的景致,但这里依然可以望见洛桑的带有温度的生活。他懂得欣赏美、欣赏角度、欣赏颜色。尽管那些在唐漪看来毫无差别。
“巴尔扎克则说,莱芒湖是‘爱情的同义词’。”那可布支上画架,拿出画笔。
“我们就站在爱情的岸边。”
那可布看着唐漪笑了笑,又低头画着他的世界。“洛桑是座让你可以回想历史的城市。”
“莱芒湖也是经历了绵长的历史,才有如今漂亮的风光吧。”
“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罗纳河在埃克吕泽地区被冰碛物质所阻断,形成了莱芒湖。”
“你们艺术也学这个吗?”
“我是讲艺术史的,瑞士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历史。”
“这里虽然美。但其实我已经开始想念中国了,想念那里生活着的人们,想他们麦色的肌肤、深邃的眼睛、黑黝的头发。也许他们多数还在为生活奔波,没有这里人悠闲富足的生活。但他们的脸上,有你能懂得的真诚。”唐漪双手插进口袋,看着湖里驶过的船只,“我看不懂瑞士人的表情。”
“那你可以多看看我。”
“少臭美,看在你是老师的分上,不损你。”
“现在我不是你的老师。”
“那更体现我的友好。”
无论在莱芒湖的码头还是在圣佛朗索瓦的街边,总有许多倾情表演的艺术家,数之不尽的露天舞台和纵情欢歌的喧闹人群,优美的旋律令人心醉。处处都是各形各色的人群,尽歌尽舞的景色。唐漪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此时的语言,已是多余的。
那可布总是会叫我做各种事情,每天马不停蹄地给我安排活动,其实他是怕我空下来会寂寞,他从不向我问起家那边现在的情况,大概他很想知道,却只是怕我回忆起来会想家难过。
公寓隔壁的AMY是美国人。猛学法语的这一年,唐漪几乎完全把英语抛到了脑后。法语里很多单词和英语的拼法相近,读音却大相径庭。唐漪总会看着AMY,然后蹦出一些英语拼写的法语单词。AMY有时会叫唐漪一起吃晚饭,唐漪已经开始习惯外国人日常食用的食品。在她看来,瑞士人、美国人吃的东西都很类似。AMY个子矮矮的是个随和容易相处的人,她有着纯蓝的眼睛和浅金色的披肩卷发。虽然她讲的笑话唐漪向来听不懂,但唐漪想努力给自己一点点家的感觉。
和AMY一起收拾好餐具,唐漪回到自己的房间。手机提示音显示一小时前的一个未接来电,是涂潇林。唐漪的心一紧。也许涂潇林没什么事找她,只是随意拨了一下,也或许根本就拨错了才拨到这里。唐漪坐在床上,手机又响,屏幕上显示—涂潇林。唐漪没有犹豫,用手指轻碰绿色通话键。
“刚才给你打电话,你没接。”
“嗯,我看到了。”
“怎么不给我回电话?”
“……刚看到。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瑞士冷吗?”涂潇林总是避开唐漪最想知道的问题,他一直这样,做什么都凭自己的意愿。
“现在还好。你那边呢?”
“你住在哪里?听陆希娅说你没住上学校的宿舍。”
“嗯,不过现在住的离学校也挺近。你那边也开始上课了吧?”
“有没有开始想我?”
“涂潇林你能不能也回答一次我的问题?”
“开始上课了,我不喜欢这里,很不喜欢。”
“为什么?”
电话那边安静了一阵,“不为什么”。涂潇林的嗓子有些干涩。
“别任性,好好地生活。”唐漪没了脾气,在涂潇林面前,她从来也没有过脾气。但此时,她又只能无力地说一句冠冕堂皇却涵盖所有期望的女孩子的生活。她不敢说想念他,不敢说让他等她,不敢让他以后打电话来。
“唐漪,你早点回来。”他像个任性的孩子。
“……你在中国一个人,要照顾自己。我要睡了。”
眼泪是如此冰冷地流淌过脸颊,涂潇林,以后别再打电话过来了。
你的父母在瑞士,你在中国;我的父母在中国,我却在瑞士。我们彼此的关怀,都如此的寂寞。
寂寞和孤单是不一样的。
唐漪在洛桑待了两个月,除了那可布和AMY她还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朋友。接到大洋彼岸电话的她,开始分外想念涂潇林,他的认真和冷漠,他欠揍的表情和温柔的眼神。他总是那样咄咄逼人,任凭自己的想法,只发问不回答,却还是会说一句“唐漪,你早点回来”。电话那边传来的声音,字字捶打唐漪的心。即使相距8000公里,她依然感觉涂潇林就在周围不远的地方,好像一开门、一下楼、一个拐角处就能碰见他。
我们对他人的喜爱到底源于什么?为什么我们远隔千里,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过去,却还是没有办法忘记你?到了瑞士,我依然感觉自己像是一次旅行,明天即可起程回国,我没有日渐忘记涂潇林,大概是想念他的遍数太多,他的样子反而愈加清晰。那呼之欲出的思念是唐漪始料未及的。唐漪决定不再写日记,原因是她不想在每天写日记的时候想起涂潇林。每天想起,每天责备自己。那种想念,让唐漪心痛,看不到也抓不住,却长着伤人的刺,穿透了心,却流不出鲜红的血。挥之不去的刺,它想让你疼,你就得疼。
涂潇林,我为什么这么想你,你让我看轻了自己。
第二日晚上,唐漪接到了陆希娅的电话。陆希娅的问候变得多余,唐漪不好,她现在一定不好。
“他总是那么任性,来电话只向我发问,却不回答我的问题,他不知道我也想了解他的情况吗?他说从瑞士回来就回来了,他有没有问过我是不是将要到瑞士去?还有以前那次我离家出走,他让我给他做饭,我就只会做炒饭又做得很难吃,他也不放过我。”
“因为你心甘情愿。唐漪,即使你骂他千遍万遍也毫无用处,因为你忘不了他。你记住了他的任性和绝情,但更记住了他对你的关心和爱护的神情。你在乎他,无论他的好与不好都会被你铭记,他深深占据你的记忆空间。”
“它们自己跑进我的脑袋,我甩都甩不掉。”唐漪谈到这个话题,总有被命运判了无期徒刑的捉弄感。
“什么时候,你不再想向我提起他,你便真的放下了。”
唐漪哑口无言,陆希娅字字如利刀扎进唐漪封闭固守的心,她真切地感觉到陆希娅揭开她最不愿承认的伤疤时的疼痛。她心甘情愿地让涂潇林闯进自己的记忆,心甘情愿看他一步步离开,心甘情愿不去挣扎,心甘情愿自己心痛。当她毫不避讳地用锋利的语言刺醒唐漪的时候,陆希娅哽咽了。电话两端,一片沉静。
“希娅,我怎么这么不了解自己。”
唐漪啊,你那么爱他,为了那个人,你百爪挠心,你放弃过、释然过、自卑过、自怜过、努力过、挣扎过,终究还是无法自拔。你活在他的世界,他活在自己的世界。他可以鲜活地在你眼前跳动,却无法察觉你夜里曾为他说过的一句随意轻薄的话彻夜难眠。你所有的朋友甚至陌生人都看得出你的悲伤,只有他不懂。或者他根本没有读过你,因为他只关注他自己。你理智地分析,你们是那么的不合适,但在感情上你依然走火入魔般的无法放弃。
不会的,一定是有原因,你才无法放弃。
其实这个原因,我们都是知道的。
唐漪曾多次动过脑筋考虑要不要给头发换个颜色。她询问过无数的人,针对她适合染什么颜色的头发。当然她知道关于这点,她绝对不能向理发店的理发师请教。她曾经毫无防备地跑去理发店像所谓的店内顶级发型设计师询问,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只要染头发,什么颜色都好看,并且越贵越好看。于是他便对理发店的审美失去了信心。
来到瑞士,她终于下定决心保持她的黑发颜色。在瑞士,黑色反而变得特别。他们的金色头发在阳光下确实高雅动人。但既然上天给了中国人黑黝黝的头发,我们何不保持这份恩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