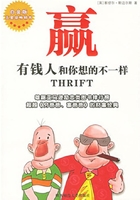迷雾,倒处都是看不透的迷雾,世界在我的眼中变得模糊,一层层的白色雾气浮了上来,包裹着我那颗越来越慌张的心。风不见了多久,我就昏昏沉沉地过了多久。漫无目的地行走,随时都会惊恐地大叫出声,晚上难以入睡,白天提不起精神,一闭眼就看到风从天而降,惊喜地睁开眼睛却发现面前空空,什么都没有。我一直都知道风对我很重要,但没想到的是竟然重要到如此地步。没有他,我寸步难行,简直活不下去。等意识到将要面临的一切,我才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清醒了过来,开始沉下心,正视现实。现实就是我和风走散了,我在找他,他一定也在找我,但我们这样漫无目的地寻找会有用吗?草原太大了,我们两个像两艘在大海上颠簸的小船,也许会在须臾间错过,也许会越走越远,相遇的可能只有几万分之一。
想到这里我打了个冷战,必须要减少或杜绝这样的可能,但是风,到底会去哪里呢?我闭上眼睛,把和风一起度过的日子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才发现,我们竟然从来没有商量过如果走散了该怎么办?那么我现在应该去哪儿呢?回到落日那里去?不,我们已经出来快要两年了,那里早就已经不是我的家了,再见面的话,我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个陌路人吧。回雨林草原去?不,虽然我和风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那里对我们两个来说根本不是家,它只是一个我们曾经到过的地方,是我们用来暂避风雨的地方罢了。而且夏洛他们还有可能在那里,据我对风的了解,他是绝对不会回到那里去的。那么,他会去哪儿呢?想了半天也想不出头绪,只这么呆着又不是办法,我只好再次上路,但这一次并不是没有目的地的。
我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并不陌生,这里离雨林草原有二百多公里,我们曾在去那里之前在这里呆了一段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多月而已,但我对这里的印象非常深。那时候,我和风刚刚离开了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抓不到猎物,也没有残羹剩饭可以吃,还要小心地躲避同类的追杀,差一点儿就饿死了。记得那一天我们来到这里,风饿得倒在了地上,我为了救他咬破了自己的前掌,用自己的血唤醒了它。到现在我右掌的掌心处还有着一块清晰可见的伤疤,从那时起风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在一起休息,他总要舔一舔我的掌心,什么都不说,只是用舌头默默地舔,有时也会含在嘴里。虽说这两年身上的伤疤渐渐也多了起来,但唯有这一块对我来说是不同的。它救了风的命,它所留下的回忆已经由痛疼变成了一个温暖的标志,以与伤疤相同的形状印在心底,让我们看到时想起时,总是会不由得微笑。
对了,这里就是我们在离开家最困难的时候所呆过的沙石地了。我记得那时风就倒在那里,我忍不住向前走,翻过一座石头山,如愿以偿地找到了一棵刺槐。当时风就躺在树下,他那时还处在成长的阶段,骨架纤细,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骨瘦如柴、蹙着眉头、一动不动的样子。当时,就算一败涂地,就算快要死了,我们至少还在一起,一起承受痛苦,一起想象未来,日子过得倒也苦中有甜。但现在,虽然已经长大,长大到不必随时仓皇逃命的程度,却只有我一个人形单影只、失魂落魄地站在树下,连遥想当年的艰难也成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幸福。我很想哭,但泪还未落,就已经风干在眼中,是了,我已经长大,我的外形已与一只成年雄狮无异,哭泣不再是我要表达情绪的唯一方式,也可以这么说,哭泣已经不再属于我了。我在布满沙石的树下躺了下来,把坚硬的碎石压在身底,清晰的痛疼传来,我没有起身,就这样一直躺着,仿佛自己已变成了那时的风,就这样在半睡半醒间感受着生命流失的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