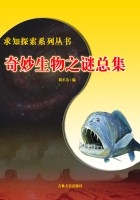因为空手而归,大家都显得有些垂头丧气,我看着胡达若无其事地溜达回来,好像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我无名火起,没来得及克制,身体已忠于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扑了过去。胡达没有防备,被我的吼声吓得一愣,就披头盖脸挨了我一巴掌,好在我还有理智,并没有直接用牙齿招呼他。只是这下子也不轻,他被我打得在地上滚了几滚,脸上划开了两道血口子,不深,但看他的表情也挺疼的。胡达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发难,被我突如其来的攻击弄得一愣,硬生生地挨了一记,但他也不是吃素的,马上爬起来还击。我毫不示弱,两人扭在地上一阵乱打,等风赶来把我们分开时,两个身上都挂了彩,虽然伤不重,但身上粘满尘土杂草,也有够狼狈的。总得来说还是胡达吃了亏,但风没有责备我也没有安慰他,只是站在我身边无聊地打了个哈欠。胡达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不敢再来,只好不甘心地吼了两声走开了,我得意地转向风向他笑笑,却突然发现夏洛在不远处看着我们,见我看到他了,就若无其事地把头转了过去。
我不由得一愣,他在呀,我还以为他不在呢,但他为什么眼看着胡达吃瘪而不帮他呢?难道他也认为胡达太过分了,但又不好与他撕破脸,所以才不出手帮他,我的出面教训也许正和他意吧。一想到被别人当枪使了,刚才的得意劲一下子烟消云散,我无精打采地跟在风的后面,准备回去休息,风也看到夏洛了,但他平静得多,只是黙默地向前走,看不出有什么情绪。野牛体格太大,吃的太多,不会像角马那样连夜迁徙,跑一段路见我们不追了,它们就停下了,接着睡觉的睡觉,吃草的吃草,好像没事发生一样。回到营地,我若无其事地趴在风身边休息,没过一会儿就见夏洛和塔塔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垂头丧气的胡达。胡达一看见我,头上的鬃毛立刻就竖起来了,低头咆哮,弓腰做攻击状。我当然不肯示弱,马上站起来张牙舞爪地示威,这时夏洛回头瞪了胡达一眼,胡达立刻蔫了,气恼地跑到一棵树下趴着不看我想和我斗,你还嫩着呢。我又一下子高兴起来,得意洋洋的向他挥了两下爪子后,才暗笑着趴了回去。
风见我乐不可支也不劝阻,只在一旁看着看着,突然偷偷笑了一下,我知道他可能是笑我这么点儿事也能高兴成这样,但那又能怎样,我不像他什么都憋在肚子里,我高兴就是笑,生气就要发火,这样才是真正直实的我。见风偷笑,我理直气壮地瞪了他一眼,显示自己很有道理。这家伙见了居然不厚道地笑出声来,于是我不客气地扑上去咬他的鼻子,风见此一边用右掌按着我的脸歪向旁边,一边还大声笑着,我气极了,张口把他的右掌含进嘴里咬了一下,当然没用全力,却也够他疼一阵的。风忽然愣了一下,他收起了笑容,右掌的力气也松了下来,少了支撑的我没有防备,一下子倒在他身上,把他压在了下面。没有听到预料中的惊叫声,我才发现风格外严肃的表情,把他咬疼了吗?我急忙爬起来察看。风默默地从地上爬起来,扭过头去抖抖身上的土,什么表情也没有,我在一旁小心伺候着,心里又很奇怪,以前更过分的玩笑也开过,都没见他这样呀。轻轻地碰碰他的背,他才转过身,脸上还是很严肃,却并不是生气,而是隐隐有些难过,我正在奇怪,他抬起前掌伸了过来,直接伸到我半张的嘴里,按在我其中的一颗长牙上,按了一会儿,又轻轻来回抚摸着。
那颗牙齿并不完整,牙尖被生生磕了一块去,历经长年累月的磨擦,已经变得平整而光滑。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这颗断了尖的牙齿,这是当年我不自量力的攻击雷,被他一个巴掌从山坡上扇了下去磕在石头上摔断的,好在雷没有用全力,不然我命都没了。这颗牙齿并不是完全没有用了,它只是顶端断裂,在我的舔噬下变得圆滑,比不上其他三个锋利,但攻击猎物时只要够用力,它还是可以穿透它们的皮肉,咬管他们的喉吼的。这件事本来真的让我很难过,牙齿对我们这些在草原上噬血的生物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小事,它的好坏决定着我们身为掠食者的资本,是我们活下去的基本条件。
但时间久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我反而开始释怀,这颗断齿也就不是那么难以面对了,但这对风来说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所以他看起来特别难过,比我还难过。他很憨厚,但不笨,他也明白我在家里的那段日子并不快活,至少不像我表现出来的那样快活。我向他笑了笑,然后扑过去把它压在身下狠狠地抱着,这次他没有反抗,我知道他可怜我这个从小就漂泊无依的可怜虫,爱心发作的时候就会百依百顺,任我胡闹,我并不想告诉他我真的已经不在乎了,而是充分利用他偶尔爆发的爱心欺负他一下。以前的事都已经淡去了,只有现在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我和风在一起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