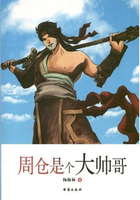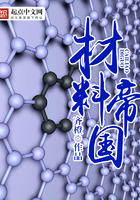这是一部纠缠不休的小说。
关于忘记与回忆,离开与回归,撕裂与弥合,清醒与幻觉,身体与灵魂,背叛与忠贞,欲望与爱恨的厮缠。我用最热烈奔放又最无情残忍的描述,让它们嵌入彼此。犹如沙粒嵌入贝壳的身体,尽管疼痛无比,但当它们彼此进入,终会有一粒珍珠,璀璨而生。
我用一封又一封的情书,串联起整个的故事。你在其内,不止可以读到爱情,还有少女与女人的撕扯,小镇与城市的冲突,男人与女人的战争,金钱与爱情的背离,父辈与子女的纠葛。
我书写它们,是因为我熟知它们,热爱它们,并曾历经过它们。自我从小镇走入城市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要为我生活的小城,为我想要逃走却又始终无法出逃的城市,寂寞书写。
你无疑,会与我一样,沉浸在这个一面背叛一面忠贞的故事之中,无法自拔。
会与我一样,爱上它,并无法将它抛弃在中途。
爱上一个人,只需要一秒。忘记一个人,却需要耗尽漫漫一生。
我们究竟需要走上多久,才能最终洗尽时光烙在灵魂上的印记?
以此记下,为我们曾经一路奔逃,寻不到出路的爱与生活。
是为序。你的小小妖精龙小白
亲爱的锦:
这是我写给你的第24封信,我想或许你已经忘记,可是,我却记得。很清楚地记得。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我有多么地爱你。爱你到可以将我的一切从这个世界上粉碎掉,如果,你能够懂得。
锦,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魂吗?或者,有灵魂也可以。我相信,真的,我不是在说胡话。我知道你看了这些一定又会用你果敢的语言教训我,说我是个傻瓜。你比我大15岁,你走过了很多的地方,你听到过许多奇异的事情,但你从来不相信鬼魂。哪怕,你第一个孩子去世的时候,你都不相信。
可是,锦,我相信。而且,我感觉过灵魂的存在。我甚至跟它有过交流。
是的,有过交流。就在昨天夜里。
我又发起了高烧。我的身体用医生的话说,如果再不知道好好爱惜,就不会是我的了。我从诊所回来,感觉躯体变得很轻。我勉强吃了药,任由自己像块破败的抹布一样,随意地丢到床上。
你送我的毛毯,我一直舍不得盖,每一次都只整齐地叠好,搭在小腹上。这样我会觉得温暖,就像你的大手,粗砺抚摸过我一样。
我就这样迷糊地进入梦境,并看到那个落魄的灵魂。它果真是从我的身体里飞升出来的吧,否则怎么会与我有一样杂乱的头发,还有瘦得让人心疼的肩膀?它的眼睛,却是明亮的。我看到里面有闪烁的光泽,是蓝绿色的,犹如夜间的鬼火。
我知道这样的描述会吓住你,但我不害怕。我记得小时候一个人在野地里跑,想要逃避父亲的打骂,就常会看到这样的光亮。它们在坟茔上空飘浮,看我跑过,会亦步亦趋地跟着。如果我停下,它们也懒懒地停下,还会散开一点,似乎,怕将我吓哭。喔,它们不知道,其实这个恐惧父亲责打的孩子,又是多么地大胆与放肆,大胆到可以在野外的坟堆上哭着睡过去,一直睡到太阳升起。那些蓝荧荧的火,也隐入到坟墓里去;放肆到裙子后面的拉链坏了,露出背上洁白的肌肤,有男人不怀好意地看她,她都旁若无人,理都不理男人的搭讪。
锦,你猜我问了那个灵魂什么问题?你肯定猜不出来,或者,你根本没有功夫去猜。你总是那样的忙,忙到连下楼梯,都恨不能一步跨下去就是十个阶梯。
那我就告诉你吧,我问它,我会有一个你的孩子吗?在我们已经分手两个月之后。
锦,这个问题,其实我很多次地问过你,在我们依然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傻傻的丫头,22岁,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你叫我“丫头”、“傻瓜”、“小妖精”,或者“小妓女”、“小荡妇”。我在北京,谁都不认识,但我却拥有了整个世界。因为,我爱上了你。而你,也那样地爱我。
每一次与你见面,与你疯狂地拥吻在一起,我都要对你说,锦,我想要一个你的孩子,我要一个人养着他。你总是将我吻得喘不过气来,说,好,我给你,给你我们的孩子。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便想狠狠地咬你,在你身上留下我深深的齿痕。我知道这是你最害怕的举动,每一次都在大叫之后,陌生人似的看我。我喜欢你这样仓惶的注视,如此你就会发现隐藏在我身体里的疯狂与激情。你会在走之前,一遍遍地用热水冲洗我咬过的齿印,试图将它们洗得了无痕迹,可是每一次你都发现这是徒劳,并对我发脾气。我抱着你,抬头嘻嘻笑着看你,像看一个我所敬仰的兄长,或者父亲。到最后,你说累了,便叹口气,捏一下我的脸蛋,说,你真坏,下次我注射狂犬疫苗,就再不怕你这个小狗子咬我了。
锦,我说的是真的,我想要一个你的孩子。哦,不,是我们的孩子。这样的话,在我与你做爱做到疯狂的时候说出来,你会将之当成我呓语似的胡话,转身忘记的吧。所以我曾经努力地寻找机会,想要与你认真地谈论这个问题,但你总是忙得没有时间。你要挣钱,要在北京供一套150多万的房子,要养活你没有工作的老婆,刚刚三岁多的女儿,还有4个没有退休金又总是进出医院的老人。除了好好地爱你,疼你,对你好,我不忍心用其他的事情来打搅你。所以每次打电话给你,听到你说在忙,我总是说,傻瓜,你忙,我不打扰你。
所以我现在要对这个通灵的魂魄说,我要问它,求它一定告诉我,我究竟能不能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在我27岁且与你分手60天零3个小时15分钟后,可以有一个代替你来让我去爱的孩子?
你一定和我一样想知道裹着一袭黑色风衣的魂魄,究竟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吧。锦,我想知道,你希望是什么样的答案呢?模糊不清,还是一语中的?或者,你根本不希望我问出这样的问题?
锦,我要告诉你,我在迷糊中,感觉自己像在一艘波浪中行驶的小船里,外面有一阵大风横刮过来,那样强烈的一股风,几乎要将小船掀翻到海里去。我紧紧地抓住那块天蓝色的毛毯,像抓住一块救命的浮冰。锦,我很冷,我觉得我好像要死了。可是我还是努力地等着那个同样孤单的魂魄开口告诉我答案。
然后我便看见它伸出枯枝一样毫无血肉的手,它冰冷的掌心里,放着一张薄薄的纸。它面无表情地说,拿去吧,答案就写在这里。我欣喜若狂地欠起身去取,可是偏偏就在这时,狂风吹破了船上的帘子。我刚刚接触到的那张纸,啪地一下便被风卷到半空里去。我想要跳起来去抓,纸却轻飘飘地落入了水中,而后不过是几个浪打过来,便远到我再也无力去追。
锦,那张纸片在海水里,像一朵凋零残破的花,随了一个接一个打过来的大浪,伶仃无依地飘着,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将抵达哪一个地方,就像现在没有工作、回不去故乡,也寻不到爱人的我。
我终于还是哭醒了,并发现自己的手脚快要成冰,而额头却是烫得几乎放上一杯冷水就可以沸腾。此时的你,在北京是奔波在夜间行驶的地铁里,还是已经回到有暖气的房子,喝一杯驱寒的姜水,写日间采访的稿子?你会不会看到这一封信,或者想起我们的约定,每天都去只有我们两个人交流的信箱里看看?我不会给你在QQ或者MSN上留言,我也知道你早已经将我删掉,永不再加。我答应过你,离开了北京,就不再有以前那样疯狂的举止,动不动就打车过去找你,而且,是站在你采访的车旁固执地等着,不管你的身边有没有熟悉的人在。
如果你依然爱我,就像我现在加倍地爱你一样,你一定会看到这一封信,包括以前给你写过的每一个字,寄过的每一张照片,留过的每一句问候,震过的每一声铃响。
锦,我要睡了。入冬以来,我总是得病,感冒,发烧,胃痛,头疼。每个月经期的疼痛,也一如往昔地折磨着我。我不想遵照医嘱持续不断地吃药,我要用我瘦弱的身体,抵抗这些病菌的侵蚀,就如抵抗无孔不入的爱情的疼痛。
锦,我多想蜷缩在你的怀里,哪怕,只是短暂的片刻。
答应我早点休息,尽管你一直失眠,早睡也不能像我一样,没心没肺地抵达梦乡。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