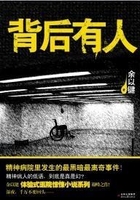我一早就听说了苏良的大名,著名的海龟派画家,以画女性人体器官闻名,当然更多的还是他与各色女子出现在报纸娱乐版的绯闻。所以,当郑栋说要带我去苏良的画室参观时,我把头摇得跟拔浪鼓似的。
郑栋说,不见识苏良的才气绝对是人生的一大损失。
得,冲郑栋这话也得去。
尽管心里早就把苏良归纳到色狼行列,但当我见到苏良时还是狠狠地吃了一惊。
苏良没有长一张画家或者色狼的脸,那是一张怎么样的脸,我觉得我突然找不到形容词,就像是岁月的年轮走过后,刻下了无数的沧桑,特别的凄美。
郑栋跟他介绍我时,他正作画的笔居然停了下来,看着我说,你就是郑栋的小女朋友,白素素。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急忙争辩,才不是,我们只是朋友,普通朋友。
他说是吗,又继续低头作画。
不知怎么的,我的脸就更红了,跟天边的火烧云似的。很久以后,我都不明白,我怎么就在这么一个声名狼藉的男人面前,表现得那么的稚嫩。
郑栋说,苏良天生具有吸引女人的魅力,女人只需看他一眼,就得陷进去,如果再看到他的画,这辈子就完了。
我想郑栋的话未免夸张了些,女人爱一个人是爱他的内心,而非单单就是外表,我不知道别的女人是什么样的爱情观,反正我不会只爱男人的外表,那太空洞了。
可是,当我看到那些女性人体在苏良的笔下如同神之笔韵,像极了一朵朵绚烂致极的玫瑰花时,我只觉得一阵晕眩,那是被某种力量冲击的感觉。
我知道我完了,苏良的神来之笔,这一刻在我的心里盛开了柔软的小花。
从画室出来后,我的心里脑海里全是苏良,我想我一定是中了苏良的蛊惑,要不然怎么会主动问郑栋关于苏良的事。
郑栋看着我,眼神忧郁地说,真不该带你认识苏良。
郑栋喜欢我是众所周知的事,其实作为男朋友他真的是很不错的人选,无论是家世还有外表,几乎没得挑,可我对他从来就没有来电的感觉。苏良不一样,仅仅一面之缘而已,我就迫不急待地想要知道他的一生。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如果是,我认了。
那个下午,郑栋告诉我很多关于苏良出国之前的事。当苏良还是一个不得志的文艺青年时,在我们这样的小城,画人体跟那些在公车上摸女人屁股的色狼,所受到的待遇几本一致。有一次,他的画室闯进来几个小混混,大家把他按在地上,一边敲打他的双手一边说,要毁了他那双万恶的脏手。
郑栋说这些时,我早就泪流满面,他看了我一眼,然后说,素素,你爱上苏良了。
我不肯在郑栋面前承认我爱上苏良,因为在这之前,我还万般抵毁他,可是郑栋坚持说我爱上了苏良,他说,素素,女人的爱情都是从悲天悯人开始的。
也许吧!
转天,我一个人去找苏良,他正在砚台上反复运笔,突然他把笔用力一提,仿佛要把自己的内心世拔出来,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声“好”。
他回头,见是我,收起笔,像想到什么似的说,你的郑栋呢?
我瞪了他一眼说,郑栋不是我的男朋友。
他嘴角向上扬,便不再搭理我。
我一下就难堪了起来,但转念一想,他是名画家,每个人来找他的目的不是讨画,就是有事相求,他大约以为我也是。
我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才把他的房间打扫干净,然后把他冰箱里的方便面都扔进垃圾桶,换上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以后的一个星期,我每天雷打不动地出现在苏良的画室,看他画画,替他打扫卫生,我们之间的对话少得可怜,他没有什么要问的,我说多了反而有些做作,干脆什么也不说。
那天,也不知道是不是心血来潮,我突然从身后抱住他说,苏良,我喜欢你!
苏良的身体僵住了,只有一秒的时间,他转头看着我,那双眼深不可测,我看到他眼中的自己苍白无力,我以为他会拒绝我。
可是,没有。
他抱起了我,重重地将我放在那张充满油墨味的画台上,我觉得有一匹野马朝我的身体,朝我的心里闯了过来,是那么的欢畅淋漓。
欢爱之后,苏良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你喜欢我什么?
都喜欢。我在这个男人面前总是毫无保留。
他的吻像雨点似地落满了我的唇,我的身体,我觉得呼吸在这一刻都停止了,因为空气里只有爱情的味道。
郑栋知道我和苏良的事后,叹了一口气,他说,素素,你迟早会受伤的,苏良那样的男人不适合爱。
我才不管,爱情是争分夺秒的事,谁还会去管天长地久的后事呀,我只要现在苏良是爱我的就够了。
可是,我错了。
苏良从来不说爱我,也不会主动打电话给我,总是我去找他,给他做饭,做卫生,然后做爱。除了身体的纠缠外,苏良讲得最多的是他的过去。
尽管苏良的那些过去,我早从郑栋那里得知,可还是愿意听,还是会泪流满面。我想一个男人愿意把他的过去毫不隐瞒地告诉你,应该是爱。
当然,苏良也会讲他和那些女人的故事,其实应该是我主动问的,明明我刻制自己不要去问,可还是问了。
苏良说,那不过是寻找灵感。
是的,没有哪个女人心甘情愿将自己身体的私处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画,除非爱上他。
我以为苏良会提出让我做他的模特,可是半年过去了,他提都没有提,又是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画我?
他竟然看着我很认真地说,我不画自己爱的女人。
这样的话,虽然波澜不惊,可我却可以为他上刀山下火海。
可郑栋却说这不过是苏良对付女人的手段,他还说苏良对待女人从来都不会长久,他见过在苏良身边停留最长的女人不过是七个月。
我想她们一定不是真正爱苏良,正如苏良所说,她们爱的只是他的画和名声,而我爱他的一切。
苏良总说我是他的精灵。
这样赞美对于我很受用,我越发的对苏良好,甚至把钱都贴在苏良那,房租,生活费甚至水电费,我通通替苏良打理得干净利索,我是真把自己当作苏良的女人。
除此以外,我心甘情愿做他的模特。
苏良要出一本画集到国外参展,需要一百名年轻的女模特,只是现在的女孩子都精得很,就算苏良再有名,出再高的出场费,她们也不愿意,在陌生男人面前展示自己的私处。
苏良急了,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天整天地抽烟。
我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然后躺在那张无数个女模特躺过的美人椅上,我看到苏良的眼睛里含着泪花,他说,素素,委曲你了,你是我永远的精灵。
真的没有什么委曲,我是自愿的,与其让苏良画别的女人,何不让他这辈子都画我,我要做他永远的,唯一的精灵。
只是这么带有私心的话,我没有敢跟苏良说,我怕他说我小心眼,艺术家都不喜欢斤斤计较的女人,苏良也是。
那天,我在美人椅上躺了整整三个小时,那可是隆冬时节,我只觉得身体如被刀子般轻轻地割来割去地痛,可心是暖的。
是啊,还有什么是比为爱付出而更伟大的事。
终于,苏良画完了最后一笔,他兴奋地冲到我面前,将我挤挤地搂进怀里,温柔地说,素素,谢谢你,我爱你!
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这么长的日子,我终于等来了这句最珍贵的话。
我知足了。
苏良的画经过宣传,反响挺不错,特别是经电视台和报纸的大幅报道后,开始有一些漂亮的想一夜成名的女孩主动找上门,我盯着她们,眼睛里都生出了剌。
可苏良没有看到我的这些剌,他把自己和那些女孩关在他的创作室,并且不允许我敲门。
他说,素素,你知道我创作的时候需要绝对的安静。
我点了点,转身。
我终于知道郑栋为什么说,爱上苏良会受伤。谁能忍受自己的男人,和光着身体的美女独处一个房间,哪怕是打着艺术的旗号。
我觉得心里有成千上万只的蚂蚁在吞噬,致命的难受让我开始胡思乱想,闭上眼睛仿佛就看到苏良和那些女孩子们躺到了画台上。
终于,当苏良和那个说话像林志玲一样嗲的长腿美女,在创作室超过四个小后,我不顾一切地撞开了那张红色的大门。
一切如我所愿。
我看到苏良和那个女孩像动物一样缠在一起,此刻,苏良的手在她的长腿上慢慢地游走。
我的心一下就疼了,仿佛从内心深处传来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
他们也被我的样子吓坏了,长腿美女迅速地穿衣服,飞快地逃离了这间小小的创作室。苏良点燃一支烟,他甚至连衣服都没有穿,大约这对他而言,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
为什么?我哭着问他。
我情她愿,就像我们一样。他漫不经心地回道。
我愣住了,没有哪一刻,我比现在更感到羞耻。真的,那一刻,我所有的爱情就一个被针扎破了的气球,一下泄了气。
我再也没有找过苏良。
很快,苏良的画集出版了,我并不想关注他,那个人是我原始的羞耻,只是电视上,报纸上整天的报道他,关于他的消息无处不在。
我终于见到了那本画集,封面写着,致我的精灵们。
那些作品里,我已经找不到哪个精灵才是我自己,只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只不过是苏良众多精灵里的一个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两个月后一个周末,郑栋给我送来了艺术馆的门票,他们报社在那里举行了一个摄影展。他说,素素,你一定要来,我的处女作品也在展览中。
去了后,我才发现,郑栋的作品竟然全是我。
只是,很快,我的眼睛就模糊了,郑栋的每张像片下,都写着那么几个字:我心中最忧伤的精灵。
那些都是我和苏良恋爱时的样子,曾经,我一度以为和苏良恋爱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候,可是只有在郑栋的镜头下,我才知道自己是那么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