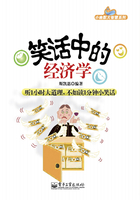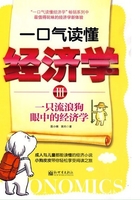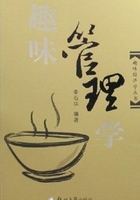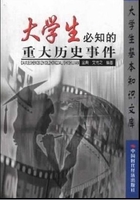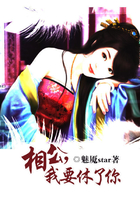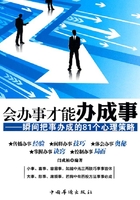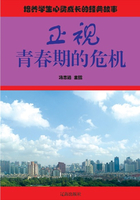仇富有理
《伊索寓言》中有一则“狐狸与葡萄”的故事:狐狸饥饿,看到葡萄架上挂着一串串葡萄,想摘又摘不到,临走时自言自语地说:“葡萄是酸的。”这则寓言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酸葡萄”心态被人概括为人性的弱点之一。“酸葡萄”心态出于人类妒忌的天性,任何人都难免。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部分人迅速致富,另一部分人相对贫困下去,这时“酸葡萄”心态成为后一种人的普遍心态,于是就有了“为富不仁”的观念。于是,“仇富”成为社会的共同心态了。
但是,“仇富”可以完全归结为“酸葡萄心态”吗?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晓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判断: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涌现的 “转轨富豪”几乎全部是“问题富豪”。他们的财产状况扑朔迷离,一直让人怀疑。带着“与生俱来的原罪”,他们没有把财产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中,而是以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引来了如今争论不休的“中国人仇富心理”。
人们对于一些富豪的财富是否干净、是否阳光,有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贫富悬殊的拉大,随着社会创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贫者不能心服口服,富者不能理直气壮。一部分人确实是在通过一些很不正当的手段、见不得阳光的措施在积累自己的财富,特别是一些人的第一桶金,淘得并不是那么阳光。
有人从民企攫取财富的“非法”形式上对“原罪”进行定义:一类是“腐败型原罪”,即依靠贿赂官员、权钱交易,从中牟取暴利;一类是“暴力型原罪”,即依靠暴力犯罪、强权垄断、黑社会组织攫取社会财富。有人从公司行为和个人情感上进行定义:一类是可以被原谅的,如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没有及时发放工资,因为经营困难没有准时纳税等;一类是不能被原谅的,如污染环境、虐待员工、假冒伪劣等。有人说:“现存原罪现象的主体为通过特权与寻租,或者通过特权、寻租、制度缺陷获取稀缺资源如资本、土地、原料等,再加捕捉到的商机而积累财富。”
但是,“仇富心理”无论怎么说也是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理,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富人们要努力减轻“仇富心理”带来的社会影响,应从以下方面做起:其一,富人应当更自觉地、更广泛地从事慈善事业,用慈善的方式回报社会。美国著名经济时评人理查德·兰伯特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曾经放出高论:“在美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聚敛财富,你可以拥有极多的财产。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所回馈,而且必须有人注意到你这样做。而且你必须这样做,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大人物。”在美国,人们并不景仰富人,而是景仰对社会有所回馈的富人。
正因为如此,《商业周刊》每年公布的慈善家排行榜比《福布斯》每年公布的富人排行榜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中国的富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深度和广度都还远远不够,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定法律把富人们的慈善热情变成实实在在的事业。其二,富人应当更自觉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把公司——一个单纯的经济单位变成一个诚实的、道德的经济单位。其三,加大立法和执法力度,切实保护好劳动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对于用种种方式侵害公民合法财产的行为要坚决给予打击,使整个社会形成合法致富的社会风气,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必须走阳光富裕之路,必须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合规合法地创造财富,那样才能够睡着觉,心里才踏实,才能够享受财富带给自己的幸福。
从“二子分财”看效率与公平
经济人是一切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因为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在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前提下,“公平”分配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公平”自然也成为自古以来永恒的话题。人们都知道公平,而时下“公平”也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甚至有人要求对财富重新进行一番分配。一个社会的确应该实现公平,但问题是显现要弄明白什么是公平。《百喻经》中“二子分财”的故事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公平观。
古印度有一个贵族,得了重病将不久于人世。他临终前告诫两个儿子:“我死之后,要合理分配财务。”两个儿子听从了父亲的教导,在父亲死后,将所有遗产分成两份,但是哥哥指责弟弟分得并不均匀。于是,一个老人给他们出主意说:“我教你们分财产,一定是平等的。将所有的物品全部破为两半,就是将衣服、盘子、瓶子、盆、缸从中破为两半,铜钱也从中破为两半,每人各取一半。”
这种分法可以说是绝对公平,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损坏了,这种公平有什么用呢?实际上,这两个儿子有完全平等的继承权,财产应该平分,但是不可能有完全的平等。如果把公平理解为完全平等,那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人们对于公平的理解应该脱离“绝对公平”的桎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永远是相对的。我们反对那种小生产者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观,提倡多劳多得。这就涉及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首先认识一下什么是公平和效率。公平指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及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都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平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存在永恒的公平。不同的社会,人们对公平的观念是不同的。效率就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值,或者叫效益与成本之比值,如果比值大,效率就高,也就是效率与产出或者收益的大小成正比,而与成本或投入成反比。也就是说,如果想提高效率,必须降低成本投入,提高效益或产出。
效率和公平是经济学中绕不过去的话题。很多人认为,要强调公平,就要牺牲效率;而要强调效率,就难免要付出不公平的代价。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完美结合,谈何容易?举个例子来说:
两个孩子得到一个橙子,由一个孩子负责切橙子,而另一个孩子选橙子。最后,这两个孩子按照商定的办法各自取得了一半橙子,高高兴兴地拿回家去了。其中一个孩子把半个橙子拿到家,把皮剥掉扔进了垃圾桶,把果肉放到果汁机上榨果汁喝。另一个孩子回到家把果肉挖掉扔进了垃圾桶,把橙子皮留下来磨碎了,混在面粉里烤蛋糕吃。
从上面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两个孩子各自拿到了看似公平的一半,然而,他们各自得到的东西却未物尽其用。表明上看似公平,却并未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即资源利用效率并没有达到最优。
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同时实现平等与效率,但事实上,同时实现平等和效率往往比较难。要提高效率难免有不平等,要实现平等又要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在30余年的改革实践中,我国一直施行“效率优先”的策略,但人们发现,不公平状况的持续恶化对效率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如不公平感导致各阶层之间“分配性冲突”增加,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所以,并不能一味讲效率。
其实,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既不能只强调效率而忽视了公平,也不能因为公平而不要效率,应该寻求一个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契合点,实现效率,促进公平。
都是“公共”惹的祸
城市公用设备是最容易破损的,公共场所的卫生是最令人头疼的,国有企业是亏损最严重的……理性的经济人都知道,对公共物品而言,你不从中获得收益,他人也会从中获得收益。所以人们只期望从公共物品中捞取收益,但是没有人关心公共物品本身的结果。难道这一切都是“公共”惹的祸?
英国人哈定于1968年就曾经注意过这个问题:“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他提出了一个“公地悲剧”的模型。
一群牧民在共同的一块公共草场放牧。其中,有一个牧民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是有利润的。虽然他明知草场上牛的数量已经太多了,再增加牛的数目,将使草场的质量下降。但对他自己来说,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因为草场退化的代价可以由大家负担。于是他增加了一头牛。当然,聪明人并不止这一个牧民,其他的牧民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都增加了一头牛。人人都增加了一头牛,整个牧场多了n头牛,结果草地被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牧场再也承受不了牛群,于是,牛群数目开始大量减少。所有聪明牧民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大家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悲剧的产生在于每一个人都陷入了一个体系而不能自拔,这个体系迫使他们每个人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无限地增加自己对资源的使用,毁灭成为大家不能逃脱的命运。80年代的中国有句著名的民谣: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不拿白不拿,白拿谁不拿。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公地悲剧最好的例子和说明。
英国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是“圈地运动”。一些贵族通过暴力手段非法获得土地,开始用围栏将公共用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由于土地产权的确立,土地由公地变为私人领地的同时,拥有者对土地的管理更高效了,为了长远利益,土地所有者会尽力保持草场的质量。同时,土地兼并后以户为单位的生产单元演化为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劳动效率大为提高。英国正是从“圈地运动”开始,逐渐发展为“日不落帝国”。
草地属于公有产权,零成本使用,而且排斥他人使用的成本很高,这样就导致了牧民的过度放牧。我们当然不能再采用简单的“圈地运动”来解决“公地悲剧”,我们可以将“公地”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比如有两家石油或天然气生产商的油井钻到了同一片地下油田,两家都有提高自己的开采速度、抢先夺取更大份额的激励。如果两家都这么做,过度开采实际上可能减少它们可以从这片油田收获的数量。在实践中,两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达成分享产量的协议,使从一片油田的所有油井开采出来的总数量保持在适当的水平,这样才能达到双赢的目的。
有人可能说,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就必须不断减少“公地”。但是,让“公地”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公地”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政府制定严格的制度约束,将管理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这样,在“公地”里过度“放牧”的人才会收敛自己的行为,才会在政府干预下合理“放牧”。
所有人都是利己的人,我们不能将“公地悲剧”的所有罪责推脱到人的本性上。其实,只要建立合理的制度,顺应人的利己心,同时规范人的行为,就一定能促使“公地”获得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