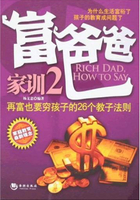有的时候,他觉得,先帝更像一个将军,果断冷酷。
先帝共有三子一女。陛下是先帝的二子,从小陛下就乖巧聪明,深的先帝的喜爱,十岁的时候就封了太子,十五时,将自己视若珍宝的侄女程后交付于他。陛下十六岁时于程后成亲,十九岁登基。
陛下的二个兄弟在先帝蓖之前,联合外戚……企图篡位,这就是最有名的“亲幕杀之变。”一时间,先帝心上,不久便离去了……
离去那夜,先帝曾独自与陛下谈论了许久……
仁慈太后,陛下的生母。随先帝去时,依旧隔了近五年……这期间,陛下和程后正是大婚……婚后三年……直到软禁二年……再几年后……太后去……
这一切,似乎有一种关联……
直至今夜,他才猛然的联想起来……
陛下登基才开始中用他,记得,他曾侯在太后的‘五德殿’外,那时候,他还不得陛下的信任,那时候……他心思虽然老诚……却想得不多……
隐约,太后苍老的声音响起:“本宫几年前说过。你要留她,就要过寄给个孩子。没有孩子。什么都不可能。”
陛下的话,他到想先依旧能回想起来。一向自制力极强的陛下竟然失控的大叫:“可朕爱她。”
“啪”
殿内传来一陶瓷的破碎声。
“朕?你还知道你是个皇帝?爱她?爱她有何用?”这是太后的声音:“你想让她背上罪名去死是吗?”
他们吵了很久,争执到深夜……
最后的最后,是太后的声音:“既然,你这么倔强。本宫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过去。倘若她没有容人之量,你……看着办吧。”
“呀——”
殿门的四扇同时打开,刘紊铁青着脸走出来,大步离开,安也未请。他紧随其后,突然。刘紊转身冷冷的问道:“你在外听见什么了?”
他把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奴才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忘记它。”刘紊最后的声音便没了。
从那日起,陛下就未踏入云秀宫一步。
赵后成了他的新人,他每日的和她在一起,自制那日,程后突然而至,他依旧站在殿外,眼观鼻,鼻观心。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为什么?”那绝色女子柔柔弱弱的带着哭腔。
“你说话啊……”半天的沉默后,程后道。
“你为何没有一丝的容忍之量呢?你是皇后……而且,朕这么做,一切都为了你啊。绾绾……你可明白?”刘紊当时的声音出奇的温柔。带着许多的无奈……和一丝的绝望。
“为了我?为了我什么?为了我去宠幸一个宫女?让她为你生儿育女?为什么?为什么?”她失控的大叫:“我爱你……好爱好爱你……你说过的……你只喜欢我一个得……你说过的……”
“绾绾。”他的语气有些暴怒。呵斥一声:“够了。”
“没够,没够!你说过让我为你生宝宝的……生很多很多的宝宝……你为什么不让我为你生宝宝呢?”她有些颤抖的继续说:“我好像有个你的宝宝。”
一时间没有说话。
“不要碰我,碰了其他女人的脏手,不要来碰我。”程后的声音有些生气。
“你为何总是这么任性?”陛下的声音已经平静的听不出任何情绪。
“我没有任性,我只是爱你……离开她好不好?她只是个宫女。”她的声音带着怜悯的祈求。
他很长时间没有听见大殿内的对话。
突然的,没有预兆的。刘紊甩袖而去,不顾身后绝望的呼唤。
同样的绝望,那高高在上的帝王也有。
辗转一番,扬才问睁大眼睛……
良久,他的屋子里传来他的叹息声:“娘娘啊——你是自找的。”
你给了自己绝望,却给了他人生的希望。倘若你……那云秀宫的主人岂会是她?说到底,这情字害人啊!
张蝶舞母病危,刘紊特下圣旨,命她好生伺候,以敬孝道。
那日,张府围满了众人,纷纷感叹,这么大的排场,张家的女儿果然在宫中受宠。也不知是羡慕,还是嫉妒。围观的人们一群热闹的呼喊。
当张蝶舞走下八人大轿时,一声粗气的男子喊道:“还不跪下,拜见娘娘。”
众人纷纷下跪,高声唤道:“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她环视一周,带着静谧的微笑,朝满地的人影喊道:“众人都起来吧。这样太客气了。”刘紊并没有对她进行任何的封赐,依旧是个“张小姐”的身份。其中的原因她隐约知道一些……眼下,受到娘娘的礼节来,她心里不知做和感想,不由自主的朝方才那男子看去。
他是文成宫的御前侍卫,刘紊派他来护送自己,真的十分给她面子。听他肯定自己的身份,她心里一喜。这定是刘紊嘱咐的。
款款下轿,小心的护住胎儿,由宫女扶起超“张府”走去。
张府门口,齐齐跪下一整片。扫视过去,估摸府上所有的人都来了。为首的张嵌恭敬道:“请娘娘入府。”
“爹爹。”张蝶舞并未扶起他。轻唤一声。“走吧。”
“娘娘?”推开房门,刺鼻的药味不禁让张蝶舞眉头微皱,一旁的宫女立即拉住她,附耳轻声道:“娘娘,还是莫要进去了,小心孩子。”
张蝶舞有丝丝犹豫,瞟眼见自己的父亲面色一变,柔声道:“没事。命人打开门窗,透透气就成。”
宫女还想说什么,被她禁止。不悦道:“我是回家看望重病的母亲,你这样。叫我怎么以敬孝道?”
宫女被她说的不敢吱声,面色煞白。三年来,她一直伺候着张蝶舞,自然对她的性子了解,方才所说本属实意,不料被她呵斥一通,有些委屈。她,必定年纪还小。观测人心的事情,她亦还要好好学习一番才行。
经她这么一说,一群侍卫立即打开了窗户和四扇房门,渐渐的,房里的药味快要散去,隐约可闻。张蝶舞似要等药物尽除才如屋,站在门外朝父亲看去。见他脸色带郁,心里有些尴尬,脸上立即挂上笑:“爹爹?方才我怎么没有瞧见两个哥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