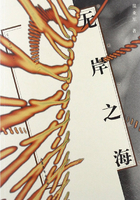罪魁祸首是谁?除了那扬言要报复的疯子,谁还会这么卑鄙?有了第一次,是否还会有更严重的报复?也许这次挑衅仅是报复的开场白吧。
上尉向父亲报告了事情的始末后,来到了特梅丝瓦尔公寓。
可以想象,哈拉朗上尉是多么愤怒。
“一定是那个无耻之徒干的,”他叫嚷道,“一定是他!他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但他不会就此罢手的,我也不会任他胡作非为!”
“要冷静,亲爱的哈拉朗,”我劝他,“别感情用事,那只会使问题复杂化!”
“亲爱的亨利,如果在那个无赖离开之前,父亲通知了我,或者当初听我的,我们早就摆脱他了!”
“亲爱的哈拉朗,我总以为,最好不要鲁莽行事。”
“如果他继续胡作非为呢?”
“警察会有办法的,多为您母亲、妹妹着想吧!”
“她们也许知道这事了。”
“不会有人告诉她们,还有玛克……等婚礼结束后,我们再想对策……”
“婚礼结束后?”哈拉朗上尉说,“不会太迟了吗?”
当天,罗特利契家每人都忙忙碌碌,准备着晚上的订婚宴会。罗特利契先生和夫人盼望,用法国人的说法,“把婚事办得体体面面的”。医生发出大量的邀请函,邀请拉兹城内的朋友们。在这片“中立地带”上,马扎尔贵族和军政要员、商界人士将齐聚一堂。拉兹城的总督与医生也是老朋友了,自然也会光临祝贺,为晚会添彩。
大约有150名宾客出席订婚宴,如果客厅、花厅的面积不够大,这么多来宾还真是个问题。晚会结束时,还将在花厅里准备了晚宴。
米拉·罗特利契为了得体大方,真是煞费苦心,玛克也没忘了表现自己,想方设法地把他的艺术风格表现出来。事实上,他早就这么做了。米拉是马扎尔人,但凡马扎尔人,不论男女,均对服饰十分讲究。这已渗透到血液里,就像他们对舞蹈的狂热。因此,我对米拉小姐的评价,也适用于诸位男士、女士。订婚晚会上将会百花争魁,令人眼花缭乱!
下午3点钟,万事俱备,我整天都呆在罗特利契家中,就像出嫁的新娘,焦急地等待着花轿来临的时刻。
偶尔,我站立在窗口前,伫立眺望着多瑙河畔,却意外地看见威廉·斯托里茨,好心情一扫而光。他偶然路过此地?可能不是。他低着头,沿着堤岸慢吞吞地走着。当他走近罗特利契家的府邸时,猛地抬起头,从他眼中射出一道光芒,是那样的令人毛骨悚然!他在附近来回走去,最后,引起了罗特利契夫人的注意,她认为应该告诉丈夫。医生听后,安慰她,叫她放心,但仍对威廉·斯托里茨来访之事只字未提。
有必要告诉大家一点,晚上我和玛克返回特梅丝瓦尔公寓时,又在马扎尔广场上遇见他。他看见我弟弟,突然停了下来,不知所措,像木头一样站着,脸无血色,两臂僵硬……他会晕倒在广场上吗?他那双喷着怒火的眼睛恶毒地盯着我弟弟。
我们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向前走去。
“你留心到那人了吗?”玛克问我。
“看到了。”
“他就是威廉·斯托里茨……”
“我知道。”
“你怎么认识他?”
“哈拉朗上尉指给我看过一、两回。”
“我以为他不在拉兹了。”玛克说。
“看来没有,否则,就是他又回来了。”
“随便吧!反正要结婚了。”
“只有如此了。”我小声附和着。
事实上,如果威廉·斯托里茨不在拉兹,订婚宴将会更热闹。
大约在晚上9点钟,自从第一批车子来了以后,客厅开始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医生夫妇和米拉站在花厅门口迎接宾朋。不久,总督大人也到了,万分真诚地向主人道喜,米拉小姐尤其受到他们欢迎,我弟弟也沾光不少。玛克和米拉被祝贺之辞包围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辉。
10点钟左右,受邀的宾客全部到齐。
尽管我看到上尉心事重重,但仍不失待客之道,热情地接待着来宾。衣着华丽的妇女们,在男人们的黑色礼服衬托下,宛如黑空中发光的恒星。医生工作室里摆满了精美礼品,昂贵的珠宝首饰,珍贵的小古玩,尤其是玛克送的礼物,显示出不凡的艺术风格,令客人们赞不绝口。大厅靠墙的桌上放着一束娇艳的玫瑰和橙花,这是订婚花束。根据马扎尔人的风俗,在花束旁边的一块丝绒方垫上搁着花冠,米拉在结婚那天上教堂时就要戴上这顶花冠。
晚会节目分音乐会和舞会两部分,舞会在很晚才会开始,这么晚,令大部分宾客感到遗憾,因为,我再重申一次,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比跳舞更能令匈牙利男女老少狂热的了!
匈牙利人深深地被音乐的独特魅力所吸引,根据一项公平的答卷,匈牙利人热爱音乐。根据一项比较公正的评价,匈牙利人与德国人在欣赏音乐的方式上有明显的区别。马扎尔人只是音乐爱好者,不是音乐家,他们不唱歌,要么也唱得很少,他们重在欣赏。如果演奏民族音乐,听,不仅是一件庄严的事情,也可以从中得到无限乐趣。我敢肯定,马扎尔人在这一点上是首屈一指的。吉普赛人,这些天生的波西米亚乐器演奏家,最擅长于撩拨听众内心的爱国主义激情。
整个乐队由十三个人组成,他们将要演奏雄伟的《匈牙利妇女》,这是一首军队进行曲。马扎尔人是实干家,他们喜欢此类音乐胜过德国的梦幻曲。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不挑选具有喜庆气氛的乐曲呢?因为匈牙利是一个注重传统的国家,而放喜庆的音乐有违传统。匈牙利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旋律,如同吉普赛人热爱他们的“佩斯玛”,罗马尼亚人钟爱他们的“杜瓦玛”,同样道理,他们需要激昂奋进的乐曲、节奏慷慨无畏的进行曲,这些音乐能唤起他们对战争烈士的怀念,并且颂扬先辈们的卓着功绩。
在四种弦乐器、低音乐器及中提琴的演奏下,乐曲的主旋律开始了,小提琴、笛子和双簧管的伴奏如梦如幻。两名乐师拨弄着洋琴上的金属琴弦,发出醉人的乐音,沁人心脾,纯属仙乐。
尤其是乐队的保留节目,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美的音乐,它引起了强烈反响。来宾们如痴如醉,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中。演出结束,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即使演奏通俗乐曲,也格外受欢迎,其中有《罗卡之歌》和《特兰西瓦尼亚进行曲》。乐队高超的演奏,足以唤起整个普斯陶的共鸣。
乐队演出结束了。置身于马扎尔人中间,我感到莫大的快乐。
在乐队演奏的短暂间歇中,远方多瑙河的淙淙流水声传入我耳畔。
我不敢肯定,新奇的音乐是否吸引了玛克;但我敢说整个灵魂都沐浴在更为温柔、更为亲密的“米拉乐”中,他们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对方。
最后一阵掌声平息后,乐队指挥及乐师们起身回礼。罗特利契医生和哈拉朗上尉向他们表示了诚挚的谢意;他们深为感动,然后退场了。
音乐演奏完以后,有一段休息时间。这时,客人们离开座位,寻找着相识的人,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圈子。
有些来宾分散在灯火通明的花园里,仆人们端着装有清凉饮料的托盘在人群里忙碌不停。
晚会节目进行到此刻,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我想,说实话,如果我开始还有所顾虑,心中时常掠过不祥的阴云,那么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该放心了。
因此,我满腔赤诚地向罗特利契夫人祝贺。
“谢谢,维达尔先生,”她回答道,“这是一个祥和而快乐的夜晚。但在这么多欢乐的人当中,我眼中只有我最爱的女儿和令弟!他们是多么幸福的一对啊……”
“夫人,”我说道,“您是这幸福之源……这也是作父母期望能得到的最大幸福。”
不知为什么,这句很普通的话却使我想到那个威廉·斯托里茨。哈拉朗上尉是真的不担心那人的威胁,还是只不过故作坦然状?我无从考究。他在人群里来往应酬,以他诙诣的谈吐感染着周围的人,许多匈牙利少女被他吸引得神魂颠倒,他也很得意能得到大家的喜爱,可以说,全城的人都想借此机会向他家表明心意。
“哈拉朗上尉,”当他经过我身边时,我对他说,“下一个节目也一样精彩?”
“当然!”他大声说,“音乐很美妙,可舞会更迷人!”
“呃,”我又说,“法国人不会输给马扎尔人的……我有幸请您妹妹跳第二轮华尔兹……”
“为什么不跳第一轮?”
“第一轮?那是玛克的专利……无论从传统上看还是从权利上看!别忘了玛克,你想他会允许吗?”
“您说得对,亲爱的维达尔。那就由那对未婚夫妻开舞吧。”
舞会伴奏的乐队已坐在花厅的里端,医生的工作室里摆了几张桌子,这样,那些不跳舞的客人可以在桌上打牌消磨时光。
乐队正准备演奏。突然,从花厅另一头,它的门朝着花园,正虚掩着,——远远传来一个很刺耳的声音。有人在唱一首外国歌曲,节奏很古怪,没腔没调,听不出任何旋律。
准备跳舞的人都停了下来,仔细倾听着。难道这是为晚会准备的助兴节目吗?
我走到哈拉朗上尉身边。
“怎么回事?”我问他。
“不知道。”他答道,语气中明显透露出内心的恐慌。
“也许是从大街上传来的?”
“不……我想不是!”
实际上,歌声一定是从花园里传出来的,它离花厅越来越近了……可能唱歌的人正向花厅走来?哈拉朗上尉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客厅门口。
花厅里只有十来个人,不包括花厅里端的乐队。其他客人都聚集在客厅里,去花园的客人早已回来了。
哈拉朗上尉走上台阶……我跟着他。我们环视亮如白昼的花园。
一个人也没有。
罗特利契夫妇也来了,医生问儿子:
“怎么回事?”
哈拉朗上尉作了个表示不知情的动作。
歌唱的声音依然回响在四周,更加响亮,更加粗暴,越来越近。
玛克挽着米拉小姐,来到我们身边。一群女人围着罗特利契夫人,问东问西,夫人无言以对。
“我知道,跟我来。”哈拉朗上尉叫着,冲下台阶。
医生、我,还有几个仆人跟了上去。
忽然,歌声嘎然而止。很显然,唱歌的人离花厅只有几步远。
花园搜查过了,树丛也翻遍了;花园里灯火辉煌,没留下一丝阴影……仍没发现人。
难道是戴凯里大街上的流浪者在唱歌?
但是,医生也去查看了大街,街道上空无一人,寂静无声。
惟一特别之处,就是在远处的斯特里茨家,有束若隐若现的灯光从窗口射出来。
我们又回到花厅,面对客人的疑问只有推说不知何故。
舞伴们重新站好位置,哈拉朗上尉示意舞会开始。
“亨利,”米拉小姐笑着对我说,“您选好舞伴了吗?”
“我的舞伴就是您,小姐,但只能等待第二轮华尔兹了……”
“哦,亲爱的亨利,”玛克说,“我们不会让您久等的!”
乐队刚奏完施特劳斯的一首华尔兹舞曲的前奏曲,歌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歌声是从客厅里发出的。
宾客中一阵骚乱,他们被激怒了。
原来,这次竟唱的是德国国歌,即弗莱德里克·马尔格拉德的《仇恨之歌》,这简直是对马扎尔人的爱国主义感情的公然挑战,肆意的侮辱嘛。
令人讨厌的歌声响彻整个大厅,但却偏偏看不见唱歌的人!但可以肯定,他就在大厅里,只是没人能看得见他!
跳舞的舞伴们都分开了,涌进了客厅和花厅。一阵不安情绪攫住了每一位来宾,尤其是妇女。
上尉火冒三丈,紧握住拳,横穿客厅,像要逮住那个无形的家伙。
突然,歌声又止住了。
这时,我看见了……是的!大家都亲眼目睹,简直难以相信……放在靠墙角桌上的订婚花束,突然腾空飞起,被撕碎,花屑飘落在地板上,一朵朵花瓣惨遭践踏……所有的人,都被吓呆了,不知所措。每个人都想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我呢,看到这情景,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头脑清醒。
哈拉朗上尉找到我,他气得面无血色,对我说:
“是威廉·斯托里茨干的。”
威廉·斯托里茨?难道他真有超凡的能力?
此刻,新娘花冠也离开了方垫,穿过客厅、花厅,消失在花园的树丛中,没人看见一个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