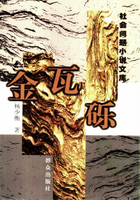有勤姑每天煎药侍奉,几个月的功夫,芸姑妈的身子渐渐地好起来了,我爷爷看到女儿的面色一天天变得红润,又听说中午芸姑娘也能吃一小碗饭了,高兴得每天晚上都要多喝两盅。我母亲看着芸姑娘想吃东西,就自己下厨给芸姑妈烧了一道清蒸鲥鱼。我母亲烧的清蒸鲥鱼和别人烧的不一样,别人家清蒸鲥鱼都带着鱼鳞清蒸,我母亲烧清蒸鲥鱼,则要把鱼鳞剥下来。这里,美食家们就要耻笑了,鲥鱼的味美,就是因为鱼鳞上的鱼油清香,把鱼鳞剥下来,鲥鱼还有什么吃头呢?对了,这就算说到学问上来了。我母亲烧清蒸鲥鱼,确实要把鱼鳞剥下来,但她剥下鱼鳞之后,并不是把鱼鳞扔掉,我母亲要把剥下来的鱼鳞用丝线穿成一串,然后再把这串鱼鳞挂在蒸笼顶上,和锅里的鲥鱼一起蒸。这样,等鱼鳞上的油全蒸出来之后,鲥鱼也就蒸熟了,这时候那鱼鳞里面的油也就一滴一滴地全渗到鱼肉里面去了。这样蒸出来的鲥鱼是什么味道,诸君,你们是吃不到了。
晚饭的餐桌上,有勤姑照顾着芸姑妈用饭,我母亲还把最嫩的鱼肚给芸姑妈挟到了面前,我爷爷、我奶奶看着芸姑妈吃得那样香,一个劲地光是笑,连饭都顾不上吃了。看着芸姑妈吃过饭,又让她在上房里休息了一会儿,我奶奶看过说是汗已经退下去了,这时,才由勤姑搀扶着,由我母亲亲自护送回房去了。
把芸姑妈送回房里之后,我母亲又回到前面用过饭,看着我爷爷和我奶奶回房去了,我母亲才回到自己的房里来。每次我母亲回到自己房里来的时候,桃儿、杏儿要到门槛外迎接,今天她们自然也是出来了,但是我母亲觉察出她两个人的脸色不象往日那样高兴,一个个还避开我母亲的眼睛,明明是有什么事情怕我母亲知道。
什么事情呢?我母亲当然也不会问她们,我母亲知道,真有了重要的事情,不用我母亲询问,她们也就要向我母亲禀告的,既然她们不说,那也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们也回房歇着去吧。”
我母亲说过话之后,桃儿和杏儿还是站在我母亲的身旁,一点要离开的意思也没有。这时,我母亲倒先噗哧一下地笑了:“怎么今天就有了规矩呢?你们不回房去,我也没法休息呀。”
“奶奶。”看着我母亲一点也不想追问她两个今天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倒是桃儿忍耐不住,她先向我母亲说起了话来。“桃儿放肆,有句话,可不知当说不当说。”桃儿说着,眼睛还向我母亲看着,明明是察颜观色,揣度我母亲的心意。
“桃儿真是多想了,你和杏儿虽说原来是奶奶房里的人,可是这几月的时间在我房里,我拿你们就当是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有什么事情,你们不说呢,我也不会追问,你们愿意告诉我呢,这说明你们不和我隔着心。”我母亲说着,就把桃儿和杏儿的手握在了手里,这一下,桃儿和杏儿才有了勇气,她两个互相看了看,这才对我母亲说起了话来。
“这几天,我一直和杏儿在暗中商量,不知道这事情该不该和奶奶说,说吧,也许就是我们的猜疑;再说,一个丫环,在府里侍候着主子做事,本来不该看的就不应该看,不该说的,那就更不应该说了。”桃儿绕来绕去,就是不往正事上说。这时倒是杏儿在一旁听得着急了,她打断桃儿的话,抢着对我母亲说道:
“奶奶别怪桃儿姐姐多嘴,这事是我撺掇桃儿姐姐说的。就是说错了,奶奶也就怪罪我一个人是了。”
“听你们这样一说,可真是怕死人了。”我母亲看着两个孩子太紧张了,就故意把气氛缓和一下,我母亲笑了一下,随后就对桃儿和杏儿说道:“回房休息去吧,这府里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说着,我母亲就要把她两个往门外推。
“少奶奶,这话今天不说出来,我们两个就没法睡下。”桃儿还是立在我母亲的身旁,万般为难地说着。
“好吧。”我母亲索性坐了下来,极是严肃地对桃儿、杏儿说着,“这房里就是咱们三个人,你们若是信着我呢,有什么话,你们就只管对我说,我绝对不会把你们今天对我说的话传出去,你们若是信不得我呢,我怎么说呢?你们总不能让我起誓吧。”
“少奶奶快不要这样,我们也想过了,无论奴才们说的话对不对吧,反正我们是一片忠心。”桃儿终于下定决心,要对我母亲说她认为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少奶奶。”看我母亲坐好要听她说话,这时桃儿就更是严肃地对我母亲说着,“也是府里把我们宠得不知天高地厚了,本来,做奴才的怎么可以如此放肆呢?这若是在老老年间,那是要用家法惩治的……”
“唉呀,你再说这些绕弯儿的话,我可是就不听了。”我母亲还是半玩笑地对桃儿说着。
“好,那我就直说了吧。”终于,桃儿拿定了主意,她鼓足了勇气对我母亲说道,“少奶奶,半个月之前,我和杏儿一起侍候老祖宗去中国大戏院看戏,就是宋燕芳唱的那出《教子》,上装之前,宋燕芳到包厢里来给老祖宗请安,随后老祖宗让大先生送她下楼。少奶奶,这可不是奴才故意察看什么人,就是无意间一抬头,奴才正看见大先生和宋燕芳走到楼梯拐角的地方,也是那地方灯黑,又没有人,你猜猜奴才看见了什么?奴才看见大先生和宋燕芳两个人手儿领着手地往偻下走呢。”说完,桃儿抬手拭了拭额上的汗珠,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似是就等着我母亲发落了。
我母亲听过桃儿的话,先是怔了一下,但没过多少时间,我母亲倒噗哧一声地笑了。“看你说的,一定是你看花了眼,包厢离楼梯拐角那么远,你怎么就会看得那么真呢?好了,好了,就算你们什么也没看见,也算你们什么也没对我说。都给我下去吧。”
“少奶奶,再容我们说一句话。”这时,杏儿站了出来,对我母亲说着,“就算是奴才看错了,可是奶奶想想,宋燕芳整天整日地在府里呆着,她算是哪一道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一天不嫁,就是她一天在打侯姓人家的算盘。少奶奶是名门闺秀,不知道象宋燕芳这样的人,心里是一个什么世界;我们身为奴才,对这种人就看得比少奶奶要清楚得多。我们是少奶奶房里的人,侍奉着少奶奶享荣华富贵,是我们做奴才的本份,有少奶奶的庇荫,我们也才有来日的好时光……”
“唉哟,杏儿,你这嘴可是真能说。”我母亲打断杏儿的话,还是玩笑地说着,“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一个奴才,我会有什么话要说呢?少奶奶拿我们当自己的孩子看待,我们才敢放肆地这么没大没小信口胡说,少奶奶拿我们当小奴才使,我们就只有好好做事的份儿了。”杏儿还是摇着她那三寸不烂之舌,转弯儿抹角地对我母亲说着。听到这时,我母亲已经感觉到这事的严重了,索性她变得严肃了起来,向桃儿、杏儿问着:
“有什么主意,你们就说吧。”
“有少奶奶的示下,我们也就敢说了。”最先说话的是桃儿,她比杏儿大几岁,凡事就要抢在杏儿前面。“一定要想个法儿对老祖宗说,快码儿地把宋燕芳嫁个人家。”
“哟,你真是说话气壮了,人家宋燕芳又不是咱们侯姓人家的人,老祖宗怎么能给人家做主呢?”我母亲打断桃儿的话,向桃儿说着。
“少奶奶今天先休息,这事,我们两个人去合计,不用少奶奶出面,也许事情就办成了,到那时宋燕芳嫁给了一个什么人家,就是她再长在侯家大院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了。”说罢,桃儿、杏儿又侍奉着我母亲睡下,她两人这才离开我母亲的房间,回到她们自己的房里去了。
第二天下午,估摸着勤姑正在给芸姑娘煎药,桃儿和杏儿一起来到了芸姑娘房里,她两个凑到勤姑的身边,极是知心地对勤姑说道:“早就想着过来向勤姑学着煎药的,总也是赶不巧时间,听少奶奶说勤姑在马府里的时候,就是侍奉着马老太太用这种药的,说是补养身子可好着呢。”
勤姑是一个实心眼儿人,还以为她两个真是向自己学煎药来的呢,于是就正儿八经地向她们介绍这些药的药性,还告诉她们如何看火,如何调药,又该如何收汤。桃儿、杏儿倒也做出认真听的样子,但待勤姑说了一会儿,她两个就和勤姑扯起家常话来了。
话题自然是由宋燕芳引出来的,杏儿问勤姑,那天晚上行酒令,你看没看出来我们两个人故意和宋燕芳做难?勤姑当然也不呆,她怎么会看不出来呢?这时,勤姑就向桃儿和杏儿问着:“你们总捉弄人家做什么?一个做艺的,好不容易巴结上侯姓人家,每天到府里来,编着法儿地哄着老祖宗、少奶奶、姑奶奶开心,够可怜的了。”
“她可怜?”杏儿抢先打断勤姑的话,挥着一双手骂道:“她才不是东西了呢,毒蛇!”
“姑娘家,可不兴恶语伤人。”勤姑还是一面煎药,一面无心地和她两个说着。
“勤姑,你是不知道,这个宋燕芳一直在打咱们大先生的鬼算盘。”桃儿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向勤姑道明了事情的真相。
“这话,可不能乱说。再说,我们姑奶奶已经是侯姓人家的长门长媳了,她宋燕芳还能打什么鬼算盘?”勤姑不解地问着。
“勤姑,你是不懂得这些事的。”杏儿嘴快,她看着桃儿要说话,一伸手就把桃儿推到旁边去了,自己抢着对勤姑说,“你知道吗,以大先生这样的地位,她可以有正房,也还可以再立个偏室。”
“噢,侯姓人家有这个规矩?”勤姑抬起头来问着。
“这种事,哪里有立规矩的?可是先辈有人这样做了,后人就可以跟着学。再说,这天底下的事,好事,要先立规矩后做,坏事,则全都是先做出来、然后才立规矩的。以宋燕芳那样的人,打死她,她也不敢梦想做正室少奶奶,可是如今有了正室少奶奶,她可就要想着高攀做二房了。”
“哦,这事可是重要了,我这就对我们姑奶奶说去。”说罢,勤姑站起身来就要走,她说的“我们姑奶奶”,就是我母亲,因为勤姑是我母亲从马家带过来的人,就是到了侯家,她和我母亲的关系,也还是按照在马家时候的规矩论定。
“早晚了三春了。”桃儿将勤姑拉住,对她说着,“我们早就对少奶奶说过了。明说了吧,今天我们找到你这里来,就是想和你一起商量一个对策的。”
“唉呀,咱们做奴才的,能有什么对策呀?”勤姑万分紧张地问着。
“明说了吧。”杏儿回身把房门关好,索性向勤姑把话说透,“这儿没有外人,侯家大院里,主子当家,奴才画道儿,若不,各房各院里养着这么多的奴才做什么?奴才,就是主子的眼睛和耳朵,给主子通风报信,给主子出谋划策,出了事,还得替主子受过,到了掉脑袋瓜子的时候,你就得先把人头伸过去,明白吗?这就是做奴才的本份。”
“唉哟,听着可是够怕人的。”勤姑来自马姓人家,诸位知道,马家是书香门第,祖辈上出过进士,先人还是桐城派作家群中的一员主将,在人家马家,是没有这些乌七八糟污浊事的,所以类如认干女儿,收二房之类的事,人家勤姑那才是闻所未闻哩。
“遇见这种事,你怕也不管用,一事当头,你就得想个办法。”杏儿一板正经地对勤姑说着。
“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勤姑为难地问着。
“这样,这房里只有咱们三个人,咱们也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这件事咱们若是不管,日后宋燕芳真把大先生缠住,也没有咱们的好日子过;咱们若是管了呢?有成,自然也会有败,万一事情败露出去,老太爷发落下来,咱三个就要被一起赶出大门。可是少奶奶对咱们三个人这样好,咱们不帮少奶奶一把,于心也是说不过去。”杏儿说话的声音那样重,就象是密谋兵变一样,听得勤姑直打冷战。
“如今一根线儿上拴着咱们三个蚂蚱,成了,大家一起托少奶奶的福,不成,替主子受过,主子日后也不会亏待咱们的。”桃儿把利害关系向勤姑交了底儿。
“咱三个人也不用盟誓了,有话咱就明说吧。”杏儿一挥手,算是下定决心了。
“可是,可是,若是伤害燕芳姑娘,咱们说到哪里也是不能去做的。”勤姑见她两个说得这样可怕,便错以为桃儿和杏儿今天找到她的头上来,是想把宋燕芳推到井里去呢,于是勤姑事先说明,搞个暗杀呀什么的,她坚决不干。
“谁也不是让你去做那种红刀子、白刀子的事。”杏儿看勤姑吓得全身打战,就缓和一下空气,对勤姑说。
“行,只要不伤人就行。”勤姑终于放心下来了。
“这事,说起来怕人,可是做起来,还是一件喜喜庆庆的事呢。”桃儿到底是大姑娘了,她拉着勤姑坐下,又帮着她照看着锅里煎的药,这才说到了正题。“我们是这样打算的,咱们三个人要一起撺掇着老祖宗早早地给燕芳姑娘说个人家,她嫁出去了,自然就再也成不了大先生房里的人了。”
“我的天,老祖宗怎么会听咱们奴才的话呢?”勤姑虽然放下心来,知道这事并不十分可怕,可是撺掇老祖宗给宋燕芳说亲,勤姑又觉得不可能了。
“老祖宗虽然不会听咱们的话,可是老祖宗听一个人的话。”杏儿靠近到勤姑的耳边,对勤姑说着。
“听谁的话?”勤姑问着。
“芸姑娘。”杏儿回答勤姑的话说。
“哦,明白了。”勤姑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她一听就听出门道来了。“你们是让我在芸姑娘的耳边放风,就说宋燕芳在打我们姑老爷的主意,让芸姑娘撺掇老祖宗给宋燕芳找人家。”
“唉呀,勤姑姐姐,你真是个聪明人,怎么你才听了半句话,就把事情听明白了呢?”说着,桃儿和杏儿一起把勤姑抱住,拉她在房里打转。
“别混闹,当心锅里的药沸出来。”勤姑挣脱桃儿、杏儿的纠缠,一面整理头发、一面对她两个说着。
沉静了一会儿,勤姑似是想起了什么事,便又向桃儿和杏儿问着:“我们姑娘若是问,就算是撺掇得老祖宗动了心,可是又该把燕芳姑娘说给谁家呢?”
“人家当然是早就想好了,不把事情想周全了,我们怎么敢惊动勤姑姐姐来呢。”桃儿和杏儿一起向勤姑做了一个鬼脸儿,表示她两个早就胸有成竹了。
“你们两个人呀,真是一对小人精!”说着,勤姑伸出一根手指,先在桃儿的鼻子上点了一下,随后又在杏儿的鼻子上点了一下,然后,她三个人就一起开心地笑了。
芸姑妈到我奶奶房里坐了好几天,终于才把给宋燕芳说人家的事,向我奶奶说清了,我奶奶一听,当即就拍了一下手掌:“唉呀,你瞧,真是咱们偏心了,咱们只知道自己的孩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怎么就把人家孩子忘记了呢?”说着,我奶奶就做起了自我批评,还一个劲地说对不起人家宋燕芳。可是,应该给宋燕芳说个什么人家呢?“咱也不能对不起人家孩子呀。”我奶奶又对芸姑妈说着。
这时,我的芸姑妈就向我奶奶推荐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侯家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