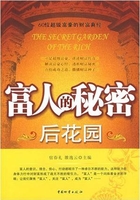“回到柳条通里,我俩享受几天。”她说。
生命最后的三天里,鸳鸯在柳条通里,太阳、月亮公正地照射他们,风过柳林气味有些苦涩,他们爱恋这个美丽世界,但是不得不离去。缺乏活下去的勇气,他们选择了卧轨,让沉重的钢铁从身上碾过……张建国跟老伴到了现场,见到车轮和钢轨齐刷刷切断的四块大军和农村姑娘。多少年过去,他们都没抹去心灵震颤的记忆。
胖婶在儿子死后,成为媒婆,到处给人介绍对象,十几年里巳经成了很多对。
大军的故事对做父母的是教育,张建国两口子引以为诫,在儿女的婚事上不深管,征求意见就提意见供参考,最后的主意自己拿。当年大儿子景山与丛天舒的婚姻就是这样。他劝老伴说:“事巳至此,他们两人都同意,你还别什么劲,别得住吗?天舒年纪这么轻,能永远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早晚要改嫁,你说嫁给景云有什么不好呢。”
“他们是叔嫂啊!”张母的症结在这里。
“在过去呀,嫂子嫁给小叔子风俗也允许,何况当今……”
“中啦,你当爹的同意,我当娘的说啥也没用,反正是你们张家的事……”
“瞧瞧你还是不满意嘛!可你想想你的两个宝贝孙子,天舒带他们嫁给别人,你不怕继父给他们气受,景云给他们当爸爸,张家的血脉在,你不用操心啦。”张母心里服嘴不服道:“怎么说也好说不好听,你准备吧,成天让人背后讲得脸发烧!”
“我多准备退烧药!”张建国诙谐道,“今晚天舒回来,你把咱俩同意的意见告诉她。”
“还是你告诉她,我可张不开嘴。”
“好,我说。”张建国说。
大姐决定嫁给小叔子,丛家姐妹站出来反对的是天霞,她说服不了大姐,就叫来了弟弟丛天飞。
“咱姐受穷的命,放大款儿不找,偏偏嫁给小叔子。”丛天霞气哼哼地说。
“说什么二姐,大姐要嫁给张景云?”丛天飞惊讶道。
昨天丛天舒跟二妹说她的决定,说:“天霞,我打算和景云结婚。”
“什么?跟他结婚?”丛天霞惊讶道,“你还动真格的呀!”
“初步定在明年五一节。”
“亲大姐呀,你怎么啦?”二妹无法理解她的决定。
“我怎么啦?”
丛天霞觉得大姐改嫁正常,只是要选择正确,带着两个儿子,他们将来要读书,要就业,要娶媳妇,处处需要钱,对方的经济实力必须考虑。张景云哪有能力养活她们娘仨?当然凑合着能过,可是那是什么日子啊!
“景云人倒不错,很有责任心,正是大姐理想的大山大树男人。”
丛天飞的看法跟二姐不一样。
“大山大树怎么样,顶钱花?大山大树也不如大钱,姐错过了当富太太的机会。你说,张景云有钱?”
“钱肯定没有,二姐,你说的大款是谁呀?”
“是谁,说什么都晚啦,大姐去向人家道别。”丛天霞说。
二妹听说大姐要嫁小叔子极力劝阻她,从几个方面讲不合适。
“天霞,你别说了,姐决定啦。”
“姐,我问你,那个赵老头有什么不好?”
丛天舒摇摇头,怎么不好她说不出来,通常人们说的没感觉吧。财富对她是诱惑,最终给她断然抛弃了。至于小叔子怎么好,也不是。同样没什么感觉。她把赵兰田的追求和景云的追求目的做番比较,发现了差异,赵兰田六十多岁,想得到的是比他小几十岁女性的身体;景云比自己年龄还小得多,想得到跟自己同舟共济的结局,抉择时她毅然选择了小叔子。
“嫁给富老头,你以后衣食无忧。据我所知他的财产够你享受后半辈子了。”丛天舒不否认二妹的说法,论经济实力,景云比不了。反感有时很奇怪,某个细小的东西足以使你反感,甚至是深恶痛绝。她接受不了富老头的手,触碰到它干树杈子一样扎人。
“到底差什么呀,姐?”
“手。”
“手?什么手?”
“见到他的手,”丛天舒说出她奇怪恐惧,“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赵兰田的手究竟怎么回事丛天霞无法想象,也许它对她伤害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是一个人的手怎么是蛇呢“我这就去辞掉保姆工作。”
丛天舒去赵家,二妹没能拦住她。
“大姐做得对。”弟弟丛天飞说。
“你认为大姐没错,那么是我错啦。”丛天霞气话气说道,“硬往火坑里跳,看烧谁。”
“太夸张了二姐,嫁给景云怎么就是跳火坑。”他反驳道。
丛天霞一团疑云始终没飘走,大姐叫张景云去寻找姐夫,几个月才回来,说姐夫景山外出打工,后来又说姐夫落海失踪,为什么一开始不说落海失踪,追问才说。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她的逻辑是,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电视上报道的真人真事,小叔子看上嫂子而杀死大哥,她深刻记忆。张景云是不是这样啊“摘下你的墨镜吧,别把世界看得黢黑的。”弟弟认为二姐偏激,社会有阴暗面,但光明是大面积。
“景山姐夫死得蹊晓,应该不是渔船遇风暴沉没那样简单。”丛天霞始终往复杂里想。
所谓左耳朵发烧有人想,右耳朵发热有人讲。丛天舒那个下午两只耳朵没反应,她打电话约到赵兰田的女儿,同她一起去跟赵兰田道别。
“你不能再……”赵兰田的女儿挽留,她明白保姆一走,父亲将受到一次打击,他喜欢这个保姆。
丛天舒摇摇头。
“我知道你坚决要走的原因。”赵兰田的女儿断定原因在父亲,他对保姆直率表白,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得了,她问,“我爸对你讲过小雪?”
“他说我长得像小雪。”
“所以他对你……哦,不说这些啦。小丛,原谅一个望见自己生命尽头的人,没有太多的时间回味美好事物。”赵兰田的女儿诚意道,“我爸对你有什么不当的言行,我向你表示歉意。”
“没什么,老人嘛!”丛天舒大度道。
“谢谢你小丛,至此我明白我爸为什么对你那么有好感。”赵兰田的女儿说。
向赵兰田告别,场面总让人心酸,赵兰田像孩子一样哭起来。
丛天舒几乎是逃出来的,她看不得别人哭泣,尤其因自己而悲伤,站在楼外擦下眼角,有几片秋天的枯叶在眼前飞舞。
赵兰田的女儿走出楼,她说:“抛却我爸的想法不说,本来以为你能做一段时间,又走啦,我又得跑家政公司,如今合适的保姆不好找啊!”
“真是对不起赵大姐,我……”丛天舒说。
“我的爸我知道,你说做儿女的怎么办。”临别前赵兰田女儿掏心肺腑地说,“小丛,实在说的,我爸打心眼儿很喜欢你……咦,他没这个福气啊!”
“赵大姐,我怕待下去更伤老人的心,所以才辞职的。”
赵兰田女儿说如今像你这样纯真的人不多了,以前的几个保姆是我轰走的,她们要死要活嫁给我爸,明摆着是嫁房子嫁家产。当然我爸没一个像对你这样动心……唔,不说这些啦。
“留步,大姐。”
“再见!”赵兰田女儿说。
秋天在三江市区可以见到蝴蝶和蜻艇,依傍白狼山,无数昆虫看到城市比日渐萧条的山林温暖,选择的大方向没有错,只是具体落到什么地方,安全和危险决定了今后命运。
丛天舒像一只蝴蝶在秋天的街上行走,冷飕飕的风撕扯她的衣服,蝴蝶愈加显得羸弱。
“嫂子!”
她听到力量的声音,回头等呼唤她的人走近。
“去哪儿嫂子?”张景云问。
“我才去赵家辞掉工作。”丛天舒说。
“辞掉工作好,在家歇歇,这一段你很累。”他关心道。
丛天舒瞥眼茶吧,从来没跟景云在这种情趣的地方坐过,她今天极想去坐坐,她说:
“我们去喝杯茶。”
他们走进西红柿茶吧,选了一个包厢。
“景云,爸说他们同意我们的婚事。”她喝口茶说。
“明年五一结婚的事爸妈还不知道,我想跟他们说。”张景云说。
“我们一起说吧。”丛天舒说,“景云,你非要跟我结婚吗?”
“是。”他回答干脆。
丛天舒沉默,往下没再说此话题,直到晚饭后到公婆的房间里,才捡起来。张母抱着孙子二多,不怎么看他们。
“你们准备明年五一办事?”张建国问。
张景云和丛天舒对望,他让她说。
“初步打算,想听听爸妈的意见。”丛天舒说。
“行,正好景山去世过了一年。”张建国表态,问,“你们商量没,操不操办,家里好有个准备。”
“我还没跟嫂子具体商量。”张景云说。
“既然两人关系变了,就别叫什么嫂子啦,我听来心酸。”张母说。
“叫惯啦,我一时改不了口。”张景云说。
张母怒气道:“改不了口也得改,嫂子、嫂子的多别扭!”
张景云惧怕母亲,低下头。
“有话好好说,吃枪药似的。”张建国说句老伴,解围道,“称呼慢慢改,景云啊,最晚叫到明年五一前,以后可就不能叫了,尤其是当着外人的面。”
丛天舒的目光落在窗台的月季花上,有些意味深长。
张家的月季花几开几落,丛天舒和张景云的婚期逼近。
铁艺分社近日接了几大单活儿,张景云亲自上阵,他戴上电焊帽,烧电焊。
“主任,你又要亲自动手。”老贾说。
“一个人待在办公室没意思,干点活儿好啊!”张景云烧起电焊,弧光,焊花,闪烁。
丛天飞气喘吁吁地跑来,手遮眼睛,躲避电焊弧光,走近景云喊:“景云,景云!”
张景云停下手上的活儿,掀起电焊帽,招呼道:“天飞。”
丛天飞神色慌张,说:“你赶快回去,我大姐住院了。家人急毁(坏)了,打你手机无法接通。”
天舒住院?张景云惊骇,早上还好好的,他看一下手机,说:“没电啦,我说怎么没接到电话。”
丛天飞催促道:“快走吧!”
他们来到市医院,急诊室门外走廊,丛天霞焦急地不停走动,见张景云和丛天飞匆匆赶到,迎上来道:“景云你可来啦!”
“怎么样?”张景云急切地问。
“正在抢救。”丛天霞说。
张景云到抢救室门前,拽门不开,透过门玻璃极力朝里看,什么也看不到,转身见母亲赶来,他说:
“妈,你咋来啦?”
“你爸急啦,我不来,他可要亲自来看天舒。”
“爸那老病号经得住这种场面刺激?真的来了,我们是顾他还是顾嫂子?”
张母责备地看儿子一眼,问:“咋不进去,都堆在走廊干啥?”
丛天霞说医生不让进,反锁门。
“天舒怎么样?”张母问。
“抢救快半小时啦,真急人。”丛天霞说。
女护士走出抢救室,宣布好消息道:“患者已经脱离危险,谁是张景云?”
“是我!”张景云往前站了站,“是我!”
女护士说:“患者要见你,跟我来吧!”
张景云进去,大家要随着进去,被女护士拦住道:“抢救还没完,只能进他一个人。”
抢救结束,张景云坐在丛天舒床前,紧紧握着她的手,她侧过脸说:“还能见到你,景云,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啦。”
“怎么会,”张景云忍着泪说,“现代医学这么发达,啥病治不了呢。何况就快到五一啦,妈昨天亲手剪了双喜字,你想象不出有多大。”
“都到了什么节骨眼,你还说这些。景云,我知道自已的病有多重,死神来敲……”丛天舒哀伤道。
“我没批准,它敢来敲你的门?那胆儿也或肥啦。”他幽默道。
丛天舒被逗微笑,说:“景云,你总这么乐观。”
“当然,我盼五一到来。”
“还谁来啦?”她问。
“妈,天飞、天霞。”张景云说众人在门外等候消息。
医生对张景云说:“你跟我到办公室来,谈谈患者的治疗方案。”
一张头部片子前,医生说:“可以断定,患者的头部有占位性病变。”
张景云听不懂医学术语,什么是占位性病变。
“就是脑瘤。”医生不得不通俗地讲是什么病。
脑瘤!犹如晴天霹雳,张景云将肿瘤理解为癌症,得了癌症还了得呀!
“是良性恶性现在不确定,手术后做病理才能确定。”医生说。
“必须手术,大夫?”
“目前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医生说。
接下去几天,张家笼罩着不幸的阴霾。
“动大手术?”张建国一只手拿着药瓶盖,倒药片的另一只手停住,忧心忡忡道,“开颅,可不是小手术。”
“没别的办法,”张景云愁眉不展道,“脑瘤就得采取手术治疗,大夫说必须尽快做。”
“唉!”张母叹息一声,她怀抱二多说,“二多才三岁多呀,太小啊。”
张建国白了老伴一眼,说:“做,砸锅卖铁也做手术。”
昂贵的手术费难住张家人。
“我再出去借借。”张景云说。
“凑了多少啦?”张建国问老伴。
“加上这个月你的退休金,三千六百块钱。”她说。
“不对,是四千。”
“留四百元给你买两个疗程的药。”张母说。
张建国恼火道:“留什么留,全拿去。”
“这不行,爸你服的药不能停,大夫说了,停药有反弹的可能,你必须连续再服两个疗程,视其病情,才决定是否可以停药。”张景云说,“爸,千万不能停药。”
“我死不了,再说毕竟活了六十多岁,即使死了,也没什么遗憾的……天舒的病一天也不能耽误。”
“手术加上后期治疗,总共费用约八万元,有没有你这四百元无关紧要,爸,可你的病”
张建国不耐烦地说:“得得得,凑点是点,停药!”
“死犟死犟的,好,停药,停药!”张母心疼老伴,生气道。
“爸!……”张景云还在劝父亲。
“非惹我生气?”张建国粗声喊道。
谁敢惹老爷子生气,张景云走出父母的房间,他闷在自己的卧室里想钱,垫桌子的旧晚报启发了他,一则报道题目是:三江惊现女子卖血队。
卖血?去卖血!张景云跑向市医院,在走廊里寻找什么科室。向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询问:
“采血室在哪里?”
几个卖血者坐候在発子上,等着采血。张景云挨着一个中年卖血者坐下来。
“大哥头一次来吧?”中年卖血者问。
“我来问问,一次可抽多少,卖多少钱?”张景云问。
中年卖血者向张景云讲,他认真听,不住地点头。越听越兴奋,他见到钱从血管中汩汩流出。
“你想不想多卖?”中年卖血者表情诡秘道。
过去张景云也听说卖血经过血头,可多赚钱。也巧,中年卖血者就是血头。
关于张景云在血头处得到怎样的指点,这涉及卖血行道的秘密,在此不便披露。
张景云进屋,一身疲惫。
“你咋回来了?天舒身边没人照看行吗?”张母问。
“天霞、天飞替换下来我。”张景云气脉有些短,说。
“哥,哥!”张景锁拉住张景云的手,去看他的画。客厅的茶几上铺展着一张纸,歪歪扭扭的女人头部线条,耳环特夸张。傻子语言不连贯地说,“嫂子……”
张景云疼爱地摸摸傻弟弟的头。
“景锁别缠磨,让你哥歇歇,在医院熬了几夜。”张母见儿子脸色发黄,没往别处想,以为护理病人吃不好睡不好造成的。
张景云进父亲的房间。
“天舒今天怎么样?”父亲问。
“不好,比昨天重。”
“钱张罗到手多少,景云?”
“能去的地方都去了,能借的地方也都借了,以前我交给天舒的存款、工资,她没花一分,原打算给我结婚用……还有我哥打工挣的钱,现在全拿出来,还差四万多。”
“我和你妈商量过,不行就卖掉房子。”
“我们一大家子人,没房子住哪儿啊?不行,爸。”
“先租小一点的房子住着,做手术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