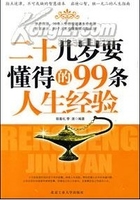花子在柳秘书心里是只苍蝇憎恶又轰赶不走富贵堂的人是亮子里的苍蝇花子房是大概郭县长也这么认为,对付苍蝇,要么彻底消灭,要么当它没存在。与其说消灭不还不如敬而远之招惹它麻烦。
“唱得好,全仗巧。”她说。
“继续唱。”黄杆子说。
唱手到娘娘庙去烧香,给送子娘娘蔬头、上香,娘娘神旁摆放着无数泥孩,亮子里街头有人捏泥人,他们这样唱:俊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一个我;捏得来一似活托,捏得来同上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娘娘庙里的泥人另一种意义,供求子的妇女抱取,谓偷子。
“你看。”唱手抱回来一个泥人。
“哈?”
“儿子。”
噗!黄杆子忍不住笑道:“一个泥人,大街上有人现捏现卖,啥稀奇的物呀?”
“娘娘送的……”唱手十分虔诚地说,“我们有了孩子,得把他披红挂绿,敲锣打鼓送回娘娘庙去。
黄杆子心说:但愿你早点儿“还子”回去。
宪兵队长角山荣从德政堂回来,立刻叫来小日山直登。
“富贵堂的那个瞩托物色好了吗?”角山荣问。
“人员基本确定,正进一步做工作。”小日山直登说,他在宪兵队任特高科课长,负责谋报工作。多年的苦心经营,编织一个庞大的情报网,三江的社会名流,有头有脸的人都被他聘为瞩托,像花子房这种地方发展情报人员较晚,或者说忽略了乞丐群落。
“队长,我们漏掉一个地方。”小日山直登说。
“哪里?”角山荣问,他的印象中,三江地区已经实行全覆盖,谍报人员、瞩托、线人渗透到各行各业之中,“还有哪个死角?”
“富贵堂。”
富贵堂?角山荣听后大笑起来,花子房这种地方发展瞩托有多大价值?这也是当时发展瞩托没把他们考虑进去的原因。
“队长,上次苏联情报员进亮子里可能住在富贵堂。”小日山直登说。
“哦,他扮乞丐?”
“可能。”小日山直登进而分析道,“苏联情报员装扮花子,游击队、胡子就可能扮花子到城里来。因此,我们要扫除这个情报工作死角。”
在富贵堂发展乞丐做瞩托,难度自然很大,这些破衣褴衫的叫花子大都没什么头脑,给吃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让他们做瞩托,弄不好误事帮倒忙。
“据我观察,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小日山直登注意上富贵堂后,暗中细心观察花子,当然是主要人员一大筐头、二筐头、三筐头,座次排下去,帮落子算三筐头,即三把手,“他是帮落子。”
“帮落子?”
“三号人物,相当于胡子的炮头。”小日山直登说。
角山荣熟悉胡子的组织和分工,炮头属于四梁之一,冲锋陷阵,前打后别,是个不怕死的人物。恰恰是这种人让宪兵队长疑虑,鲁莽之人不宜做瞩托。
“他叫刘大愣,是个外陋内险,胆大心细的人。”小日山直登说,他摸清了帮落子的底。
“刘大愣?”角山荣琢磨帮落子的绰号,愣冲、愣瞪、愣头青……他说,“愣,又大,大愣,慎用此人。”
“队长,绰号巧妙地掩盖……”
刘大愣在老膙子做花子王时代就是帮落子,大筐头老膙子没儿子,他窥视王位,万没想到黄杆子到来打破梦想,老膙子临死将鞭子交给了他,黄杆子做了掌柜。刘大愣期待新花子王提拔自己做落子头,结果让扇子龙虱子做了二筐头落子头。
“刘大愣想做掌柜,我想帮助他。”小日山直登钩子下得很深,扶持一个乞丐做花子王,这大大超出了发展瞩托的意义。至于宪兵队特高科课长为什么这样做,目前无法猜测。
“可以!”角山荣同意,看来他清楚部下的目的,说,“此事不宜操之花子在柳秘书心里是只苍蝇,憎恶又轰赶不走,富责堂的人是亮子里的苍蝇花子房是大概郭县长也这么认为对付苍蝇,要么彻底消灭,要么当它没存在。与其说消灭不还不如敬而远之,招惹它麻烦。
过急,有机会再做。当务之急是加强情报工作,秋天这个季节,游击队、胡子都红了眼,要进城搞越冬的衣物……最近有一批军用棉衣、皮靴运抵货场仓库,我们必须保护好这批物资。”
亮子里货场有两个,一个是民用的,一个是军用的,两个货场连体婴儿一样相连。货场修在离城几里远的地方,历史原因造成的,当年俄国人的铁路修到亮子里镇北,而日本人的南满铁路从镇南经过,两条铁路连接上是近些年的事情,始终使用当年满铁修建的货场。十几个日本兵守卫军用货场,由曹长谷川英一指挥。
“我们已经加强了那里的看守,新近配备了一挺机枪。”角山荣说。
小日山直登说富贵堂离货场很近,来侦察的人可能藏身花子房里,角山荣命他尽快掌握刘大愣,我们需要随时掌握富贵堂的情况。
“加快,要加快。”宪兵队说。
“是!”小日山直登成竹在胸道。
帮落子有时单独出去讨要,有时带人出去。春天那个早晨,他带扇子去米店讨粮。
“兄弟,鸿源米店经理连半子嘴,可是只铁公鸡,弄不好空手回来。”帮落子刘大愣说。
连半子嘴是米店经理的绰号,乔经理说话快而不分句儿,所以得此外号。扇子和米店经理打过交道,哪次讨米也不顺溜,也不指望这次顺溜,但是讨到米是肯定的。你看看扇子手里拿的两样东西是什么?一双鞋底,是女人穿的“花盆底”另一样东西是竹筒子,显然是装米用的。
乔经理在店里,见两个花子走来。
“经理,您是不是躲一下。”伙计说。
“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本事,从我这儿弄出一粒米去。”乔经理有了和花子斗一斗的兴趣。
“经理,瘸老病瞎,给点粮吃。”帮落子喊叫。
“我的米面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到别人家去讨吧!”乔经理不肯给。
花盆底:旗鞋一种,即从鞋底上沿向下渐收,成为上大下小的盆形。
“经理老爷,做做好事,保你多福多寿。施我一斗米,功德无量;救苦救难,后福无穷!”刘大愣说唱乞讨无效,随即说道:
你不给,我不走,就在你家死糗!
乔经理叫下人沏了壶铁观音,拉开架势观看花子表演。刘大愣说了一段又一段,米还是没讨到。
扇子上场了,他受伤动物一样哀叫道:“老爷!太太啊。”然后用“花盆底”鞋底打自己的肋骨,乓乓响。
乔经理无动于衷,泰然地品他的茶,一双阴阳眼望着乞丐,心想:打吧,看是你疼还是我疼,死也不给你米。通常,东家赶紧给些东西打发走花子。可是今天遇到了茬口,乔经理和花子叫起劲儿来。
硬壳硬收场出人意料,小日山直登撞见这一幕,他正寻找花子做瞩托,刘大愣已经进人视线多日。他进米店来,乔经理谱摆不下去了,急忙站起身来,道:
“太君,您好!”
“他们的要米的有?”小日山直登问。
“是,死皮赖脸的要。”乔经理说。
“他们的要米的干什么?”不料小日山直登这样问。
“吃……要米……”乔经理的连半子嘴打起奔儿来,摸不准宪兵的脉,不知道他为啥如此问。
“给他们,装满口袋,竹筒子。”小日山直登不可违拗地道。
“这?”
小日山直登不经意的表情,使乔经理内心颤抖,他只大睁一下眼睛,鸿源米店经理听见日本人睁眼睛的声音,如同冻裂的冰面轰然巨响。
“是,太君。”乔经理不怕花子,怕日本人,照宪兵的命令办。
满满一口袋小米和一竹筒子高粱米,装得花子乐得合不拢嘴,乔经理花子在柳秘书心里是只苍蝇,憎恶又轰赶不走,富贵堂的人是亮子里的苍蝇花子房是义、花子在柳秘书心里是只苍蝇,憎恶又轰赶不走,富贵堂的人是亮子里的苍蝇花子房是窝。大概郭县长也这么认为,对付苍蝇要么彻底消灭要么当它没存在。与其说消灭不:还不如敬而远之招惹它麻烦。
却格外心疼,日本宪兵目光下他超常表现,亲手为乞讨者挣口袋嘴灌米,全当是孝敬太君。
以后相似的场合,小日山直登为刘大愣要到钱物。因此,小日山直登敢在角山荣队长面前表示很快说服刘大愣当瞩托。
三江警察局长陶奎元瞧不起章飞腾,才没参加郭县长的告别酒宴。他和前任县长的私交很好。只因为新任县长要在酒席上露脸,他不想见到这张没好感的脸。往前说,章飞腾任北沟镇警察分驻所长,是给他送了一匹好马外加五百块大洋,才当上的。过去三江警察署管着警察分驻所长,如今县长管着警察局长。
“局长,你还是去吧。”冯八娃子劝道。
郭县长的大红请柬放在桌子上,陶奎元说他不去赴宴。
“不去不好吧,郭县长请你,又不是章飞腾。”冯八挫子说。
“前任县长告别,新县长接任,这出戏为章飞腾唱半台,我可不去为他捧臭脚。”陶奎元执意不去,谁也劝不动他。
县长比局长职务大陶奎元清楚,警察局归县府管辖他也认这个头绪,只是他从骨子里瞧不起章飞腾,瞧不起的原因是他太了解他,一个人对一个人了解透彻了,意味着知道他的所有缺点和毛病,拿本地话说:我知道你屁眼儿上有几块疤,尿尿呲多远。
“章飞腾有多大能耐?顺风放量呲不过半尺!”过去陶奎元对冯八矬子说过这样的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章飞腾摇身一变成了县长,命运开的玩笑有些残酷,根本没顾及陶奎元的感受。他慨然道,“土豹子开花,扬棒起来!”
“怎么说他挠扯(竭力奔波)上去,面子还得给他。”冯八矬子见局长神情阴郁,尽管同他关系密切,也不能呛着他说话,“我是说没得罪他的必要,可以敬而远之嘛。”
冯八逨子是自己的大脑,他想的周全,可以不跟县长走近,但是得罪他不成,上边没人当得了县长?说穿了,没日本人的信任更当不上。伪满洲国是谁的天下?他绝不能得罪日本人。
“是啊,打狗也要看主人。”他说。
郭县长的告别酒宴他派冯矬子代表自己去的,编造了不去赴宴的理由,给郭县长捎去个沉甸甸的红包。
柳秘书打电话给冯八矬子,说章县长叫他去一趟。冯八矬子对陶奎元说:“章飞腾找我。”
“哦,没说什么事?”陶奎元问。
“没有,让我到县府去见他。”冯八挫子说。
陶奎元说你去吧,听听他要放什么屁。
冯八挫子去见章飞腾,两人谈了半个上午,县长中午留饭冯八矬子没吃,他知道局长等他带回谈话消息。
“那枚方形古铜钱他随身带着。”
“什么方形古铜钱?”陶奎元没什么印象。
“那年胡子大柜南来好逃走,现场遗留下的……”
冯八挫子的话让陶奎元想起那件气愤的事,如果不是章飞腾失职,将胡子大柜南来好送到省里,督军赏自己的官就不只县长,干警察的话,说不定是警察厅长。唉,好事给这个丧门星葬送了。
“他留古铜钱何意?记仇?”
“不,深深的自责。”冯八挫子说。
这么简单地说陶奎元信吗?不相信。章飞腾当时可是给自己跪下哀求饶命,真的忘记干净?
他说:“我是不是成了东郭先生?”
“章飞腾说得很真挚。”
陶奎元哪里相信章飞腾真挚,狼会真挚吗?留着方形古铜钱是等东山再起,报仇他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局长,我觉得他在找救出胡子大柜南来好的那个人,一直在寻找。”冯八挫子从章飞腾的话中听出来的。
“找谁以后会知道。”陶奎元想换一个话题,他说,“找你没提别的?”
花子在柳秘书心里是只苍蝇,憎恶又轰赶不走,富贵堂的人是亮子里的苍蝇花子房是窝。大概郭县长也这么认为,对付苍蝇,要么彻底消灭,要么当它没存在。与其说消灭不了还不如敬而远之,招惹它麻烦。
新县长和他谈到富贵堂,详细询问了花子的情况。
“唔,他问花子房的情况?”陶奎元觉得奇怪。
“很认真,很详细地问。”冯八矬子也觉得不大正常,县长问花子做什么?不像随便问问。
“干什么呢?”
冯八矬子想了想后说:“郭县长的酒宴上,章飞腾敬酒,黄杆子卷了他的面子没喝。”
“郭县长请了富贵堂掌柜?”
“而且是上上宾,坐在主桌。”冯八矬子身为警局科长都没资格上主桌,他十分不解,郭县长的做法太出人意料。从古到今,三江的县太爷都没如此看重花子,也太过分太夸张啦。他说,“叫花子也是一盘菜?”
“当然。”陶奎元诙谐地说,“一盘秀菜!”
关东人爱吃牲畜的鞭,不仅男人们吃,女人也吃,牛鞭马鞭驴鞭做出的菜,统称秀菜。
秀菜,家常菜,总之警察局长把富贵堂当一盘菜,在三江社会生活中没错。不把丐帮当盘菜不行,你想日子过得消停,就和花子们和睦相处,别惹火他们。
“瞅黄杆子的态度,像似跟章飞腾有底火。”冯八矬子敏感到,警察善于捕捉,“不然,他怎么不肯喝县长敬的酒。”
“也许哪句话冲了大筐头的肺管子。”陶奎元没想得太多,章飞腾做过北沟镇的镇长,富贵堂的人每年都到各处讨要,说不准就磕磕碰碰,他倒担心县长叫自己手下的人做什么,敲打说,“咱别受架弄(窜弄),去撩骚招惹人“没人架弄。”
“相信你也受不了谁架弄。”陶奎元说。
“局长,宪兵队对富贵堂……”
“哦?你看出什么棱缝?”
冯八挫子奇怪的是角山荣怎么会与花子王一个桌子吃饭,宪兵队长竟然同黄杆子撞了杯。
“是给郭县长面子,如果不是,就不好解释了。”陶奎元说。
“肯定不是。”冯八矬子肯定地说,“有戏,富贵堂有戏。”
角山荣是什么人物,在三江地面上,他敢横着走,县长都听他的,怎会把富贵堂放在眼里?还同花子王碰了杯。
“你留心点儿富贵堂的动静,看是一出什么戏。”陶奎元说。
“是,局长。”
花子在柳秘书心里是只苍蝇,憎恶又轰赶不走,富贵堂的人是亮子里的苍蝇,花子房是蛆窝。大概郭县长也这么认为,对付苍蝇要么彻底消灭要么当它没存在。与其说消灭不还不如敬而远之,招惹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