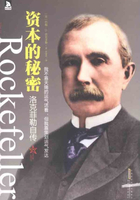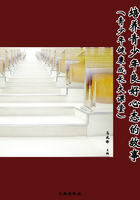当然,董其昌醉心于参禅悟道,在当时,也是受明末特殊的哲学背景和文化风尚影响所致。从宋元到明初及中叶,程朱理学作为一种皇家钦定的正统思想及哲学观念,统治着整个中国的思想界。不变的“天理”,森严的“等级”,严格的“君臣关系”,僵化的“三纲五常”等,窒息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王阳明的与禅学相契合的“心学”开始在知识阶层普遍流行起来。
王阳明认为,“心即性,性即理”,“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这种以关注人的主体、关注人的心灵为主要导向的哲学思想,广泛地蔓延和渗透到各个文艺领域。在戏剧界以汤显祖为代表,在文学界以袁宏道为代表,在绘画界则以董其昌为代表。他们都从各自的领域汇集在明代哲学思想的旗帜下同气相求,遥相呼应,掀起了一股浪漫主义、人文主义的文艺思潮,在作品中把这种“心之本体”中的主体精神充分地显露出来。
董其昌“三纪之中,自为古今”的艺术抱负与这种哲学中的主体精神是息息相通的。他对这种禅宗式的心学,尤有心得,深受影响。
晚明谈禅之风蔚然流行。和西晋时代的清谈一样,当时,大批的文人士子皈依禅宗,如著名文人李贽、袁宏道、陶望龄、陈继儒、汤显祖等。董其昌除了用禅宗来比较理学和心学的异同之外,还用禅理来阐论八股和书法,用禅理来诠释老子,并认为老、庄、列、韩都有与禅相近的地方。因此,他以禅宗的“南北宗”来论画也是很自然的。
出于对禅宗的偏爱,董其昌为自己的斋室取名“画禅室”,而且他的论禅著作也很多。《容台别集》卷一便有“禅悦”五十二则,《画禅室随笔》卷四中有“禅悦”十六则。他的许多论文、论画也喜欢借助禅宗的观点来比喻。董其昌将讲求精工制作的绘画比作北宗,认为这一派绘画颇类“积劫方成菩萨”的渐教;而把逸笔草草的绘画比作南宗,并认为这一派绘画很像“一超直入如来地”的顿教。
可以说,在寻找禅学与书画艺术在精神内涵的联系与融合上,董其昌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文学和绘画本属于同一文化思潮之下的产物。当明初绘画上浙派势焰高涨之日,也正是文学上以李梦阳、何景阳为领袖人物的前七子的诗文复古运动崛起在文坛之时。稍后,吴门派与浙派同时并存,并逐步取代了浙派的优势地位,此时文学上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的唐宋派古文运动风靡文坛;到了松江派,俨然以画坛正宗凌驾于吴门画派之上;在文学上,公安派、竟陵派相继掀起的文学创新运动,席卷着大江南北,文学与绘画领域表现出了在审美取向上的一致性。
董其昌与公安派的袁宗道、宏道、中道三兄弟过往甚密,曾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北京城西崇国寺蒲桃林“结社论学”。作为社友,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少相同的见解。首先是,他们都服膺于禅宗,都在文学和绘画上乞灵于禅宗思想,以求从习惯势力所笼罩的陈陈相因的审美格局中解脱出来。在共同的以主体精神反对古人权威的出发点上,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三袁那里,从禅宗思想所得到的是冲决文学上的复古守旧的时风,力求个性解放,摆脱抄袭。而在董其昌那里,从禅宗思想所得到的,是在传统的文学和书画的基础上,求得有所“悟入”“人须自具法眼,勿随人耳食也”。从“及法”中做到“舍法”,做到“一超直入如来地”。如果说公安派与松江派在接受禅学思想的表现方式上有所区别的话,那么,松江派与竟陵派则表现出趋同性。在竟陵派钟惺、谭元春那里,评介古诗,动辄以“禅机”“禅偈”的方式来暗示、阐释。
晚明兴起的松江画派对于吴门派的变革,是和当时文化艺术思潮的整体氛围紧密相连的。或者可以说,是文化艺术思潮的整体环境促使董其昌提出了“南北宗”论新的审美主张,并以松江画派主导思想的形式呈现出来。
(三)“南北宗”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晚明时代,朝纲不振,危机四伏,虽然政权统治在不断削弱,但中国城市经济却在晚明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小城市发展尤为显著。如董其昌的家乡松江,万历时期人口即达二十万,以出产棉布、纱布驰名全国。“所出布匹,日以万计”。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松江遂有“衣被天下”的美誉。商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刺激绘画的商品化。当商贾们富裕起来之后,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自身的社会形象,书画需求呈现出空前广阔的市场。
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供养着晚明的画家,众多的购买者,不仅能够保障画家的生计,而且促使了文人画家的职业化。险恶政治环境在客观上起到了扩充文人画创作队伍的作用,为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许多士子文人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无意仕途。有的则是在科举落第之后,绝意于功名仕宦之念,如莫是龙、陈继儒等。有的在派系斗争中或被罢黜革职,或致仕求退,如董其昌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晚明时期文人画家和古代的隐士不一样,他们无意仕途,但并非真正遁迹山林,息交绝游,终老田园,而是寄食于城镇,不拒绝与达官显贵的往来。他们的精神生活在表现出一种超然态度的同时,也追求生活上的物质享受。如松江画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陈继儒,既卖诗卖画,也充当买卖字画的中介人。他曾以沈士充的画请董其昌题款,再转手卖给求董画的人。他与当地显贵官僚来往极为密切,所以当时的人讽刺他说:“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巨大的经济收益,使二十多年赋闲在家的董其昌也能姬妾成群,奴仆众多。
政治斗争的酷烈,自然也改变了画家的创作心态和目的。到了晚明,一般的文人画家已不再关心国计民生和社会变化,在他们身上已很难找到任何的社会责任感。董其昌曾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黄子久、沈石田、文征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虽品格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
董其昌把绘画创作的目的,与人的寿命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作画如果刻意求工,而不是从中寄乐,那会有损人的寿命。“寄乐于画”的主张,其实也是发自明末文人画家的普遍心声,寓示了绘画朝着“墨戏”方向发展的道路。在他们看来,绘画的创作目的,纯属于画家个人思想情感的寄兴,成为画家享受天年的手段。这种主张,也反映出明末社会文人画家苟且偷生的享乐风尚。这种绘画主张和享乐风尚,直接对重构文人画创作心态和目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对文人画理想的重构,也已成为晚明画家的自觉。
(四)“南北宗”论与明代画派的发展
在晚明,文人雅集,饮酒、赋诗、作画已成为一种风尚。孙克弘在汉阳太守任上被罢官后,回到故乡华亭。在家中修建亭台楼阁,假山瑞石,种植奇花珍木。又在室中陈列古董与书画。每次雅集,除观赏收藏、创作书画之外,还有童子唱时新曲调,演杂耍戏剧。绘画的商品化,促使了文人画向世俗化的转向,文人画家们以城镇为依托,形成了一定的画家集群体,画派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谋求经济利益的集群组织方式。
这种经常性的集会,加强了画家之间的往来,促进了他们在艺术上的互相影响,由此而逐渐形成以城市为依托、以某几个画家为首的画家集群,并在相互标榜中建立派系。在晚明,除吴门派之外,还有松江派、武林派、嘉兴派、姑熟派、武进派、江宁派等等。这些以地区城镇命名的派别,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画派的形成与城镇经济发展的联系。
绘画的商品化也就必然涉及到画派之间销售市场的竞争,画派之间的相互诋毁时有发生。比如吴门派与松江派就有相互讽刺的现象,在晚明是颇具代表性的。
在整个明代,浙派、吴派、松江派是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山水画流派。这三大流派,以其不同的绘画主张,分别于明代初、中、晚三个时期盛极一时,代表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绘画风格和艺术主张。
从明初宫廷绘画分化出去的浙派起始于戴进。戴进父子本在宫廷作画,后从宫廷回归故里杭州。作为宫廷画师,戴进也接触到了南宋时杭州的院体画传统,遂成为明朝一位成就卓著的画家,影响一时,形成浙派。戴进以后,浙派的光大者吴伟最受皇帝恩宠,被授锦衣镇抚,后又赐画状元印。由戴进开创的浙派,在经过吴伟的光大之后,其影响力达到了顶峰。
浙派绘画主要师法南宋院体,以粗犷豪放见称。
如果说浙派绘画的兴盛是明初对元代审美风尚的一种反叛,那么,随着明朝统治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朝与元朝的敌对状态逐渐消除,这种对元朝审美风尚的反叛心态也不复存在。加之南宋院体画法本不十分符合表现江南自然山水的特征,难以与自然山水完全契合,这样就限制了浙派继续发展的可能性。
另外,出于对“锦衣卫”的憎恶,人们对被授以锦衣卫官衔的浙派画家也不抱有好感。吴伟卒于正德三年(1508年),这是浙派由盛至衰的一个转折点。在正德之前,浙派是画坛趋之若鹜的主派;正德之后,浙派的传人汪肇、蒋离等人画风愈趋草率粗狂,不仅没有充分地发展浙派前期绘画的长处,反倒扩大了浙派粗率的不良习气。浙派末流的作品被作为“画中邪学”的典型,遭到收藏家的排斥。前人将浙派末流的习气总结为四个字:硬、板、秃、拙。
而在明朝中叶兴起的吴门画派,则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审美需求。吴门派绘画的中心在吴门,吴门即苏州。苏州绘画虽在明初受到政治气候的抑制而一蹶不振,但元画传统并非损失殆尽。明代中叶,随着与元朝政治上的敌对情绪的消解和明代政治中心远离江南,苏州画坛渐复元气。
吴门画派初创之时,正是浙派兴盛的时期。戴进死于天顺四年(1462年),沈周此时才36岁,还没有在画坛上崭露头角。吴伟最受皇恩宠遇的时候,沈周才开始驰骋江南画坛。沈周虽在浙派中坚吴伟卒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而新起的一批吴门文人也同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被称为“吴门四家”,又称为“明四家”。
四家之中,沈、文力主继承“元四家”秀逸萧散的画风,仇英以工笔重彩见长;唐寅虽早年师承南宋院体,但和浙派截然不同,他在院体画法的基础上加入了文人的野逸之风与书卷气,化苍劲刚猛为沉静柔和。四家中以文征明享寿最长,他以文秀沉静的画风博得了吴门画派实际领袖地位数十年,可谓领一代风骚。吴门派的迅猛发展和扩大,自然离不开苏州地区的经济繁荣。这种经济繁荣的标志,是绘画市场的求大于供,这也就必然促进画家集团的形成。
文征明之后,师承他的子孙、门生和后学先后有姓名可考者不下六七十人,实际数字远远超过此数。但他们的作品皆在文、沈的流风之内,不仅鲜有新意,而且相形见绌。那些临写沈周的作品,虽然表面图式像沈,但用笔往往刚狠粗霸,色墨浓浊可厌,风采神韵更是不逮;那些摹仿文征明的画,大多平庸板滞,运笔干枯而缺少韵致。他们所继承和发展的,与浙派未能继承戴进、吴伟的优点而是扩大浙派的习气一样,文征明的子侄和弟子辈所继承的是细弱、繁琐、甜腻和纤媚等习气。这和他们缺少诗文修养和文人气质是密切相关的。
在晚明画坛,无论是浙派还是吴门派,其末流都已到了世风日下的困境。这个时期也就必然会兴起一个新的画派,开创画坛新的局面,其重任就是革去浙派末流硬、板、秃、拙的恶俗习气,改造吴门末流细弱、繁琐、甜腻和纤媚的粗滥图式。
这个历史重任落在董其昌等人的身上,他的“南北宗”论,着重于文人画理想的重构,运用对禅理的体悟,重新构建文人山水画美学理论。这种理论,是为了革除画坛弊端而提出的。董其昌面临的问题就是作为一个文人画家,如何重新建立一种正宗的文人画传统。董其昌强调了绘画者的文人身份,推崇“文人画”“士人画”。在董其昌看来,禅宗的思想方式与文人士大夫画家的创作心理结构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他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唐宋以来开始形成的文人画进行了一次理论化的史学梳理与理性升华,总结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山水画创作风格及对流派进行考察与梳理,并把禅宗南宗的“顿悟”与北宗的“渐修”等概念,引入具体的山水画理论分析之中,崇南贬北,极力推崇南宗的文人画。
“南北宗”论对文人画理想的重构,发现并阐述了文人画家的出身地位与其创作态度、审美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对王维、苏轼等人提出的“文人画”概念的深化和对文人画概念外延的拓展。
商业经济发达,政治环境险恶,都促使了职业文人画家群体的形成,扩大了文人画创作的队伍,董其昌“南北宗”理论对“文人画”的推重,自然引起了文人画家们的普遍附和。
董其昌以他山水画的创作实践和“南北宗”论,引领了松江派的画风,奠定并确定了这个画派的基本面貌。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代表了这个画派所达到的最高艺术水准,董其昌的艺术思想及其所倡导的理论,成为松江派在晚明艺术变革中的理论依据。
“南北宗”绘画审美理想的提出,使画坛中心由苏州移至董其昌的故里松江,松江画派遂在晚明浙派与吴门派山水的式微中兴起。董其昌的绘画思想、创作原理、艺术风格以及“南北宗”学说,在16世纪下半叶以后,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