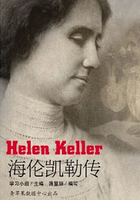蛹的颜色开始变化是在五月末,表示快要变成虻蝇了。这时头和身体的前部,渐渐呈现美丽光亮的黑色,这就是昆虫将来要穿上黑衣服的预兆。我很急迫地要想看穿孔器具的动作,因为在自然情况下根本无法看到这项工作的过程,所以我将虻蝇放在玻璃管里的两个芦粟髓的厚塞子之间。两个塞子间的距离与蜂室大小相近,这种隔壁虽没有蜜蜂巢那样坚固,然而也相当的强韧,可以抵抗相当的力量。旁边的墙是玻璃,那条有齿的带是钉不住的,所以完成这项工作十分困难。
不过,不用担心,只一天工夫那蛹已把前面的隔壁钻通,这壁的厚度有一寸的四分之三。我看到它用犁头将后面的壁抵住,身体弯作弓状,忽然弹起来,用它带钩的颚撞在前面的塞子上。
芦粟髓受钉子的打击,就慢慢地一点点破碎下来。经过一段时间后,它的工作方法又改变了。
它将有锥子的帽钻进髓去,急躁地摇摆一会,然后重新冲击。当中有休息的时间。最后,洞做成功了。蛹溜了进去,但并不完全穿过。在洞口的外面露出头和胸部,身体的其他部分仍然留在里面。
在玻璃制成的小室里,虻蝇有点眩晕感,髓上的洞宽而不整齐,这简直是个破洞,并不是隧道。它在舍腰蜂小室壁上所穿的洞却非常整洁,大小与它身体的直径相同,因为隧道的狭小整洁是必需的。蛹被阻在里面的身子有一半以上,甚至被背上的挫滞住。只有头和胸部露在外面。一种固定的支撑物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它,虻蝇角质的鞘就不能脱下来,也不能将它的翅膀和长足伸展开来。
所以,它用背上的锉将身体固定在狭小隧道的出口中。这时一切都预备好了,变化就从现在开始了。头上露出两个裂口,一直一横,将头壳裂成两半,并且一直裂到胸部。从这种十字形的裂口中,虻蝇突然出现。它的身体由颤动的脚支持着。翅膀干了,开始飞行,飞行前将它脱下的壳抛在隧道的门口。这种颜色幽暗的虻蝇,有五六个星期的寿命,可以让它在百里香花下搜寻,充分地享受快乐的生活。
进入城堡如果你仔细分析这段虻蝇的故事,你一定认为这段故事并未讲完。寓言中的狐狸看到狮子的客人进了它的巢穴,但没有看见它们怎样出来。而此时这件事情正相反,我们只知道它怎样出舍腰蜂的城堡,却不知它进去的路。它把主人吃掉,而要离开那小室时,虻蝇变成了穿孔器具。当隧道开辟的时候,这种工具与在太阳之下裂开的豆荚相似,并且从很坚固的构造中,出来了一个文雅的虻蝇。它看上去就像一丛细毛,这和它所穿通的粗硬的牢墙,真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但是蛴螬进蜂巢的道路,迷惑了我二十五年之久。
母亲不能将它的卵放到蜂巢里去,这一点不容置疑,因为那是关闭的,而且阻碍物是水泥的墙。要钻进去,也就是说它就得再变一回穿孔器,重新穿上它抛在隧道门口的破衣裳,它必须重新变成蛹。因为成长的蝇,没有爪,没有大颚,没有任何工具可以穿过墙壁。
可是,我们前面所见的那个柔弱的蛴螬,能自己跑进储藏室去吸食蜂的蛴螬吗?让我们回想一下吧:它是一段小的油腊肠,只能在卧着的地方伸屈,根本不能够自由移动。它的身体是光滑的长瓶,它的嘴是一个圆孔。它没有方法可以移动,丝毫不能前进。它除消化食物外,不能做任何事情。要想开辟进蜂巢的道路,似乎根本不可能。然而食物在里边,它必须要到达那里,这是一件关乎生死的事。究竟虻蝇如何解决这件事呢?对于这个难题,我决定去做一回差不多不可能的实验,我从虻蝇开始产卵时就看守着它。
在我家的附近,这种蝇很多。所以我到卡本脱拉司去旅行,这是一个可爱的小村镇,我曾经在二十岁时,居住在那里。我第一次做教员的那个老学校,还在那里,它像感化院一样的外观没有丝毫改变。在我幼年时,大家都认为小孩子快乐活泼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的教育制度就采用郁闷和黯淡的方法。我们的学校尤其像感化院,四面墙中有一块空地,简直是一个熊坑,悬木下是孩童们常常争夺游戏的地方。
空地周围是许多像马房的小房间,既没有亮光,又没有流通的空气,我们的教室就在那里。
我站在这所学校的门口,我看到了我常常去买雪茄烟的店铺。我从前的住宅,已成了僧侣的住宅。在窗洞里,外面关闭的百叶窗和里面的绿窗之间就曾放过我们的化学品,放在这儿,是因为以免触动它。这是由家用里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买来的。我的实验,都在火炉上一个汤锅里完成的,不管是安全的或是危险的。我是多么地想重新看到这屋子,在那里我曾研究过算术题目。黑板是我的好朋友,那是我花五法郎一年租来的,当时我缺乏现钱,所以没有买。
现在,让我们还回到昆虫的话题上来。我到卡本脱拉司来,不幸来得太迟,好的季节已经过去。我只看到几只虻蝇在岩壁上面飞。然而我对这些虻蝇并不失望,因为它们并不是在那里做体操,而是在为建立它们的家族而工作。
我顶着烈日在岩石脚下站着,差不多有半天工夫在看着虻蝇的动作。它们在斜坡前面静静地飞转,离开土面只有几寸远。它们从这个蜂巢又到那个蜂巢,但是不想进去。它们的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因为隧道太狭了,它张开的翅膀根本无法进入。所以它们只是视察岩壁,或高或低,有时飞得很快,有时又飞得很慢。有时候我看见它们中的一个,飞近岩壁,瞬间用身体的尾部去碰碰泥土。当这件事过去时,它停下来,稍作休息后便又开始飞舞了。
此刻,我能够肯定地说,当蝇碰一碰泥土的时候,它就已经将卵产在那个地方了。然而,我跑近前用放大镜看时,却并没有看见卵。虽然我深切地加以注意,也不能辨别出我想看到的东西。其实是因为我的疲乏,加上耀眼的日光及焦灼的热度,使我不容易看见任何东西。后来,我和从那卵里出来的小东西熟悉以后,我就不再为我的失败而感到惊奇了,因为就是在我安静而悠闲的研究时,我都很难看出这种无限小的动物。那么,处在太阳烘烤着的岩壁下的我,是那样的疲倦,即使有卵也未必看得见。
可是,我确信,我曾经看见虻蝇一个个地将卵散布在蜂常来的地方。它们将卵暴露在自然状态下,实际上母亲身体的构造上也决定了它们不能将卵掩盖起来。纤细的卵就这样放在炎热的日光之下,土粒之间。至于怎么样处理未来的事,那就要看小蛴螬自己的了。
第二年,我仍然继续我的工作,这次是在我邻近地方卡里科多玛,观察生活在那里的虻蝇。每天早晨九点钟,当太阳正热的时候,我跑到野外去。我预备回家时,头被太阳晒得很痛,只要能够解决我的迷惑,愈是炎热,我成功的机会也愈多。使我吃苦的,能使昆虫快乐;能让我跌倒的,却可使虻蝇更加振作。
焦灼的太阳晒得路面发光,如同一片溶化了的钢。从灰色而阴郁的洋橄榄树上,发出一阵颤动的歌声,那是蝉的音乐会,愈是炎热的天气,它们愈叫得发狂。槐树上的蝉也在尖厉地叫,与普通蝉的单调歌声相应和。
这正是时候了!差不多有五六个星期,我都在早晨或下午,在那些岩石的荒地上搜索。
在那里有许多蜂案,这正是我想要的,但是在它们的面上看不到一个虻蝇,没有一个在我的面前产卵。至多不过有时候看到一个很快的远远的飞过,在与我有一定的距离时就很快消失了。所有的情形,就是如此。想让它们在我面前产卵简直不可能。我招来很多放羊的小牧童,告诉他们注意大的黑蝇和它们常常爬到上面去的蜂巢。但毫无结果。八月末,我的最后幻想破灭了。我们没有看到大的黑蝇在舍腰蜂的房子上停留。
我想,它从不在那里停留。它只在多石的地面上飞来飞去。当它飞翔时,它老练的眼光,能够搜寻到理想的蜂案,当它找到时,立刻飞下去,把卵产在上面,连足都不着地。如果它要休息,那就另寻地方,如土块上、石头上,或百里香和欧薄荷的枝上,所以,我和小牧童们找不到它的卵也不奇怪。
此时,我在舍腰蜂的案里搜寻,寻找正要从卵里出来的蛴螬。我的小牧童们替我拿来几块巢,可以装满好几篮。我将它们带回,放在我的试验台上,仔细的观察。我从小室里拿出茧子,里里外外的看。我用放大镜,观察它们最内层的东西,睡着的幼虫和四周的墙壁,但没有任何结果。我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功夫搜寻那些案,看过的抛在墙角里,积成一大堆,我的研究功夫可以说已经用得很深了。将茧破开来搜寻,还是一无所得,我仍然看不见什么。看来做这件事要有百折不回的恒心才行。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似乎看见有一样东西在蜜蜂幼虫上移动。这是个幻觉吗?是我的呼吸吹起的细毛吗?结果证实这并不是幻觉,也不是细毛,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蛴螬!但是最初我认为这种发现并不重要,因为我已经被这种小动物的出现弄得大惑不解了。
两天以后,我先后找到了十只这样的蠕虫,把它们和蜜蜂蛴螬放在一起,一一分放在玻璃管中,它在蛴螬上扭动。这东西非常之小,只要皮稍稍皱缩,我就看不见了。第一天,在放大镜下,我用一整天的时间观察它,到第二天再来看时,却找不到它了。我以为它已经跑掉了,可是不久后,它又重新蠕动了,能够看见了。
我早就知道,虻蝇幼时有两种形态,我们看见在吃食时的蛴螬是第二种形态。我问我自己:这个新发现是不是第一种形态呢?时间告诉我,它就是第一种形态。因为最后,我看到这小蠕虫变化成我刚才说过的蛴螬,开始用接吻来吸食它的牺牲者了。这一会儿的满足,使我从疲倦里得到了快乐。
虻蝇的“初级幼虫”就是这种小蠕虫,它们非常活泼。它在牺牲者的肥胖的身上爬,在周围行走。它一屈一伸,在地上爬得很快,和尺螃虫的行动方法十分相像。它身体的两端是主要的支撑点,行走的时候,它伸出来,似乎是一根有节的小绳子。连头包括在内,它共有十三节,头的前部,还长有很短很硬的毛。在下方也有四对这样的毛。它在行走时,要靠这些毛的帮助才能完成。
大约有两个星期,这柔弱的蛴螬就保持在这种状态下,既不长大,显然也不曾吃食。
事实上,它能吃什么呢?茧子里除舍腰蜂的幼虫外,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而这种蠕虫本身,在它未达到第二形态,吸盘(即嘴)还没有生出的时候,是不能吃东西的。然而,如我以前说的一样,虽然它不吃,但并不闲着。它观察着未来的食物,在它身上爬上爬下,在它附近跑来跑去。
对于蛴螬的长期断食有一定的原因,在自然环境下也是必须如此。卵是母亲生在蜂巢上面的,要想接近蜂的幼虫,中间还隔着厚的壁垒。寻一条路通到食物那里,是蛴螬自己的事。它不会用激烈的方法,只能很耐心的爬过一条裂缝中的迷路,即便对于这种细长的蠕虫,也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因为蜜蜂的土房非常紧密,既没有因建筑不好而破裂的缺口,也没有因天气不好而裂开的缝。照我看来,只有一个弱点,也只限于少数的案中,就是房屋与石头接连的那一条线。但是,这种弱点也不是常有,因此,我相信虻蝇蛴螬能够在蜂巢墙壁上任何地点找到进入蜂巢的路。
这蛴螬柔弱异常,除掉坚强的忍耐之外,一无所长。它必须经过很长时间的工作才能进入这土房。我不能说完成这项工作非常困难,而工作者又是如此的柔弱。在有些情形下,我相信,这需要好几个月的漫长旅行。所以你看,这种专以穿通墙壁为工作的第一形态的蛴螬,没有食物能够生存,它的生命力很强。
不久,我看到这些小蠕虫皱缩起来,脱去外皮。于是它们就成了我所知道的,也是我在渴望着的,形状似乳色的长瓶子、头上有个小纽扣的虻蝇蛴螬。它们很紧地将圆吸口放在蜜蜂蛴螬的身上,它们开始吃食了。其余的事前面已经讲过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它奇怪的本能,让我们想像它刚刚跑出它的卵,刚刚在酷热的日光下获得生命的时候,它的摇篮就是光石头。当它到世界上来时,没有谁欢迎它,它只是一段线状的半硬物质。忽然,它开始与陵石战斗。它顽强地测探过石头上每个小孔,它溜进去,向前爬,退出来,重新再试。究竟是什么感觉驱使它向有食物的方向去呢?是什么指南针引导它的呢?它晓得那里的深度或有什么东西卧在里面吗?不晓得的。植物的根晓得土地的膏腴吗?也不晓得的。然而,植物的根和这种蠕虫一样,都奔向有营养的地点。为什么呢?我不知道。甚至我不想知道。这是个无法解答的问题。
现在我们继续研究虻蝇传奇的一生。它的生命可分四个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特别的形态和特别的工作。最初的幼虫,跑进贮有食物的蜂案;第二形态的幼虫吃食物;蛹钻通水泥的墙,使成虫能够沐浴阳光;成虫散布它的卵。于是,这故事又周而复始,不断地重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