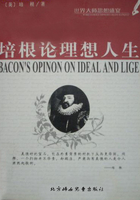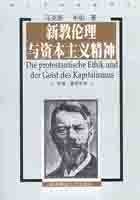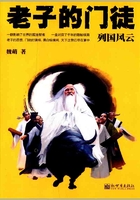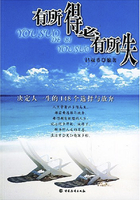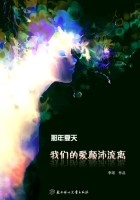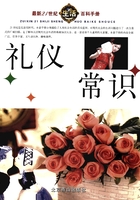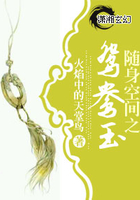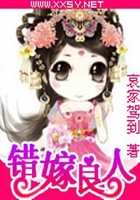孟子把人所独有的、先天的、内在的,并且对人的行为具有本源意义的性质称为人性,这个人性在他看来就是善,就是道德。人之所以高于禽兽,是因为善和道德。这种对人性的看法是片面的、机械的。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性的存在,但它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后天的实践中形成的;它不是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最终本源,相反,它是由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的。人的本性不是善,而是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肯定包含着道德性,即人类需要一定的道德,能够履行道德的准则,这就是所谓的善。但是人类又能恶,能够否定道德,而且恶也并非都是坏事,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善与恶总是如影相随,相辅相成的,不仅如此,善与恶的具体内容也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之间的善恶观也往往是不同的,甚至可能相反。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处于两千多年前的孟子无法了解这些思想。他提倡人性善,强调道德,目的是论证封建道德的权威性,突出它的重要地位,这正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伦理道德领域里的反映。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孟子在道德伦理方面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孟子·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认为,人的善性产生和存在于人的心中。“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过去往往把性和神秘的天命联系在一起,说成是“天命之谓性”。孟子把“心”这个范畴引入伦理学领域,以为它是人性和道德的“发源地”和“储藏所”,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天命”对人性和道德的支配。这是孟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在孟子看来,人性和道德的产生并不神秘。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者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当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就是理义,就是道德,心为什么能够产生理义、产生道德?孟子认为这是“心之官则思”,而理义和道德这些东西是“思则得之,不思不得也”。(《孟子·告子上》)不仅如此,孟子还把“心”里所思的东西(亦即仁义礼智)也称为心,如恻隐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等。孟子以为把心说成是思维器官是不科学的,但是他认识到道德观念和原则与人的心理活动有关,这一点无疑是极有价值的。他举过一个例子:“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纳姑嚎之,其颗有砒,院而不视。夫砒也,非为人砒,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说,孝子仁人合乎道德的活动,与天命无关,都是由“心”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们知道,道德现象与一般的物理现象、生物现象不同,它虽有客观性的一面,但还有主观性的一面,它要通过人来实现,人们的认识、情绪、情感、意志等等都和道德紧密相连。因此,除去研究社会实践对道德的决定作用外,研究心理活动与道德的关系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孟子又给了我们有益的启发。此外,孟子还看到感官与思维器官、感性与理性的不同,而且试图用这种哲学和自然科学上的成就去解释道德观念、道德原则的产生。他认识到耳目感官的局限性,指出道德观念、道德原则不能建立在它们的作用之上,而必须用思维器官、用“心”来认识和把握。他强调养心,主张充分发挥心的能动作用,认为道德的培养只能“困于心,衡于虑,而后得”。如果“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强调主观能动性对道德的作用,这是孟子伦理学说中的又一个合理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把心当成性和道德的本源,这个理论有其致命的缺陷。其一,是把心和耳目感官绝对对立起来,在强调心的作用时,完全否定了感官的作用。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他不知道、感官与思维器官、感性和理性不是绝对对立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互相依存、相互转化。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而作为思维器官的“心”(其实是大脑),不过是个加工厂。孟子轻视感官和感觉,反映了他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和偏见。其二,也是最主要的,孟子把心看成是先天固有的、自满自足的。认为人们的仁义礼智之心,“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完全否定了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对道德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就不会产生一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这种“仁义礼智根于心”的观点完全是违背科学事实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道德观。
依照孟子的伦理观,人性是善的,性善根源于心,心是人先天俱来的,那么这种性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换句话说,孟子以为评价道德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就是他自己提出的主要道德规范,即“仁义礼智”。“仁”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孟子也非常重视它。在孟子的思想中,“仁”已经没有克己复礼的含义,而是肯定了它的“爱人”的一面。他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强调了恻隐之心是仁的道德。他举例说,乍见小孩子的人会“有恻隐之心”,这种思想感情,“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是自足的、绝对的。但是他又很快地泄露了他的世俗目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闻耳。”(《孟子·尽心下》)可见,“仁”和“爱人”不过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更聪明的手段。真正的“仁”、“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义”,孟子认为它是“人之正路也”,也就是道德的具体原则和规范。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尊重私有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所谓“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未有义而遗其君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在批评陈仲子时说过,不贪利只是小义,“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认为最重要的义是维护“亲戚君臣上下”,即遵守封建社会的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礼”,也就是辞让之心,这是孟子提出的评价道德的第三条标准,它是对“仁义”的补充和修饰。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节文斯二者”,目的是给封建道德披上一层温情脉脉、文质彬彬的外衣。“智”,即智慧,这个被古希腊誉为“四德”之首的道德规范,被孟子列为“四德”之末,又称为“是非之心”。在他眼里,智是消极地顺应社会和自然,而不是积极地利用和改造社会和自然。最根本的“智”是能够懂得封建道德,明白仁义。孟子有一段话明确指出他的“四德”的本质:“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这就是说,以“仁”“义”为核心的“四德”,实质上是事亲和从兄,即维护封建主义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巩固封建主义的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与“四德”配合的还有“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孟子以为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关系。认为仁主要是处理父子的原则,义主要是处理君臣的原则,礼是处理夫妇宾客的原则,这样,五伦又使四德得到进一步的具体化和确定。在五伦中,真正平等的关系只有朋友一伦。他主张结交朋友应该“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朋友。友也者,友其德也”。(《孟子·万章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君臣关系这一点上,孟子对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作了最大的修正。孟子认为,君主的世袭制度不是不可改变的,“无与贤,则与贤;无与子,则与子”。(《孟子·万章上》)他主张君臣关系应该是一种相对的、互相尊重的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心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孟子·离娄下》)甚至臣可以杀掉昏君,像武王伐纣,汤伐桀那样,这都符合“义”的原则。这种见解在封建社会里可算是骇世惊俗。难能可贵的是孟子所提的“五伦”,看起来是五种血缘关系为核心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其实,都是社会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早已被打上阶级的烙印。孟子自然认识不到这些,只能从表面上去进行概括。这些道德规范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并为社会所公认的。它们对巩固当时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从性善论出发,孟子建立了自己的义利观。孟子是一位既承认物质利益又重视道义的思想家。他曾朦胧地感觉到社会道德对物质利益的依赖关系,因而赞成发展社会公利,如“制民之产”“勿夺其时”,减轻赋税、发展生产等等。在个人利益上他也采取了相当现实和合乎情理的态度,例如对于“好货”“好色”“好乐”,他认为这都是人之所欲,不能算是什么缺点,只要推己及人,满足了大家的这种愿望的就是明君圣主。但由于他没有掌握物质利益的科学概念,而把“损公利私”之“利”与物质利益混淆了,因此,他经常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强调“义”而又否定了“义”,甚至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这样一来,人的“义”似乎完全是由本性而生,与物质利益丝毫无关了,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但是,孟子强调“义”的重要性,也有着合理的因素:第一,它肯定了人的精神生活和道德情操的重要性。人与动物的一个显著不同就是人有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依赖于人的物质生活,但是它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孟子说:“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秀也。”(《孟子·告子上》)在精神生活中,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操又是其中主要的部分。第二,它重视人格尊严和道德价值。在孟子看来,判断一个人的人格高下和价值高低,不在于财富与地位,而是看其道德状况。他指出:“仁者荣,不仁者辱。”这在把人格商品化了的社会中,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孟子认为,维护人格尊严比生命更重要,“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下》)这正是他藐视权贵,主张人格平等的思想。第三,它鼓励人们坚持道义原则,为道德理想而奋斗。在财富和生死面前,首要的是坚持道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种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视道义传统的最好表现。
孟子的义利观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重“义”方面,对我国人民尊重道义、崇尚气节、克制自我、照顾大局等优秀品质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有益的影响。而其轻“利”方面,经过汉儒宋儒的夸大使之绝对化,把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引入脱离实际、退缨保守、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境地,起了消极作用。这是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和评价的。从孟子的人性论中,引申出一个光辉的命题—“圣人与我同类”。
孟子对“类”的概念的把握,虽没有达到墨家那样高的水平,但他对“人”这个“类”的归纳,的确反映了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封建主义经济关系的要求。同类必相似,这是孟子的类概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凡同类者,举相相似,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孟子·告子上》)圣凡之别在于“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这正如名厨师易牙得味于天下之先,名乐师师旷得音律于天下之先一样,没有什么神秘。人们之间的差异,圣凡之间、善恶之间,不是由于先天的不同,而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差异、个人努力的程度不一所造成。从“圣人与我同类”这一理论出发,孟子蔑视权贵,最重视人的气节,认为知识分子和有道德的人,不能卖身投靠权贵,而应努力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从这里出发,他还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鼓励人们不断地加强道德上的修养,努力达到一个更高的道德境界。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性论时指出:“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孟子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费尔巴哈身上是落后的,在孟子身上却是进步的、值得称赞的。这是因为时代有差别,它们所起的作用不同。费尔巴哈处于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这时,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个“类”,就掩盖了人的阶级性,用虚幻的平等思想欺骗了人民群众,起到了保护反动的剥削制度的作用。而在奴隶制刚刚崩溃,地主阶级正在蓬勃发展的封建社会初期,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个“类”,尽管提供的仍然是抽象的、虚幻的平等,但对新兴地主阶级和广大下层人民却是一个鼓舞,它打击了奴隶主贵族那种“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级观念,否定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陈腐观点,它符合时代要求,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一样:“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
毋庸讳言,性善论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人性论一样,是离开人的实际活动来考察人性,无不具有片面性和绝对化。性善论除了先天的道德观和将封建伦理抽象为永恒人性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谬误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它理性主义的人性论中潜伏着将封建伦理教条夸大、绝对化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倾向,从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的道德规范会演变成为压迫和奴役人的绝对理性和外在权威,形成一种特殊的人的异化,这些都是孟子性善论的不足和消极因素。但是,就孟子性善论所包涵的内容和意义而言,也有强调人的本质和价值,重视理想人性和人的理性等积极因素。既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本质的探索,又是对人性的赞美和对人的热爱,是阶级性和人类性、欺骗性和理想性的矛盾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