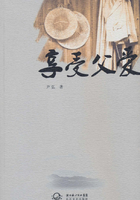一
美得令魂魄都澄澈透明的夜。
虫儿在鸣。邯郸。金钟儿。瘠螽。这些虫儿在草丛中,已经叫了好一阵子。
大大的上弦月悬挂在西边天际。此时,月光正好在岚山顶上吧。
月亮旁边飘着一两朵银色的浮云,云在夜空中向东流动。看着月亮,仿佛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正以同样的速度向西移动。
天空中有无数星星。夜露降临在庭院的草叶上,星星点点地泛着光。天上的星星,又仿佛是凝在叶端的颗颗露珠。
庭院里,夜空明净。
“多好的夜晚呀,晴明……”开口的人是博雅。
朝臣源博雅,是一位武士。
生就一副耿直的模样,神情里却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可爱劲儿。他那种可爱,倒不是女孩子的温柔。在这个年轻人身上,连他的可爱也是粗线条的。那句“多好的夜晚啊”,也是实在又直率。
这并非捧场或附庸风雅的说辞。正因为是有感而言,所以听者心中明白。如果那边有一条狗,就直说“有条狗呀”。便是近乎这般的说法。
晴明只是哦了一声,仰望着月亮。博雅的话,他似听非听。
一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人。他就是安倍晴明,一位阴阳师。
他肤色白净,鼻梁挺直,黑眼睛带着浅褐色。身穿白色狩衣,后背靠在廊柱上。右膝屈起,右肘搁在膝头,手中握着刚才喝光了酒的空杯子。
他的对面,是盘腿而坐的博雅。两人之间放着半瓶酒和碟子,碟中是撒盐的烤香鱼。碟子旁有一盏灯,一朵火焰在摇曳。
博雅造访位于土御门大路的晴明宅邸,是在那天的傍晚时分。
与往常一样,他连随从也不带,在门口说声“在家吗,晴明”,便走进大开的宅门,右手还拎着一个有水的提桶。
这碟子里的鱼,刚才还在桶里游动呢。
博雅特地亲自带香鱼上门。
宫中武士不带随从,手拎装着香鱼的水桶走在路上,是极罕见的。这位博雅看来颇有点不羁的性格。
晴明少有地出迎博雅。
“你是真晴明吗?”博雅对走出来的晴明说。
“如假包换。”
尽管晴明说了,博雅仍然狐疑地打量着他。
因为到晴明家来,往往先出迎的都是诸如精灵、老鼠之类的东西。
“好鱼好鱼。”晴明探看着博雅手中的提桶,连声说道。
桶里的大香鱼游动着,不时露出青灰色的腹部。
一共六尾香鱼,都成了盘中餐。
此刻,碟子里还剩有两尾。晴明和博雅已各吃掉了两条。
说完“多好的夜晚啊”,博雅的目光落在香鱼上面,迟疑起来。
“真奇妙啊,晴明……”博雅把酒杯端到唇边,说道。
“什么事奇妙?”晴明问道。
“哦,是说你的屋子。”
“我的屋子有什么奇妙?”
“看不出有其他活人在的痕迹呀。”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
“没有人在,却把鱼烤好了。”
博雅认为奇妙,自有他的道理。
就在刚才,晴明把他带到外廊,说:“那就把香鱼拿去烹制吧。”
晴明把放香鱼的提桶拿进屋里便消失了。当他返回时,手里没了装鱼的提桶,而是端着放有酒瓶和两只杯子的托盘。
“鱼呢?”
听博雅问,晴明只是不经意地说:“拿去烤啦。”
两人一口一口地喝着酒时,晴明说声“该烤好了吧”,站了起来,又消失在屋子里。等他再出现时,手中的碟子里是烤好的香鱼。
就因为有过这么回事。
当时,晴明隐身于房子何处,博雅并不知道。另外屋里也没有传出烧烤香鱼的动静。烤香鱼也好别的什么也好,总之这个家里除了晴明,完全没有其他活人存在的迹象。
来访时,也曾见过其他人。人数每次不同,有时几个,有时只有一个。别无他人的情况也有过。虽不至于让人联想到这么一所大房子里仅仅住着晴明,但要说究竟有几个人,实在是无从猜测。
可能只是根据需要驱使式神,其实并没有真人;又或者里面确有一两个真人,而博雅无从判断。
即使问晴明,他也总是笑而不答。
于是,博雅便借着香鱼的由头,问起屋子里的事。
“香鱼嘛,并不是人烤的,是火烤的。”晴明说道。
“什么?”
“看火候的,不必是人也行吧?”
“用了式神吗?”
“啊—哈哈。”
“告诉我吧,晴明!”
“刚才说的‘不必是人也行’,当然也有‘是人也行’的意思啊。”
“究竟是不是呢?”
“所以说,是不是都可以呀。”
“不可以。”博雅耿直地说道。
晴明第一次将视线由天空移到博雅的脸上,那仿佛薄施胭红的唇边带着微笑,说:“那就谈一谈咒?”
“又是咒?晴明……”
“对。”
“我的头又开始疼了。”
见博雅这么说,晴明微笑起来。
晴明谈咒的话题,已经有过好几次了,什么世上最短的咒就是“名”,什么路边石头也被施了咒之类。但越听越不明白。
听晴明说的时候,感觉好像明白了,但当他解释完,反问一句“如何”的瞬间,立刻又糊涂了。
“驱使式神当然是通过咒,不过,指使人也得通过咒。”
“……”
“用钱驱使或者用咒驱使,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而且和‘名’一样,咒的本质在于那个人。也就是说,在于被驱使者一方是否愿意接受咒的束缚……”
“哦。”博雅的神情是似懂非懂。他抱起胳膊,身体绷紧。
“哎,晴明,求你了,我们说刚才的话题吧。”
“说刚才的话题?”
“嗯。我刚才提到,没有别人的动静,香鱼却烤好了,实在奇妙。”
“哦。”
“所以我问你:是不是命令式神干的?”
“是不是都可以嘛。”
“不可以。”
“因为不论是人还是式神,都是咒让烤的嘛。”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博雅直率得可爱。
“我说的是,人烤的也好,式神烤的也好,都一样。”
“什么一样?”
“这么说吧,博雅,如果是我让人烤了香鱼,就不难理解吧?”
“当然。”
“那么,我让式神烤了香鱼,也完全不难理解吧?”
“没错……”
“真正费解的不是这里。如果没下命令,也就是说,假如没施咒也没做别的,香鱼却烤好了,那才是真正奇妙的事。”
“哦……”博雅抱着胳膊点头,又说,“不不,我不上当,晴明……”
“我没骗你。”
“不,你想蒙我。”
“真拿你没办法。”
“一点不用为难,晴明。我想知道看火烤鱼的是人还是式神。你说出这个就行。”博雅直截了当地问。
“回答这个就行了?”
“对。”
“式神。”晴明答得很干脆。
“是式神啊……”博雅仿佛如释重负。
“能接受了吗?”
“噢,接受了,不过……”博雅的表情像是挺遗憾的样子。
“怎么啦?”
“很没劲似的。”博雅斟上酒,端起杯子往嘴里灌。
“没劲?不好玩?”
“嗯。”博雅说着,放下了空杯子。
“博雅,你这老实的家伙。”
晴明的目光转向庭院。他右手捏着烤香鱼,雪白的牙齿嚼着烤鱼。
杂草丛生的庭院,几乎从不修整。仿佛只是修了一道山檐式围墙,围起一块荒地而已。
鸭跖草、丝柏、鱼腥草,山野里随处可见的杂草生长得蓬勃茂盛。
高大的山毛榉下面,紫阳花开着暗紫色的花,粗壮的樟树上缠绕着藤萝。
庭院的一角,有一片落了花的银线草。
芒草已长得很高了。野草静默于夜色之中。
对博雅而言,这里只是夜晚时分的庭院,杂草疯长。而对晴明来说,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
但是,博雅对这里如水的月色和草尖露水映现的星光,也并非无动于衷。草木的叶子,和着吹拂庭院的柔风,在昏暗中唰唰作响,让博雅觉得好舒坦。
文月以阴历而言,是七月初三的夜晚。按现在的阳历,是将到八月或刚入八月的时候。
时节正是夏天。白天即便待在树荫里不做事,也会流汗。但在有风的晚上,坐在铺木板的外廊,倒很凉爽。
整个庭院因为树叶和草尖的露水降了温,使空气变凉了。
喝着酒,草尖的露珠似乎变得越发饱满。
澄澈的夜,天上的星星仿佛一颗颗降落在庭院里的草叶上。
晴明把吃剩的鱼头鱼骨抛到草丛中,发出哗啦一声响,杂草晃动的声音逐渐消失在昏暗的远方。
就在声音响起的瞬间,草丛中有一双绿莹莹的光点注视着博雅。
是野兽的眼睛。好像是什么动物衔着晴明扔的鱼骨,跑进了草丛中。
“作为烤鱼的回报吧……”
发觉博雅带着疑惑的目光望着自己,晴明便解释道。
“噢。”博雅坦诚地点着头。
一阵沉默。
微风吹过,杂草晃动,黑暗中有点点星光摇曳。
忽然,地面上的星光之中,有一点泛青的黄光幽幽地画出一道弧线,浮现出来。
这黄光像呼吸着黑暗似的,时强时弱,重复了好几次,忽然消失了。
“是萤火虫吧?”
“应该是萤火虫。”
晴明和博雅不约而同地说道。
又是一阵沉默。萤火虫又飞过两次。
“该是时候了吧,博雅?”晴明忽然小声说道。他依旧望着庭院。
“什么是时候了?”
“你不是来请我办事的吗?”
晴明这么一逼,博雅便挠着头说:“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嗯。”
“因为我这人藏不住事情吧?”
博雅在晴明说出这句话之前,先自说了出来。
“是什么要紧事?”晴明问,他依旧背靠着柱子,望着博雅。
灯盏里的灯火摇晃着小小的光焰,映照在晴明的脸上。
“那件事嘛,晴明……”博雅的脑袋向前探过来。
“怎么回事?”
“刚才那香鱼,味道怎么样?”
“哦,确是好鱼。”
“就是这香鱼。”
“香鱼怎么了?”
“其实这些鱼是别人送的。”
“哦。”
“是饲养鱼鹰的渔夫贺茂忠辅送的……”
“是千手忠辅吗?”
“对,就是那个忠辅。”
“应该是住在法成寺前吧。”
“你很熟嘛。他家在靠近鸭川的地方,他在那里靠养鱼鹰过日子。”
“他碰到了什么问题?”
“出了怪事。”博雅压低声音说。
“怪事?”
“嗯。”博雅探向前方的脑袋又缩了回去,点点头继续说,“忠辅是我母亲那边的远亲……”
“嗬,他身上流着武士的血啊。”
“不,准确说来不是。有武士血脉的是养鱼鹰的忠辅的外孙女……”
“哈哈。”
“也就是说,与我母亲血脉相关的男人生了个女儿,正是那位忠辅的外孙女。”
“噢。”
“那个男人是个好色之徒。有一阵子,他往忠辅女儿处跑得勤,因此生下了忠辅的外孙女,名叫绫子。”
“原来如此。”
“忠辅的女儿也好,那好色男子也好,几年前都因病辞世了。但生下的这个女儿倒还平安无事,今年有十九岁了……”
“哦?”
“出怪事的,就是这个绫子。”
“怎么个怪法?”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我也不大清楚。”
“噢。”晴明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看着博雅。
“昨晚忠辅来央求我。听他说的情况,应该和你有关,就带上香鱼过来了。”
“说说具体情况。”
晴明这么一说,博雅便叙述起来。
二
忠辅一家世代以养鱼鹰为业。忠辅是第四代,论岁数已六十有二。
他在距法成寺不远的鸭川西边修建了一所房子,和外孙女绫子相依为命。他的妻子于八年前过世,只有一个独生女。有男子找上门来,忠辅的女儿为这男子生下一个孩子,就是外孙女绫子。
忠辅的女儿—即绫子的母亲,在五年前绫子十四岁上,患传染病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那相好的男子说要带绫子走,但这事正在商谈中,他也得传染病死了。于是忠辅和绫子一起过日子,已经五年了。
忠辅是养鱼鹰的能手。他能一次指挥二十多只鱼鹰,因其高超的技巧,有人称他为“千手忠辅”。
他获允进出宫中,在公卿们泛舟游湖的时候,经常表演捕鱼。
迄今也有公卿之家提出,想收忠辅为属下的养鱼鹰人,但被他拒绝了,继续独来独往地养他的鱼鹰。
忠辅的外孙女绫子好像有恋人了。约两个月前,忠辅发觉了此事。似乎有男子经常上门。
忠辅和绫子分别睡在不同的房间。
绫子十四岁之前,一直和忠辅同睡在一个房间。但母亲去世后约半年,绫子就单独睡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一个月前的某个晚上,忠辅察觉绫子的房间里没有人。
那天晚上,忠辅忽然半夜醒来。
外面下着雨。柔细的雨丝落在屋顶,给人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入睡前并没有下雨,应该是下半夜才开始的。大约刚过子时吧。
为什么忽然醒过来了呢?
忠辅这么想时,外面传来一阵哗啦哗啦的溅水声。
“就是因为它!”
忠辅想起睡眠中听见过完全一样的声音。这水声打扰了他的睡眠,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庭院的沟渠里跳跃。
忠辅从鸭川引水到庭院里,挖沟蓄水,在里面放养香鱼、鲫鱼和鲤鱼等。所以,他以为是鲤鱼之类的在蹦跳。
想着想着,他又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浅睡,这时又响起了哗啦哗啦的声音。
说不定是水獭之类来打鱼的主意了。如果不是水獭,就是有只鱼鹰逃出来,跳进了沟里。
他打算出去看看,便点起了灯火。
穿上简单的衣服,就要出门而去。忽然,他想起外孙女绫子,因为家里实在太静了。
“绫子……”他呼唤着,拉开门。
屋里却没有本应在那里睡觉的绫子。晦暗狭窄的房间里,只有忠辅手中的灯火在晃动。
心想她也许是去小解了,却莫名地升起不安的感觉。
他打开门走出去,在门外和绫子打了个照面。
绫子用濡湿般的眸子看看忠辅,不作一声,进了家门。
可能是淋雨的原因,她的头发和身上穿的小袖湿漉漉的,仿佛掉进了水里似的。
“绫子……”
忠辅喊她,但她没有回答。
“你上哪儿去了?”
绫子听见忠辅问她,却没有转身,径直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
那天晚上的事仅此而已。
第二天早上,忠辅追问昨晚的事,绫子也只是摇头,似乎全无记忆。绫子的神态一如往常,甚至让忠辅怀疑自己是否睡糊涂了,是在做梦。后来也忘掉了这件事。
忠辅又一次经历类似的事,是十天之后的晚上。
和最初那个晚上一样,夜半忽然醒来,听见水声,仍是来自外面的沟渠。
哗啦哗啦!
声音响起。不是鱼在水中跳跃,是一件不小的东西叩击水面的声音。侧耳细听,又是一声“哗啦”。
忠辅想起了十天前的晚上。
他轻轻起床,没有穿戴整齐,也没有点灯,就悄然来到绫子的房间。
门开着。从窗户照进来幽幽的月光,房间里朦胧可辨,空无一人。
一股异臭扑鼻而来,那是野兽的臭味。
用手摸摸褥子,湿漉漉的。
哗啦!
外面传来响声。
忠辅蹑足悄悄来到门口,手放在拉门上。他想拉开门,但随即又打消了念头。
他担心弄出声音的话,会让在水沟里作响的家伙察觉,于是从屋后悄悄绕出去,猫着腰绕到水沟那边,从房子的阴暗处探头窥视。
明月朗照。月光下,有东西在水沟里游动。
那白色的东西,是一个裸体的女人。
女人把身体沉到齐腰深的水里,神情严肃地俯视水中。
“绫子……”忠辅惊愕地喃喃道。
那女人正是外孙女绫子。
绫子全身赤裸,腰以下浸泡在水里,炯炯有神的双眼注视着水中。
月光满地,清辉洒在绫子濡湿的白净肌肤上,亮晃晃的。
那是美丽却不同寻常的境况。
绫子嘴里竟然衔着一条大香鱼。眼看着她从鱼头开始,活活吞食那条香鱼,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这一幕令人惊骇。
吃毕,绫子用舌头舔去唇边的血迹。那舌头比平时长一倍以上。
哗啦!
水花溅起,绫子的头沉入水中。
当绫子的脸重新露出水面时,嘴里这回叼着一条鲤鱼。
忽然,从另一个方向响起了“啪啪”的声音,是拍手声。
忠辅转眼望着那边的人影。
水沟边上站着一名男子。他中等个头,脸庞清秀,身穿黑色狩衣,配黑色的裙裤。
因为他的这身打扮,忠辅刚才没有发觉那里还有一个人。
“精彩,精彩……”
男子微笑着,看着水中的绫子。
他除了鼻子大而尖,外貌上并无特别之处。脸给人扁平的感觉,眼睛特别大。
男子嘴巴一咧,不出声地微笑着,低声说道:“吃吧。”
绫子便连鱼鳞也不去,就从鱼脑袋啃起,开始大嚼衔在嘴里的大鲤鱼。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绫子就在忠辅的注视下,将整条鲤鱼吞食了,然后又潜入水里。
哗啦一声,她的头又露出水面,口中衔着一条很大的香鱼。
“绫子!”忠辅喊了一声,从房子的暗处走出来。
绫子看见了忠辅。就在那一瞬间,被抓住的香鱼猛地一挣扎,从她嘴里挣脱了。
在水沟的水往外流出的地方,有竹编的板子挡着。这是为了让水流走,而水中的鱼逃脱不了。
挣脱的香鱼越过竹编的挡板,向前面的小水流蹦跳过去。
“真可惜!”绫子龇牙咧嘴地嘟囔着,嘶地呼出一口气,根本不像人的呼吸声。她扬起头,看着忠辅。
“你在干什么?”
忠辅这么一问,绫子嘎吱嘎吱地磨着牙,神情凄楚。
“原来是外祖父大人光临了……”沟边的黑衣男子说话了,“那就下次再来吧!”
他纵身一跃,随即消失在黑暗中。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