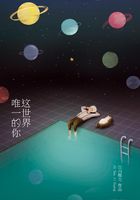她很孤独,但她并不想孤独。眼前的她是一个成功、性感的女子,外表刚强,人们能看到的只有这些。人们看不到那个内在的小女孩,女孩的父亲觉得她不够优秀便拒绝抚养,女孩的母亲对她的态度,不是失望,就是漠不关心。她将那些创伤藏了起来,有些是来去匆匆的坏“叔叔们”造成的,有些是因为别人为她作的坏选择,有些则是她自作自受。人们只看到她的怨恨,却看不到她内心的巨大创伤。人们觉得,她没有心。
别人又怎么会看得见?她自己都看不见,自记事起,她就在为自己建筑一层一层的保护。一次伤害就多一层保护。抵挡嘲讽的保护层,抵挡冷漠的保护层,抵挡残酷的保护层,一层一层堆积起来,终于,她再也无法感受到别人,别人也无法接触到真实的她。
内心的小女孩在哭泣,伤心欲绝,孤单一人。
“我爱你”毫无意义,而天长地久也绝不存在。
他看见吧台对面的她,一手拿着香烟,另一手握着一杯马丁尼。她看上去很诱人;他想碰碰运气,却完全不知,她轻而易举地就能将他看穿。他的搭讪既不新颖,也不好笑。她眯眼打量着他,看着他窘迫的神情。她并不担心他会走开,恰恰相反,她明白自己的举动只会让眼前的男人觉得这更具挑战性,她打了个哈欠。这些套路令她觉得无聊之极。男人全都一样。
他的自尊被那个哈欠挑起来了,不可原谅的话语未加思索便脱口而出。
“究竟发生了什么,能让你如此无情?”
酒吧一下变得很安静,她愣住了,紧盯着他的双眼。自动唱机传出刺耳的音乐,可他们俩都没听到。他深深地看进她的内心,而她退缩了。他看到的太多了;正因为太多,所以不可原谅。她非常恼怒,自己不设防备的样子就被人看到了,已经很久都没发生过这种状况了。她试着让他走开,可令她恐惧的是,话竟然堵在嗓子说不出来。他请她跳舞。
他们走向舞池,宛如在梦境中前行。在静默中她闻到了他的气味,触发了某种陌生却又最熟悉的感受;她拒绝为这种感受分类,预感那会很危险。搂着她的双臂既温暖又舒服。
他小心地避免做出任何有威胁性的举动,就像是在手掌里握着一只娇小的麻雀一样,他可以看到她的心在嗓子眼里跳动。他被迷住了,非常好奇;而她则僵住了,不知所措。
音乐包围了他们,她闭上了双眼。他抱得更紧了一点,而她对此加以默许。摇摆的动作非常抚慰人心,而她决定就这么一次,好好享受当下。她任凭自己的头靠落在他肩上,而由于某种原因,他的心砰砰直跳作为回应。
他被打动了,并不知为何意识到了这对她来说是多么艰难的举动。他好奇生活究竟对她做了些什么,让她如此胆怯,如此冰冷。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要追寻答案。他觉得要是将自己的心交给她,她不加考虑便会本能地将它撕碎,其后甚至可能都不会感到抱歉。
她希望他唯一所追求的,在她的双腿间,而不是她的双耳间。她希望这种对她来说难以定义的渴求,会在一杯,两杯,或者六杯马丁尼后消逝。音乐结束了;他们仍然保持着拥抱的状态多停留了几拍,方才分开。她避开他的凝视,缓慢走回吧台,不知自己接下来要去做什么。她心底清楚自己接下来会怎么做,这与她心底希望自己能做的事,一直抗争着。
他追随着她回到吧台,看着她的臀部随着步伐摇摆,长发在肩头轻抚。他回忆起自己曾认识的一个女孩子,那时她在他身上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最终她在一瓶药和一夸脱伏特加间找到了她要的。昔日的那个年轻男子梦想着被救赎。他在考虑自己该怎么做,而这点和自己能做的事,一直抗争着。
他们在吧台旁坐了下来。他凝望着她的脸,而她则避开他的目光。她望向酒保,轻轻点了点头,酒保开始为她调制又一杯马丁尼。酒保打量着她身边的男人,他也点了点头。于是酒保便回去做自己的工作。他们静静地等待着。两人之间,隔着些什么,孕育着某种承诺。是希望?是拯救?是赎罪?
她面无表情,但他依然可以从中看出痛苦和永恒。酒保递来他们的酒。半杯酒下肚后,她终于回望向身旁的人。这次他看出了反抗,还有正为捍卫领土伺机而动的魔鬼。尽管如此接近她,他也一言不发。
她在他的眼中看到了理解,而这吓坏了她。她不想被人理解,理解意味着距离太近。距离近意味着接触,而接触意味着揭露,也就意味着脆弱。当他望着她的时候,她感觉到他双眼中的温暖,于是凭借着残存的力量,迎了上去。他被打动了。
酒精在她的胃里灼烧,但他眼中燃烧的接纳之情更加炽热。她困惑不解,而他看出了这点,握住了她的手。
他轻柔地言语,但在她心中,这些话响亮并且久久回荡着。
“我想要了解你。”
泪水在她的眼中涌现,种种情绪滑落脸庞。
人们看到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坐在吧台旁,吞云吐雾,周围音乐声强烈。他们穿着考究,让人觉得他们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人们会认为他们只不过是另一对雅皮士,准备脱下衣服随意找个人热舞一番。人们看不见表面下的真实,或者是未知的希望;看不见那渴求肯定的小女孩,也看不见那个需要拯救的年轻男子。
他们很孤独,但他们并不想要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