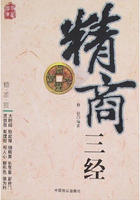在调研那年我对商业有了彻底的认识,它让我真正地步向成功:一,如果视钱财重于工作,则有可能阻碍工作,破坏服务根本。二,如果首先考虑的是赚钱,而不是工作,就会畏首畏尾,阻碍企业发展——它会使人害怕竞争,害怕改进方法,害怕任何可能改变现状的事。三,任何将服务置于首位,尽可能以最好的方法工作的人,其前途是不言而喻的。
在底特律,我的“汽油马车”是第一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唯一一辆汽车。众人视它为讨人嫌的东西,因为它发出的噪音震耳欲聋,吓着马匹。
它还阻碍交通,因为不管我把车停在哪儿,在重新发动之前,总有一堆人围上来看。要是我丢下它,哪怕只是一分钟,也总有好奇心旺盛的人想上来一试身手。最后没办法,我只好带个链条,每当要把它停哪儿时便将它拴在路灯柱上。不仅如此,警察也找我麻烦。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因为印象中那时还没有限速法令。不管怎样,我得从市长那儿得到特许;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倒享有全美唯一一位有驾照司机的殊荣。1895至1896年,我驾驶这辆车行驶了约一千英里,然后以200美元的价格将它卖给了底特律的查尔斯·安斯利(CharlesAinsley)。这是我的第一桶金。我造这辆车只是为了实验,而非为了销售赚钱。不过安斯利想买车;我想试造一辆新车,那200美元正好能派上用场。因此我俩一拍即合,对价格没有任何异议。
像这样的手造零卖并非我初衷,我所期望的是大规模生产。但在那之前,首先得有东西可供生产。凡事欲速则不达。1896年我试造了第二辆车;它与第一辆车相仿,但轻便些。这辆车仍使用传送带装置——到后来我才放弃了这一装置。传动带的确不错,但天气一炎热便不行。这就是为何后来我改用齿轮。通过这辆车,我学到了很多。那时,美国和国外不少人也开始造车。1895年我听说梅西百货(Macys)在展出来自德国的奔驰(Benz),便去观摩。
但那车看上去没什么特征性能值得我借鉴。它用的也是传送带装置,却比我的车重多了。我努力想建造轻便的汽车;而国外生产商似乎从不理解轻便的意义所在。在我自家的工作坊里,我总共造了三辆车,它们都在底特律成功行驶多年。我仍珍藏有第一辆车;当年安斯利将它转卖给另外一个人,几年后我花一百美元从这人手上把它买回。
那段时间,我继续在电力公司工作,并慢慢升到了总工程师的职位,月薪125美元。但是公司总裁对我使用内燃机的实验并不支持,同当年父亲反对我学机械如出一辙。倒不是我的老板反对我实验——他只是反对使用汽油发动机的实验。他所说的仍言犹在耳:“电力,当然行,那是未来主流。可是汽油——那可不行!”
他对内燃机的质疑——这算是最中性的措辞了,自然不无道理。当时电力大发展正刚起步,几乎没人能看见属于内燃机的哪怕一丝的曙光。电力对于未来有许多相对新的理念,人们对它寄予厚望,期望高到时至今日我们仍看不出它有这般功用。我是看不出使用电力对我的实验目标有何帮助。即便架空线是便宜些,道路用车也断不能架在触轮上;且也找不到重量合适的蓄电池。电力车的活动范围必定受限,还得配备大量与其所产动力相应的发动设备。这倒不是说我那时或现在仍看不上电力;我们还未真正好好开发电力,电力自有其用武之地,内燃机也是如此。幸运的是,谁也不可替代谁。
当年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我首次负责主管的那台发电机,至今仍被我保存着。当福特公司建立位于加拿大的发电厂时,我把它从一办公楼购回——它原是被电力公司卖给了办公楼。我将它修补一番,用在加拿大的厂房,运行多年,状况良好。后来由于公司发展,需要建立新的发电厂,我便将这台老发电机带回我的小小博物馆——位于迪尔伯恩市的一间房子,那里藏有多件我视若珍宝的器械。
爱迪生公司提出将我升至公司总管一职,条件是我放弃汽油机的实验,将精力放到一些“真正有用”的事上。也就是说,我得在工作与汽车之间作出选择。我选择了汽车,或者说,我放弃了之前的工作——其实选择结果是明摆着的。我已确信,汽车日后定会成功。1899年8月15日,我辞了工作,投身于汽车制造业。
鉴于我没什么个人储蓄,这或许能看做是我人生迈出的一大步。除去生活费,所有的钱都用来实验了。但我妻子也同意,不能放弃汽车实验——不成功,便成仁。对于汽车,没有“市场需求”——对于新兴事物,本来就没有“需求”一说。汽车被普罗大众接受,同如今飞机逐渐被认可是一样的。一开始,“不用马拉的车”只被当成痴人说梦。对于为什么汽车只能是个玩具,不少聪明人还颇为考究地作了解释。也根本没什么投资者认为它具有商业可行性。我着实不懂,为何每种新交通方式的面世,都伴着如此强烈的反对。甚至时值今日,仍有人摇头晃脑地大谈汽车之奢侈,只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或许运货卡车还是能派点用场。一开始,几乎没人预想到汽车会在工业中发挥如此大的作用。最乐观的也不过是希望它能如自行车那般小有发展改进。当人们发现汽车当真能行驶,且有几家生产商开始生产汽车了,他们第一个疑问也只是,哪辆车跑得最快?赛车的主意实在是古怪,但也再自然不过。我从未考虑过赛车,但大众只将汽车看作跑得快的玩具。所以之后我们不得不制造赛车。
就因为一开始把重心置于赛车上,整个汽车制造业都被拖了后腿。因为制造者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制造速度更快,而非质量更好的车上。这样的汽车行业,只是为投机者服务的行当罢了。
我一离开电力公司,一伙颇具投机头脑的家伙便成立了底特律汽车公司(DetroitAutomobileCompany),来开发我的车。我担任总工程师一职,并持有少量公司股票。连着三年,我们都或多或少以我第一辆车的模型为基础造车,然而它们销售惨淡;我想造更好的车,面向大众,却苦于寻助无门。
公司只想着按订单造,高价销售。公司的宗旨似乎就只是赚钱而已。但除却总工程师一职赋予我的那点权力,我也无能为力。我认识到,新公司并非实现个人理念的理想平台,它不过是赚钱的机器而已——但它也没赚多少钱。于是1902年3月,我辞了职,决心再不听任何人使唤。我走之后,利兰兄弟(theLelands)接手,底特律汽车公司后来也改组成为凯迪拉克汽车公司(CadillacCompany)。
我在公园地81号(81ParkPlace)的一间砖瓦平房租了间店面来继续我的实验,并真正深入了解商业。我揣测,它一定与我刚进入这行当时所感知的有所不同。
从1902年我辞职,到1903年福特汽车公司(FordMotorCompany)成立,这一年其实算是我的调研期。在那单间的小砖瓦铺里,我致力于四缸发动机的研发;而在工作以外,则试图了解商业究竟是怎样的,是否真有必要如此自私自利,如我第一次短暂经历所感受到的那般追金逐利。
从我第一辆车(前文已提到过)的问世,到福特汽车公司的成立,我总共制造了25辆车,其中第19到20辆都是在底特律汽车公司时造的。汽车制造的最开始阶段,只要车子能行驶便足够了;但现在它已进入新阶段,开始追求速度。克利夫兰(Cleveland)的亚历山大·威顿(AlexanderWinton),即威顿车的创始人,是当时全国道路赛车的冠军,他欢迎所有挑战。我设计了一个比我以前所造更为紧凑的双缸密闭式发动机,将它安在底盘架上。我发现这提高了速度,便与威顿安排了一场赛车以一争高下。我们约在底特律的格罗斯角路(GrossePointtrack),结果,我打败了他。这是我第一次赛车。这次赛车结果为我打了广告,广告内容也是唯一能让人们感兴趣的——除非一辆车跑得快,除非它跑赢另一辆赛车,否则人们对这辆车不屑一顾。我立志造世界上最快的车,这让我计划研发四缸发动机。但这是后话了。
商业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就是,众商家将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到钱财上,对自己提供的服务却鲜有关心。在我看来,这真是本末倒置。自然过程本该是,工作的结果是获得金钱,而非金钱先于工作。商业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只要所做工作还混得过去,也有钱可赚,大多数人对改善制造方法漠不关心。也就是说,商品的制造显然不是以如何更好服务大众为指向,它的价值仅在于赚了多少钱——顾客满意与否则无足轻重。东西卖掉就行了。一位不满的客人并不被看作是信任度降低的顾客,而只被当作是讨厌鬼,或是棵摇钱树——替他检修产生的问题,就可以收取更多费用。而本来在开头就该避免这些问题的产生。
举个例子,在汽车业,一旦车子卖了出去,就再没人关心售后。它每英里耗多少油无关紧要;它可提供多少服务无关大局;如果它坏了得更换零件,那只能说车主运气背。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零部件被看作一桩不错的买卖,因为商家持有这样一个观念:既然车主已经买了车,他铁定需要零部件,那他也只有掏钱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