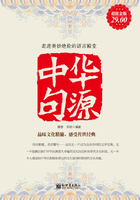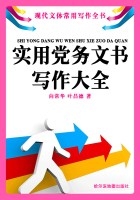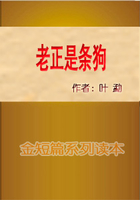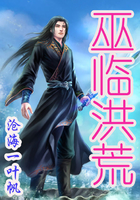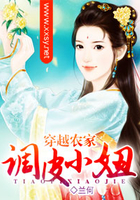从上述统计可见,在历史上,自然灾害以水灾为多。其他灾害如:明成化八年(1472),大旱,运河水干涸;正德九年(1514),蝗灾,庄稼被吃光;嘉靖二年(1523),大旱,“饿殍遍野”;崇祯十四年(1641),大旱,斗米银二两,人相食;清顺治十一年(1654),冬,大雪封门,人畜不能出门;道光八年(1828),地震;光绪二年(1876),秋,大旱,颗粒无收,树皮草根都被百姓吃光;光绪十七年(1891),地震;光绪二十八年(1902),霍乱病流行等。各种灾害交替,严重威胁着农民的生计。
在历史上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之下,单靠农民的一家一户的力量,难以对抗自然灾害,然而国力的薄弱,可用来协助减弱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的作用有限,导致自然力量发挥着对社会秩序的巨大影响。这样,一方面,自然灾害破坏了农民通常的生存方式,使其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国家力量的薄弱,又无法为其创造条件,民众不得不自我寻求谋生方式。
人多地少,耕地条件又差,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性减弱,转而谋求其他生存方式。这点可从历史上杂技艺人的“卖口儿”中得到佐证。
天苍苍,地茫茫,蝗遮日,碱荒荒,蛇蝎豺狼齐当道,财主狗官连裤裆,天地之间无所求,无所求,拜吕祖,学套把戏走江湖。
这段“卖口儿”中,除了讲述人文因素外,所述的“蝗遮日,碱荒荒”即为强调吴桥地理条件差,因而民众不得不采取民间的自救方式——“学套把戏走江湖”,被迫学艺。
2.吴桥尚武之风与杂技兴起
沧州是武术之乡,作为沧州辖属地的吴桥,无疑受到习武风气的影响,自古至今在杂技艺人中不乏武术高手,可以说,武术和杂技是在相互影响中前进的。
作为吴桥受习武之风影响的一个有力证据是在当地广为流传、几乎家喻户晓的传说。传说吴桥是孙武后代的封地,吴桥人武润玺以吴桥姓孙的人数多、以孙姓命名的村子有十几个为证据,证明这一传说。他还认为,吴桥古城东南面有一道由西至东长达十多里的大土丘,传说是孙膑和庞涓打仗时所摆“迷魂阵”遗址,土丘南面十里处有个孙公庙村,该村有座孙公庙,庙里供奉的是孙膑。他以此推测,“吴桥人习武练杂技之所以早大概与此有关。”
首先,笔者不同意武润玺的推测。这里涉及的是如何看待传说的作用、如何使用传说的问题。
传说的存在是民众记忆历史的方式。因为,正史文献受到作者本人身份和时代的限制,能著书立说的往往为有权势、地位和金钱的人,以统治阶级为主,所以他们及其御用文人代表的是“精英阶级”、“特权阶级”,反映的是他们的思想主张和利益,大多数平民百姓的生活状态极少得到记载。于是,广大民众发明了民间自发的一种流传方式,这就是传说,成为另类的“记忆”。
许多学者肯定了传说的价值。黄淑娉曾指出,“无文字的民族既然没有留下记载具体历史事件的文献资料,那么根据传说、系谱、语言及文化的各方面资料,……不失为研究该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可行办法。”赵世瑜甚至认为,传说和正史文献一样重要,他认为口头传说和历史文献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达方式,“在历史记忆的意义上,传说和正史文献传达的历史在价值上是平等的”的观点。在如何看待传说、剖析传说的价值方面,老前辈顾颉刚对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去伪存真的研究堪称典范。这个传说经历了几个时期的发展演变。春秋时期,杞良妻在丈夫战死后,因杞国国君没有按照礼仪到她家里悼念而只在野外遥祭因而拒见国君。战国时期,由于齐国发达,休闲文化的发展,杞良妻被传成会唱歌。汉代,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行,杞良妻就变成能哭来感动天地,城垣也因之崩塌。南北朝时,大兴土木修长城,杞良妻哭倒的城垣被传成是长城。唐朝时,被联想成最早修长城的秦始皇。而杞良妻也被更名为春秋时美女的代称“孟姜”女。由此可见,传说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虽然它融合了不同利益、不同群体的需要,但是传说一定包含某种“真实”。
吴桥是不是孙武后代的封地,大土丘是不是“迷魂阵”遗址,笔者并没有找到史料作为佐证,孙公庙村的孙公庙内供奉孙膑也不能作为确凿的证据。吴桥孙姓多、以孙姓命名的村庄存在,笔者认为也不能和吴桥是孙武后代封地划上等号。而这个传说在吴桥千百年来盛行,那么传说背后的“真实”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吴桥民众把吴桥和孙武、孙膑附会,而不是别人,与孙武、孙膑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军事家、精通武术的人物有关,这一附会反映的是民众强调吴桥人和武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是吴桥人对武术和竞技活动杂技的热爱,是吴桥人为杂技很早就产生、在当地存在时间久寻找历史依托。所以,笔者认为不是因为孙武、孙膑的关系吴桥人才“习武练杂技”,而是因为吴桥人“习武练杂技”才制造了和孙武、孙膑相关的传说。
然而,从何时吴桥人开始“习武练杂技”已无从考证。在吴桥盛传杂技起源于炎黄帝与蚩尤大战。据考古发现,1958年,在吴桥小马厂村发掘了一座南北朝时期的古墓,在古墓中发现了绘有杂技表演图案的壁画,说明至少南北朝时期杂技已经盛行。
3.学艺潮的形成与扩大
吴桥自然地理条件的恶劣,迫使人们往外谋生,而由为了多要点饭发展起来的杂技被越来越多的人证明是一条容易谋生而且可能发大财的路子,这个发现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学演杂技的行列。但是,正是由于学艺、从艺都是贫穷的人,他们几乎没有可能接受文化知识,加上杂技艺人历史上低下的社会地位,导致正史文献对该群体的忽视,这为我们今天的研究造成了困难。笔者的研究集中在20世纪上半叶,以期从那一时期和当今的比较中探讨当今杂技学艺的变迁。
历史上,吴桥人学艺、卖艺的根本原因就是贫穷,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岳永逸在解释解放前天桥艺人形成时说,“人穷了当街卖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杂技艺人。
杂技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使其非常适合在生存线挣扎的普通农民。首先,杂技“杂”的特点决定其学艺成功率很高,柔韧度好的学柔术、力气大的学力量型节目、眼疾手快的学“三仙归洞”
等魔术类节目,身体基础差又无特长的可以学扔草帽等捧逗类节目。不论身高、身材、长相等身体条件如何的人,几乎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学习的杂技门类,这一特点使杂技符合了大众需求,为普通人学艺、从艺创造了条件。在访谈中,老艺人说,只要想学杂技,就一定可以干这一行,他还强调学杂技,最主要的就是努力,其他的是次要的。更证明了对学艺者基本条件的要求低。而且,杂技学艺周期短,几个月即可演出。从而使杂技有可能成为大众的谋生手段。其次,从事杂技演出需要的设备简单,杂技界流传“穷杂技、富魔术”的说法,与魔术演出道具至为重要不同,杂技演出主要靠艺人功夫,道具简单易携带,几个碗、一个坛子、一把刀就可以表演。
为生存所迫而学艺王玉林(1893-?)的个案颇具代表性,他凭着“卸锁”的绝活在北京天桥游乐场立足,并成为天桥八大怪之一。他是吴桥杨家寺人,小时候得到邻村表哥指点,自己偷偷练习。1917年,吴桥遭遇连年大旱,庄稼歉收,难以维持生存,王玉林的父母相继离开人世。为了生存,他带着两个外甥闯关东卖艺。王玉林和妻子、两个外甥和几位同乡在日本演出时遭到欺凌生了一场大病,花光了所有积蓄,乞讨着回到家乡,发誓不再干这一行,可1931年,吴桥遭遇洪涝灾害,庄稼再次歉收影响到生计,为了活命,他带着妻子再次外出卖艺乞讨为生。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生存更加艰难,他带着两个妻子、一个儿子举家到处演出为生。
当这些穷得快无法生存的人外出卖艺几年,就“衣锦还乡”的时候,家乡的人被触动了,这成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学艺、从艺的主要推动力。本文开篇提到孙福有的故事即为一例。
孙福有成立“中华国术大马戏团”后的1929年,从香港到越南西贡,演出40天,收入20万大洋。孙福有回到家乡,为交不起租、还不起债、难以过年的穷苦人家散发钱财。他的中华国术大马戏团规模庞大,近百名杂技演员,3辆摩托车开路,孙福有本人则坐着小轿车,另有4辆卡车装老虎、狮子等动物以进行表演,由第二位妻子茄莉组织由一个二十多人组成的西洋乐队为演出伴奏,为家乡人义演了十多天。这样的声势无疑震撼了在生死线挣扎的穷苦农民。于是,希望加入中华国术马戏团的人们蜂拥而至。同时,孙福有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了杂技演出这条路的希望。
在吴桥和孙福有类似的成功者很多。1933年“北京班”回国解散后,32岁的史德俊回到吴桥,用多年的积蓄买房置地,定居乡村。“四大金刚”杂技团,这是由吴桥杂技艺人张献树和他的3个儿子组成的杂技团。起初,只是张献树听说印度卖艺好赚钱,为了凑外出的盘缠,就把家里的地卖了,买了护照和船票,1933年带着3个儿子离开家乡到了印度。他到印度赚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寄钱回家,把卖掉的地买了回来。14年后,他回国时,已经积攒了一笔可观的积蓄,他们认为当时的积蓄足够花一辈子的,计划回乡买地、盖房。孙福有的例子更是典范。当年孙福有在家乡所盖的俄式二层小楼曾轰动乡里,成为“杂技是生财之路”的样板。1933年底,出外多年的孙福有在吴桥老家动工兴建了一座“豪宅”,用款14000块大洋,木料、水泥是从天津购买,用船经运河运回的,石灰是连镇石灰窑的,砖是张圈的窑烧的,共计用砖40万块。至今,这栋房子,依然伫立在孙福有的家乡沟店铺乡的孙龙村,是该村,乃至吴桥的一个招牌,无声地向世人展示这段历史的记忆。
一个村有一个或几个学艺后,在外演出发了财,艺人发财后,出于其农民本质,往往在家乡盖房、买地,而且艺人有一个不同于农民的地方,就是不藏富,花钱大手大脚。成功艺人树立的榜样吸引着村里在温饱之间挣扎的人,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学艺队伍。吴桥位于华北大平原,村庄和村庄之间没有阻隔、交通也方便。吴桥的村庄与村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和姻亲关系。因此,消息传播虽然主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但传播速度很快,很多人得到信息后加入了进来,组织杂技团、杂技班也不是件难事。反而,一旦一个村庄内,由杂技致富的由一个人变为一个甚至多个杂技团、杂技班或者多个人的时候,当地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学艺的氛围,整个村庄、多个村庄,直至整个乡认可学艺、从艺。
4.吴桥杂技文化圈的界定
在界定吴桥杂技文化圈之前,需区分两个概念,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域。
文化区域亦称文化区,是指具有某种共同文化属性的人群所占据的地域空间单位。文化区域滋生和维系着特定的区域文化,而区域文化一经形成,便会对区域内民众的行为具有导引性。文化区域具有一定的边界和外部特征。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由于文化氛围的相对一致性,便会形成一个边界模糊的文化氛围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物,相同的文化传统会使某一地区的人们产生相同的历史感应和心理认同,形成特定的文化氛围。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区不同于行政区。行政区是一个行政管理区域单位,而文化区则是不同文化特质的空间载体。前者是根据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的需要人为划分的,而后者则是在一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自然形成的。
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区域文化框架,在长达两千多年历史中,随着朝代的更迭、战争的频发、人口的迁移、自然条件的演变、经济的开发、疆域的开拓、外敌的侵入等诸多因素的作用而多次变更。区域文化框架的变更使原有文化区域的版图处于一种被行政区划的不断分割调整之中。这种文化区域被行政区划调整、打乱,造成文化区域边界的模糊和混乱,为文化圈的界定带来一些困难。
作为文化特质的区域分类,文化区与行政区不属于同一个概念。因此,既不能无视行政区域对文化区域分割发生的重要影响,也不能简单地运用行政区域的概念来代替文化区域。
在了解了文化区和行政区的区分之后,我们知道今天行政版图下的吴桥,不应等同于吴桥杂技文化圈。历史上,吴桥县行政区划变动频繁,使划定吴桥杂技文化圈具有一定复杂性。在此笔者仅将涉及吴桥和景县、东光、宁津、德州几地的部分进行概述。以期从历史上寻求他们之间的文化共通性、关联性,这对解释当今吴桥杂技学童群体构成中这几个地方占较大比例极具意义(参见)。
吴桥县境,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齐国。西汉时,吴桥境内设置安县、重平县和安陵侯国,均隶属幽州渤海郡。
东汉时,安县、重平县和安陵国都被废除。三国时,吴桥辖地大多并入脩县(脩,同修。今景县),属冀州勃海郡。
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东光县境内重置安陵县。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将安陵县并入东光县。
唐代,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东光县宣府镇(位于今吴桥县北境)再置安陵县,隶属河北道德州;景福元年安陵县曾改隶属河北道景州,但不久进行更改仍属德州。
宋代,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安陵县并入将陵县(今山东陵县)。
金大定二年,陵县之吴桥镇设置吴桥县(吴桥镇,即今吴桥县城关),属河北东路景州。
明代,吴桥县属河间府景州。清代,吴桥县也曾属景州。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吴桥县属直隶省渤海道,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属河北省。1943年,与东光、南皮县共同组成东南吴联合县;1944年初又与东光县组成东吴县,均属山东省渤海区一专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上半年,吴桥县恢复原建制,仍属山东省渤海区一专区。
1949年8月,山东省渤海区一专区改称沧南专区,继辖吴桥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山东省撤销沧南专区,吴桥县改属德州专区。
1952年11月7日,吴桥县划归河北省沧县专区。
1958年4月28日,撤销沧县专区,吴桥县改为天津专区。
1958年12月20日,撤销故城、景县并入吴桥县,县人民政府迁驻桑园,同时改为天津市辖。
1961年5月23日复设沧州专区,吴桥县还属。1970年沧州专区改称沧州地区,继辖吴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