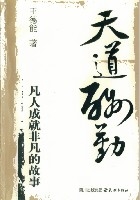他的视线又一次模糊了。他期待着见到她。但是台莱西娜没来,餐厅的谈话声又响起来了。过了几分钟(对他来说好像过了许多年),玛塔姨妈回来了。这次没戴帽子,大衣和手套也没了,也不再那么尴尬了。“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吧?”她对他说。“我陪陪你……他们现在正在用餐。我们在这里一起吃晚饭。我们可以谈谈以往的日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真的在一起、单独在一起。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你能谅解,是吧?亲爱的,她也是没办法。你知道,她必须为她的前途着想。她必须这样。你看过报纸了吧?今天有重要活动,亲爱的,但是我……这使我快受不了了……整个这段时间……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今晚和你在一起是真的。”
老太太絮絮叨叨地谈着,不给米珂西渥考虑的时间。最后,她笑了,一边柔情地看着他一边擦着自己的手。
杜吕娜进来摆桌子。她很匆忙,因为餐厅的晚饭早已开始了。
“她会来吗?”米玛西渥担心地问,声音是沮丧的。“我是说,我最后能见她一面吗?”
“她当然会来的,”老人立即回答,极力掩饰她的窘促,“她一有空就来。她跟我这样说。”
他们对视了一眼,笑了。仿佛直到现在他们才互相认识。他们的感情随着这尴尬而深情的微笑融到了一起。米珂西渥的眼睛似乎在说,“你是玛塔姨妈。”玛塔姨妈的眼睛好像在说,“你是我亲爱的好米珂西渥。你还是老样子,可怜的孩子。”但老太太的眼睛立刻移开了,她怕米珂西渥从中看见别的表示。她又擦了擦双手,说:“现在我们吃饭吧!”
“我确实饿了!”米珂西渥欢叫道,心里踏实了。
“先做祷告。在这里,在你面前,我可以做祷告了。”老太太做了个鬼脸,边画十字边向他眨眼。
管家送来了第一道菜。米珂西渥仔细地看着玛塔姨妈如何搛菜。但是当该他搛菜时,他伸出手想到自己走了这么远路手还是脏的。他脸红了,感到很难堪。他抬起头看着管家,这时管家已十分恭敬。他微笑着哈了哈腰,好像是请他自己动手。幸亏玛塔姨妈出来帮忙。“来,米珂西渥,我给你夹。”
他非常感激,真想吻她一下。
要完菜,管家走出房间后,他也赶紧画了十字。“好孩子。”玛塔姨妈赞赏地说。
他感到很高兴、很痛快。于是立刻开始吃饭,就像他这辈子从没见到过食物一样,不在乎手脏,也不顾虑管家了。但是每次管家进出餐厅,打开玻璃房门,都传来一阵嘈杂的谈话声、欢笑声,这时他都要转过身去。他的忧虑的目光与老人的痛苦、深情的目光相遇,好像要从中找到答案似的。但是他从她目光里得到的却是现在什么也别问、待会儿再说的恳求。然后,他们两人就笑笑又接着吃了。他们谈着远方的家乡,他们的朋友、熟人。玛塔姨妈有问不完的问题。
“你要喝点酒吗?”
米珂西渥伸手去拿酒瓶。就在这当儿,餐厅的门又开了。
随着沙沙的绸衣声和一阵轻快的脚步,进来一道闪光,仿佛把整个房间都照得通明,使他睁不开眼睛。
“台莱西娜……”
他惊呆了,话在嘴边停住了。这是什么?
他脸发烧,眼冒火,张着大嘴,愣愣地盯着她,傻了。这是她吗?怎么这样?她的胸部、肩部、胳膊都露着……身上的绸缎、珠宝闪闪发光。他觉得她已不是真实的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的人……她在说什么?她的声音、目光、笑容,没有一样是他梦想的那样。“你过得怎么样?你现在好了,是不是,米珂西渥?那很好。你曾告诉我,你病了。我一会儿再来看你……现在先由妈妈陪着你,这样行吧?”
台莱西娜急匆匆地回到了餐厅。
“你不再吃点了?”玛塔姨妈问他,试图把他从惊呆中唤醒。他几乎连头都没动一下。
“吃吧。”老太太指指他的盘子,再次说。
米珂西渥伸出两个指头,把又脏又皱的领子拽了拽,想深深地吸一口气……“吃?”
他用指头点点自己的下巴,好像是说:“我吃不下了,我确实吃不下了。”他还是一声不响地坐着,垂头丧气,一心想着几分钟前的情景。过了一会儿,他喃喃地说:“她竟变成这样了!”
他看见玛塔姨玛在痛苦地摇头。她也不吃了,好像在等他。
“但是现在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他闭上眼睛,自言自语似的加了一句。
在黑暗中,他看到了他们之间的鸿沟。不,那不是他的台莱西娜,不是台莱西娜。一切都已结束了,多年前就结束了。这么多年了。而他,像个傻瓜一样。直到现在才看出来。在家的时候,人们就这么说,但他不相信。现在,他不是在出自己的丑吗?在这所房子里待着。如果这些人,包括那管家,知道他米珂西渥·波拿维诺贴上血本,从那么远的地方,坐三十六小时火车来,满以为自己还是这美人的未婚夫,那么人们一定会哄堂大笑——包括管家、厨师、帮手和杜吕娜。如果台莱西娜把他拽到他们面前,在餐厅里向他们说:“瞧,这个穷小子,一个吹笛子的,竟说他想成为我的丈夫。”那将会把人们笑成什么样子!她自己作过保证,这是真的。但是他那时怎么能想到有一天她会变成这样?是他使她今天的成功成为可能,是他为她提供了成功的条件,这也是真的。但是她现在已走得那么远,那么远了,而他被远远抛在后头,还跟从前一样,星期天在地方公园吹笛子。他怎么可能配得上她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现在她已成为显赫的贵妇人,他花在她身上的几个钱还算得了什么!他感到惭愧,只怕人们认为他来是想以那几个钱为资本,要求得到点什么。这时,他想起来,他口袋里装着他生病时台莱西娜寄给他的钱。他感到脸红,感到惭愧。他伸手去摸上衣胸兜,他的钱包放在那里。他立刻说:“玛塔姨妈,我这次来也是为了送还你们寄给我的钱。这算什么钱?是工钱?还是债钱?我看到台莱西娜现在已成了……成了一个……明星了。我看到……不,没什么!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了!但这些钱,我没有资格拿她的。一切都已过去了,我们不会再谈到它了,但是我不要钱!不要!抱歉的是,钱已花掉了一部分。”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的孩子。”玛塔姨妈含着泪花,想打断他。米珂西渥向她示意不要说话。
“不是我花的。是在我生病时我的亲属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是那些可以抵消我花在她身上的钱。你还记得那些钱吗?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了。这是剩下的钱。我走了。”
“什么?这么快就走!”玛塔姨妈喊道,想把他叫回来。“请你一定等着,跟台莱西娜谈谈。你没听见她说她多么想再看见你吗?我去叫她来。”
“不,那样没好处,”米珂西渥肯定地说。“让她和那些人在一起吧。那是她应该待的地方。我是个穷人……我已见过她了。这对我来说已够了……哦,好吧,你要去就去吧,你到那里去……听他们欢笑……我不想让他们嘲笑我。我走了。”
玛塔姨妈把米珂西渥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作了最坏的理解,把它看做是藐视、忌妒。这使可怜的老人觉得好像每个见到她女儿的人都会立刻把她看得很坏。因此,她痛心地哭了,心里一直想着可恨的奢侈生活所造成的不幸,使她劳累的晚年变得不光彩、不名誉。
“但是我已没有能力保护她了,我的孩子。”她迸出一句。
“为什么?”米珂西渥问道。他突然看到她眼神里有一种他一直没注意到的疑惑。他的脸沉了下来。
可怜的老人沉湎于自己的苦痛。她把脸埋在颤抖的手中,但她制止不住外涌的泪水。
“好的,走吧,我的孩子。你走吧。”她抽噎着说。“你说对了她已不属于你了。你当初不该不听我的。”
“那时候,”米珂西渥俯下身来,使劲把她的手从脸上掰开,接过话茬。她痛苦万分地看着他,把手指头放在嘴边求他宽恕。这使米珂西渥按捺住自己,迫使自己用另一种口气温柔地说,“那时候,您……您跟我现在一样穷。但这已够了。不管怎样,我要走了——可以说,我现在更应该走了……我真傻,玛塔姨妈。我原来不懂。不要哭了。哭又有什么用?钱,人们说,钱……”
他从桌子底下拿出公文包和袋子。正想走,他突然想起袋子里还有一些从乡下给台莱西娜带来的香甜的橘子。
“看,玛塔姨妈,”他说。他打开袋子,把喷香的鲜橘子倒在桌子上。“我要是拿这些橘子朝那里的人扔去,他们会怎么样?”他接着说。
“不!万万使不得!”可怜的老人抽泣着说,再次请他安静些。
“不?好吧,那我不扔了。”米珂西渥把空袋子塞进兜里,苦笑了一声回答说。“我原想给她的,但是现在我把它们全部留给你,玛塔姨妈。”他拿起一个送到她鼻前,“闻闻,玛塔姨妈,这乡下的香味。想得到吗?买这些橘子还要付税呢。好了。记住,这只是给你的。并请代我祝她‘好运气’。”
他拿起公文包走了。但在楼梯上,他闪过一阵压抑不住的心寒。他被孤零零地抛弃在远离家乡的陌生的大城市的黑夜里。他被人冷落、遭人歧视,幻想破灭了。他到了大门口,看到外面下着大雨,他没有勇气在这瓢泼大雨中在陌生的街头奔走。他又悄悄地回来,爬上一段楼梯,在最上层坐下。他把胳膊支在膝上,头埋在手里,无声地哭了。
晚饭吃完后,台莱西娜·玛尔尼斯又来到小房间。她发现她母亲一个人在哭,而那边的人却又说又笑。“他走了?”她惊奇地问。玛塔姨妈看也不看,点了点头。苔莱西娜若有所失地叹了一口长气。“真可怜……”但她很快就只能笑了。
“看,”她母亲对她说,听任眼泪往下流,“他给你带来了这么多橘子。”
“哦,多好看!”西娜高兴得跳了起来。她张大手,抓了满满一把。
“不,不要拿到那里去!”她母亲伤心地制止她。但是台莱西娜耸了耸肩,向餐厅跑去,嘴里喊着:“看,西西里岛的橘子。”
(姜望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