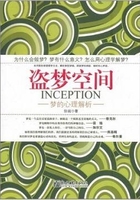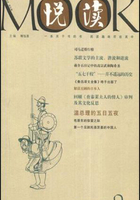有关原罪的教义源自俄狄浦斯的传说。它是这些神秘传说的组成部分,并由此传人古希腊哲学的各个流派之中。(雷诺1905~1912,第2卷,第75页以下)传说人类是提坦神(Titans)的后代,他们曾杀了年轻的狄俄尼索斯-扎格柔斯”(Dionysus-Zagreus)并将他撕碎。这一罪孽因而也成了人类的负担。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一个残篇阐述了宇宙整体是如何遭远古时代的原罪破坏的,并说从原罪中流出的一切必将经受惩罚。提坦巨神们聚众闹事、肆意屠杀并碎尸万段,这一切足以使我们清楚地想起圣尼禄(同上,第2卷,第93页)所描述的图腾献祭。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其他的古代神话也能让我们产生这一回想。例如,俄狄浦斯之死。然而,在这里却有一个令我们不解的差异,即受害者总是一个年轻的神祗。
毫无疑问,在基督教神话中原罪是违抗天父上帝的罪。然而,如果耶稣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原罪的精神负担上拯救了人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原罪就是夺命之罪。在人类感情中根深蒂固的以牙还牙惩罚法有一明确的规定,杀人必偿命。所以,自我牺牲也就暗示了原来的杀人之罪。如果以这种牺牲能偿还天父上帝一命的话,那么所偿还的也只能是弑父之罪了。
因此,在基督教教义中,人们毫不掩饰地承认了早在远古时期的那一罪恶行径,因为他们通过一位儿子的牺牲对这一原罪做出了最彻底的补偿。对父亲的补偿是更加的彻底,因为紧随这一牺牲是儿子们对女人的完全弃绝(须知,她们正是儿子们反抗父亲的原因所在)。然而,就在这一点上,矛盾情感这一心理必然现象找到了表现机会。儿子向父亲做出最大补偿的这一行为使他同时实现了反对父亲的愿望。他自己成了与父亲平起平坐(或更准确地说取代了父亲)的上帝。儿子宗教置换了父亲宗教。作为这一替代的一个标志,古老的图腾餐以圣餐礼(communion)的形式得到了复兴。在圣餐中,弟兄们济济一堂分食这个儿子(已不再是父亲)的血和肉,以此获得圣洁并与他认同。透过这漫漫的岁月,我们可以找到图腾餐与动物献祭、与神人合一的人祭以及与基督教的圣餐之间的同一性。而且,在这种种礼仪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一压得人们无法抬头,却多少又让他们引以为豪的原罪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基督教圣餐从本质上讲是对父亲肉体上的消灭,是那一罪恶行径的重演。“基督教圣餐同化了一个无疑要大大早于基督教的圣餐。”我们可以看到弗雷泽的这一断言是完全正确的。
儿子们合力剪除原父这样的事变必然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件事越少被人们回忆起,由它产生的替代物也就越多。我将竭力不去指出它们留在神话中的俯拾皆是的痕迹,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并采纳雷诺在一篇极富启发意义的讨论俄狄浦斯之死的论文中提出的建议。
在希腊艺术史中,我们见到过这样一个情景,它与史密斯所说的那种图腾餐场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不乏巨大的差异。我脑海中呈现出最最古老的希腊悲剧的情景。一班人有着相同姓名,身着相同服装,围着一名领唱人,全神贯注于他的一言一行。他们是歌队,是英雄的模仿者。原初,英雄是唯一的演员。后来又增加了第二个、第三个演员,作为英雄的对应者,作为从他那儿分化出来的角色;但是,英雄本身这个角色以及他与歌队的关系没有改变。悲剧英雄必须受苦受难;时至今日,这仍是悲剧的本质。他必须承受所谓的悲剧罪过;但是,这一罪过的根本内容是不太容易看出的,因为从我们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这根本算不上是罪过。通常它只与反抗某个神或权威人物有关;歌队满怀同情陪伴着英雄,竭力阻止他,警告他,并竭力使他冷静下来,在他因鲁莽行事而遭罪不容赦的惩罚时,为他感到哀伤。
但是,为什么悲剧的英雄要受苦受难呢?他的“悲剧罪过”又是什么意思呢?让我长话短说,做个爽快的回答。他必须受苦受难,这是因为他是原父,是远古时期那一大悲剧中的英雄(这一悲剧经过有倾向性的歪曲之后正被重新上演);而悲剧性罪过则是为了使歌队摆脱他们的罪过,英雄本人必须承当的罪责。戏台的场景是经过一系列系统歪曲后的历史情景--人们甚至会说,这是最滑头的伪君子的产物。在远离现实的场景中,其实正是歌队的成员们使得英雄遭受苦难;不过,此刻他们已因同情和懊悔而身心交瘁,因而英雄只能独自承受苦难了。面对赫赫权威却恣意妄为、桀骜不驯,这一本该是歌队成员--众弟兄们担当的罪责,都由他来独自承当了。因此,这位悲剧英雄尽管有违自己的意愿,还是成了歌队的救世主。
在希腊悲剧中,表演的特别题材是神羊--狄俄尼索斯的苦难,以及他的追随者(他们都与他认同)的悲叹。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几近湮灭的戏剧是如何在中世纪围绕着耶稣受难而再度获得新生。
因此,在结束这一极其简约的讨论时,我要坚持说,讨论结果表明,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汇集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中。这与俄狄浦斯情结(目前就我们所知)构成了一切神经症的核心这一精神分析研究结论,完全一致。社会心理学的种种问题竟然也能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论点--人与自己父亲的关系--的基础上得到解决,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惊人的发现。甚至还可能,另外一个心理学问题也与此有关。我常常不失时机地指出,本意上的矛盾情感(即同时存在的对同一对象的爱与恨)植根于许多文化制度之中。我们对这一矛盾情感的起源一无所知。一个可能的假设是,它是我们情感生活的一个根本现象。然而,我认为更值得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即矛盾情感本来并不是我们情感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人类通过父亲情结习得的。正是在父亲情结方面,精神分析学对现代人类个体所做的检查发现,矛盾情感仍有极其强烈的表露。
但是,在结束这番议论之前,我必须找个机会指出,尽管我的所有论点使得各论点间本应为一种综合性的联结关系出现了高度的集中,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忽视我的前提的不确定性和结论中的种种困难。我只想提一下后者中的两点,它们也许早已引起许多读者的注意。
大概不会有人注意不到,首先我将集体意识(collective mind)的存在当作我全部立场的基础。(可以说,集体意识的心理过程与个体意识的心理过程是相同的。)尤其是我假定了因那次行动的罪恶感已绵延了数千年,而且在那些对此行动可能一无所知的一代又一代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我假设了诸如遭受那位父亲百般虐待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儿子们所形成的一种情感过程已殃及新的一代又一代的儿子们,而他们却因那位父亲早已被消灭,而免遭了那种虐待。必须承认,这些都是巨大的难题;任何解释若能不要此类假设,将是求之不得的。
然而,进一步的思考将表明,我并非孤掌难鸣,要独自去承担作出这种大胆推论的全部责任。如果不做集体意识的假设,社会心理学大概是无法存在的,因为集体意识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忽略因个体的消亡而出现的心理活动的中断。假如心理过程不能代代相传,假如每一代人都不得不习得自己对新生活的态度,那么,在这一领域中就不会有任何进步,几乎不会有任何发展。这就引起另外两个进一步的问题:代代相继的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心理连续性(psychical continuity)?心理状态(mental states)的代际相传所采用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我并不想装出一副样子,好像这些问题已得到了充分的解释,或者仅凭直接交往和传统(这些都是人们从呱呱坠地时便能接触到的现象)就足以说明这一过程。总的说来,在一代又一代的精神生活中,必要的连续性是以何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心理学并不感兴趣。这一难题也许部分地可用心理气质的遗传来解释,不过,心理气质必须先在个体的生活中获得一定的内在动力后,才能被激活进入实际运作。这也许就是诗人诗句的意义所在:
你从祖先手里继承的遗产,
要努力利用,才能安享。
假如我们承认心理冲动可以完全被压制,以致不露任何痕迹,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更加棘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最严厉的压制也一定会为畸变的替代性冲动和由这些冲动引起的反应留下余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没人能将自己的一些较重要的心理过程瞒过自己的后代。因为精神分析学已经向我们表明,每个人都在潜意识的心理活动中,拥有一套装置。这套装置能够使他诠释他人的反应,就是说,能够使他复原他人加诸在他们自己的感情体现上的种种失真表现。原初与父亲的关系遗留下众多的风俗、仪式和教条。对这一切所做的这种潜意识理解可以使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承接他们的情感遗产。
另一个难题实际上可以从精神分析领域中提出。原始社会中最初的道德戒律和限制已被我们解释成对一种行为做出的反应,而正是这种行为使那些做出这一行为的人获得了“罪”的概念。他们为这一行为而感到悔恨,并决意使这一行为不再重现,使这一行为的执行无利可图。这一富有创造性的罪恶感仍然存在于我们之中。我们发现,在神经症患者之中它以一种非社会的方式在运作,并形成新的道德戒律和恒久的限制以作为对他们所犯罪行的偿还,并作为对重犯这类罪行的防范。然而,如果我们调查这些神经症患者从而去发现到底是什么行为引起了这些反应,我们一定会大失所望。除了那些指向邪恶目的但却无法达到的冲动和情感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行为。掩隐在神经症患者的罪恶感之下的永远是心理的现实,绝不是事实的现实。神经症的特征就是,患者们在这二者之间择取心理的现实,并像正常人对现实做出反应一样,对思想一本正经地做出各种反应。
难道原始人不是这样吗?我们有理由认为,作为他们自恋组织的现象之一,他们将自己的心理动作过高估计到一个离奇的程度。因此,仅仅针对父亲的那种敌视冲动,仅仅是那种杀父吞食的欲望幻想的存在,就足以导致形成了图腾崇拜和塔布的道德反应。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从一个令我们绝无好感的险恶罪行中,去推论出我们是那么引以为豪的文化遗产的源泉。这样也不会破坏横贯古今的因果链,因为心理现实非常牢固,足以承受这一切后果。对此,人们可能会反对说,以社会为形式的从父权部落到兄弟氏族的转变真的发生过。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论点,但并非结论性的。这种转变虽然也许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完成的,但依然能够决定道德反应的出现。只要原父施加的压力仍能感觉得到,对他的敌视感便有理由存在,弟兄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恨,也只能有待日后了。如果就此进一步争论,认为从与父亲的矛盾关系中所派生的一切(塔布和献祭禁忌)具有最深沉的严肃性和最完整的现实性特征,这种进一步的争论便毫无价值可言。因为强迫性神经症患者的仪式和抑制显示了这些相同特征,而且这些仪式和抑制不过是由心理现实(即由意向而非意向的执行)派生而已。我们绝不能从这个一切财富尽显其物质价值的平凡世界中,将一种对仅仅是想象或欲求之物的轻蔑移植到原始人和神经症患者的那个一切财富尽在人们心灵深处的世界中去。
我们现在该拿定主意了,但这确实不太容易。不过,首先我们必须坦白地说,在别人看来似乎是根本性的那种差异在我们看来并不一定影响事物的核心。如果愿望和冲动在原始人看来具有充分的事实价值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多多理解和重视他们的态度,而不是根据我们的标准来矫正他们。因此,让我们对神经症展开更为细致的检查,因为正是与这种病症的比较导致了我们目前的这一疑虑。不太准确地说,强迫性神经症患者在过分的道德包袱的重压下,只是在防御心理的现实,并且因仅仅是感觉到了某些冲动而自我惩罚。历史的现实在此也占有一席之地。早在孩提时代,他们就有了这些邪恶的冲动,纯粹而又简单,并且在童年尚欠阳刚之气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这些冲动转化成动作。这些过分贞洁的人们中的每一个人早在婴儿时代便都经历了一个邪恶时期,即倒错(perversion)阶段。这一阶段成了后来极度道德时期的先驱和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假设在前一种情况下,心理的现实(至于它的结构形式,我们不加怀疑)一开始就与事实的现实相符,原始人也真的是干了他们想干的一切,那么原始人与神经症患者间的相似性将因此得到更彻底的巩固。
不过,我们也不可被这一判断(即原始人与神经症患者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牵得太远。要牢牢记住,这二者间还是有区别的。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我们在思维与行动之间所做的截然区分在他们身上都是不存在的。然而,神经症患者毕竟在其行为方面是受到抑制的,在他们那儿思维完全替代了行动。而另一方面,原始人则是不受抑制的,所以思维直接过渡到行动。在他们那儿,行动却替代了思维。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没下任何定论,我却认为面对此情此景,仍有把握假定“太初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