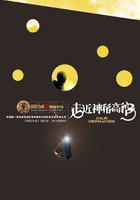第三章 儒学之流贯千年 (1)
董钟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
著名的经济学家赵靖先生曾说:“按由近及远的顺序说,人类历史上我最佩服的三个真有其人的死人是:梁漱溟、董仲舒和释迦牟尼。”还说 “在中国国学的思想天空,站在云端上的是四个人:孔子是儒家创始人,董仲舒是儒学大师,朱熹是理学大师,王阳明是心学大师”。他认为,董仲舒是其中真正承先启后、开天辟地的人。孔子的作品难免粗糙不成体系,最早将儒家思想系统化的正是董仲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使得儒学上升为官学,正式确立了它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赵先生甚至说:如果没有董仲舒,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可能是一被埋没的小人物。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和“大一统”思想成为后世封建王朝统治的理论基础。他在人性的问题上主张德育和教化,与梁漱溟重礼乐、凡刑罚的态度是一致的。梁漱溟看到人性本善,所以主张以礼乐对人进行熏陶;而董仲舒也同样用礼乐来引导善,但同时也指出要用刑罚来对待恶。这一分歧源于对人性的认识不同。
董仲舒在人性的问题上,对先秦儒家的人性论进行了扬弃,既不同于孟子,也有别于荀子,提出了性三品说,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三性之中最上等的是圣人之性,“圣人过善”,其性“不可以名性”,圣人凭借生来而具的过善之性,无需教化,善是一种已经实现了的现实人格。最下等的是“斗筲之性”。董仲舒视之为“又不可以名性”而低于“万民之性”的下品之性,是纯恶之性。““斗筲之民”作为恶的化身,不具有任何成圣的可能。可见在这两类人身上,前者已成善,无需教化,后者教化亦无用,只能用刑罚来待之。所以教化的对象是 “中民之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其实就是说这类人身上有成圣或成恶的可能性。针对这些人,他提出了德育的主张,其德育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五个方面,其核心不离“仁”。
董仲舒提出的仁的法则是在爱人,不在爱我。
西周初年,营荡任齐国司寇。司寇在商代和西周初年是王朝的高官,其职责是驱捕盗贼和据法诛戮大臣等等。那年,姜太公封到齐国,就问营荡治理齐国的主要原则是什么,营荡说是仁义。姜太公又问:如何实行仁义?营荡回答: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姜太公又问:如何爱人尊老?营荡说:爱人就是要爱自己的孩子,不要他出力,让他吃好的;尊老,就是要尊重自己家的老人,妻子岁数大了,丈夫要向他跪拜。姜太公一听气坏了,说:我要用仁义治理国家,你却用仁义来搅乱齐国。结果姜太公把营荡杀了。
董仲舒是赞成姜太公的做法的,因为要推行仁政,实现大一统,必定要把善心施及天下百姓,只爱自己亲人的人怎么可以为政?
他说:“昔者晋灵公杀膳宰以淑饮食,弹大夫以娱其意,非不厚自爱也,然而不得为淑人者,不爱人也。”
《左传》里有一篇文章写“晋灵公不君”:晋灵公不遵守做国君的规则,大量征收赋税来满足奢侈的生活。他从高台上用弹弓射行人,观看他们躲避弹丸的样子。厨师没有把熊掌炖烂,他就把厨师杀了,放在筐里,让官女们用车载经过朝廷。此外还派人刺杀屡次进谏的忠臣赵盾。
董仲舒就直言说他“不爱人也。”这样的人哪有作为君主当有的仁义之心?这样的君主是自取灭亡。
他在《春秋繁露》里写道: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能够做到爱其他的诸侯,就能在诸侯中树立权威,成为霸主;能够把爱推广到四海之外,施及天下,那他就是王者;如果只爱自己封地里的人民,虽可保全,却难有大作为;如果只爱自己,那就是自取灭亡。可见,他的社会理想不独为君,不独为民,而是为天下的,也就是他所崇仰的大一统。
董仲舒这一思想对国家的大一统和社会的安定和谐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推而广之,中国人的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等外交政策也可以从这里找到哲学依据。赵靖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说:“董仲舒的思想标志着儒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儒学作为维护一统封建帝国统治的主要意识形态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
弦外听儒音
《春秋繁露》: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著作,体现了天下一统、宣扬“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为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提供理论依据。
天人三策:又称为《贤良对策》,汉朝经历了“文帝好刑名”,“景帝不任儒”,“窦太后好黄老”之后,终于迎来了有雄心建大汉的汉武帝,他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以此选拔人才,在这种背景下,董仲舒连上三策作答,这就是天人三策,其中心思想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朱熹:天理亦在人欲内
“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出来。随时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朱熹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理学集大成者,他的学说在当时的南宋虽然被认为是“伪学”,并且一再受到打压,但却在元明清三朝被立为正宗儒学。康熙作为杰出的政治家,看了朱熹注释的《性理精义》后,在序中说,他读了这本书,“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而确然,知其不可易。”并且认为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因此说“康乾盛世”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朱熹治国思想的产物,丝毫也不为过。
朱熹的格物致知以“理一分殊”为基础。“总天地万物之理”的“太极”高于万物,分殊就是天地万物各自本于“理”且互不相同的理,也就是说花鸟鱼虫皆有“理”且各不相同。人想要通达最高的理,就应当先从万物身上去“格”,格就是推究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联系起来反复思考,不知不觉就达到了一定境界,在某一天豁然开朗,所以才有后来王守仁“格竹子”的故事。
人作为万物之一,也有自己的理,于是就有了一直为后世所诟病的话:“存天理,去人欲”。从字面上看,仿佛天理和人性是对立的,要求人绝情寡欲,也因此被后世所诟病。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果结合梁漱溟先生的见解,就会发现他们原来不谋而合。
梁漱溟先生说:“合适者,他们的生活法恰合于生命之理之谓也……恰即是恰合生命轨则之谓。轨则是什么,就是调和,就是中。所谓调和与中在何处求,要在恰字上求,增减一点,偏邪一点,皆不对。要在恰好,要在恰中,因此生命才是顺,否则就是逆,就是戕害生命之理。”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过质或质过文,都不是圣人之道。
朱熹所说的“天理”指的正是人正常的要求;而“人欲”则指的是“私欲”,是指那些超出了正当要求以及违反了社会规范的欲望。所以,朱熹说:“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出来。随时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他也并不是一概反对人的欲望:“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圣人与常人皆如此,是同行也。”可见他和孔子一样,是承认“食色,性也”的,他知道人的合理欲求。但圣人之所以圣人在于:“圣人之情不溺于此,所以与常人异耳。”也就是说圣人能够做到文质彬彬,达中庸之道,这就是“天理”,而常人沉溺于“欲”中,就堕入了恶。
为了让人能够不为欲念所吞噬,所以才要“明天理”、“存天理”,“格物致知”正是朱熹提出的方法。康熙皇帝曾如此评论:“朱夫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也。”此后的圣人无出朱熹之右者。康熙皇帝本人爱好数学,格物致知带有科学研究的学术精神,因此他交口称赞本不足为怪,但是推崇如此之高,必然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就是朱熹的学问中藏有助于社会统治和江山社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