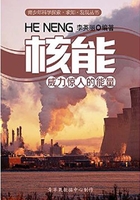第二章 孟子取义,浩然为生 (2)
齐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说:“如果您的司法官不能管理他的下属,那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他的职!”
孟子又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治理得很糟糕,那又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一边去了。
人之向善同水之就下
“性即是指现在人性的倾向。这个倾向即是善。”
人性是善还是恶?孔子并没有为之下定论。但自他之后,儒家的两大家荀子和孟子一水中分,从性的善恶出发延伸出了两派政治主张。荀子尚性恶,故主张用礼乐刑罚来约束,这也就难怪他的弟子韩非子等崇尚霸道,别开法家了。而孟子一直推崇的是性善论,认为礼乐是人性的外化,因此他期待君主能够推行王道,以仁政来获取民心。
但孟子的性善论常常被人误解,以为性善就是好,每个人生来都是好的,不需要教导,实则不然。梁漱溟先生指出,孟子所说的性善被人误解的最大之处就是“把所谓性看成一个已成的呆板东西。”他认为性应当是活动着的:“性即是指现在人性的倾向。这个倾向即是善,不但圣人是性善,即暴虐如桀纣亦是性善,是彻始彻终的没有人不是性善,因人人的倾向是如此。”性是一种倾向,性善就是人愿意向着好的方向去努力,这才是孟子所言的性善论。
《孟子·告子上》里有一段话就很好地阐释了他这一论点。
告子说:“人性好比湍急的水,在东边开个口就往东流,在西边开个口就往西流。人性本来就不分善与不善,就像水流本来不分向东向西一样。”孟子说:“水流确实是本来不分向东向西的,难道也不分向上向下吗?人性的善,就好比水朝下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水,拍打一下叫它飞溅起来,也能使它高过人的额头;阻挡住它叫它倒流,可以使它流到山上。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形势导致这样的。人之所以可以使他变得不善,他本性的改变也正像这样。”
在告子看来,人的本性并无善恶,全然由外界去引导,欲东则东,欲西则西,而且是固定不变的。而孟子不然,他认为人性是活的,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流动着的一个趋势,即人总是向着善靠拢的。但是人性既然是向善的,为何世间依然有作恶多端之人呢?桀纣之徒也能算是善的吗?如果善是本性,那么恶呢?
如上所言,善是一种引导人们向着好的方向努力的倾向,它本身并不是人们言行的全部内容。要把这种倾向落到实处,使自己成为善人,还必须要求人们去不懈地努力,梁先生称这种努力为生命的奋强,是一种蓬勃的茁壮的生命力。他说,生活是以活动为性,不以静为性,因此恶虽然是一种倾向,却不是生活的本性:“正有生命时,没有不努力者。故不努力不能归之于生命,即恶不应归之于本性。”
恶是静止的,当人们不愿顺着善的方向前进时,就会滞留原地,久而久之,画地为牢,堕入了恶的圈子。普通人偶尔会说一些粗鄙的话,这在梁先生看来与桀纣之徒行恶并无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后者堕入了一种惯性之中,心昏沉下去,消极生活,这就是静。因此梁先生说:“世间上实没有人有力气去作恶,只是没有力气去做好事而已。”生命是活动的,因此恶并不与生命本身同轨而行。
孟子曾对梁惠王说: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那些行恶的人并不是没有善的本心,而是如孟子所言,非不能也,不为也。世人往往徘徊于不为与不能之间,因此才需要在引导之下不懈地顺着善的倾向走。
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都能衍生出礼乐文化,前者使之成为可能,因为性善的人本身的行为就与礼乐相契合;后者则使之变成必须,如果没有礼乐,人就容易堕入昏昧之中。但是性善论无疑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那就是不论有些污垢如何令人生厌,底下的种子随时都可能绽放出一朵鲜嫩而美丽的花,这样的世界不是更值得让人期待吗?
弦外听儒音
王道:这是孟子认为的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他说:“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
霸道:与“王道”相对,指以武力、刑法、权势等统治天下的政策。
春秋无义战:孟子认为春秋时代没有符合义的战争。所谓征,是指天子讨伐诸侯,同等的诸侯国是不能相互征讨的。但是当时的诸侯国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打着周天子的名号发动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故有此语。
顺天机而行,一喜一怒一忧惧
“真正的乐天,是一喜一怒一忧一惧,都是乐乎天机而动,顺自己生命,用着精力去走,然并不是格外用什么力,只是从生命里有力的发出而已。”
生命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从哪里来又回归哪里去,中间的那段长长的路回头看也许会缩成一个小点。尽管如此,对命运的探讨自古以来从未有过间断,不同的学派有着不同的见解。儒家所谓的知天命,并非是指能够洞察宇宙的万般变化、对人世百态能够洞若观火,自己超然物外。这种人是庄子笔下的至人、神人、圣人,而非孔孟所谓的知天命之人。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从自己的心出发去看待宇宙万物的变化,因此时常以性命对举,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性即是我,天即是命,知有我然后才去探索我的痕迹,这和孔子所言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孟子》中有一段这么一段话: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一样不是天命决定的。顺从天命,接受的是正常的命运;因此懂天命的人不会站立在危墙下面。尽力行道而死的,是正常的命运;犯罪受刑而死的,不是正常的命运。
梁漱溟先生在谈到孟子这段话时说:知命者是最能尽自己力量的人,即孟子所谓尽其道而死者,是正命也。修身养性,三省吾身,琢磨透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然后再去行动,这样自己的每一份付出都是为了心中所求,这才是“尽心”,这样走过的路成就的命运才是“正命”。孟子所言的“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也是这个道理。
梁惠王曾对孟子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而已。做自己该去做的事,这就够了,而知天命的关键在于是否“知心”并且尽力。
屈原的自沉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人赞其高义,有人认为这是弃君的不忠行为,更有人觉得他应该高引而去或另择明主。但是对于屈原自己来说,这却是他唯一的选择。作为三闾大夫,他有高远的政治眼光和谋略,知道暴秦不可为友,于是结交中原各国,在楚国国内推行美政。他本身也洁身自好,德高望重,堪为表率。他一直希望能够完成“明君美政”的梦想,要实现梦想却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楚王身上。因小人进谗,他被一贬再贬,终于在楚国都城被攻破之际毅然跃身汨罗江,将自己送回了生养他的土地,并不再分离。司马迁称赞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他的死,是用生命为代价向自己的理想做出的最后一跃,可谓死得其所。
而相比之下司马迁选择了忍辱负重。他因在汉武帝盛怒之际为李陵说情,家中又无金赎罪,身受宫刑。自古道,刑不上大夫,更何况这种刑罚对身心伤害尤其之大。司马迁自己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甚至无颜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士可杀不可辱,但他并没有选择和屈原一样的路。在昏天惨地之际,他思考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对命运提出了质疑:伯夷高义,却饿死首阳;李广武功赫赫,却不仅未得封侯,还落了一个自刎而死的下场。经过一番熟思,他终于将《史记》作为支撑其一生的事业,藏之名山,传之后人,并且获得了堪与屈原相比的地位: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屈原和司马迁一个殉道,一个忍辱负重,所选择的道路并不相同。他们的生活并不顺利,都是命途多舛之人,但是按照孟子的天命观,他们都是知天命者,能够明白心中的所求,所以义无反顾。他们不是随波逐流,任由波涛席卷而去,而是在每一次选择面前都认真严肃地拷问着自己的心:你要往哪里去?
存心、养性、事天,这三者本就一体,屈原和司马迁都做到了。如梁先生所说,真正的乐天,是一喜一怒一忧一惧,都是乐乎天机而动,顺自己生命,用着精力去走,然并不是格外用什么力,只是从生命里有力的发出而已。屈原和司马迁正是这样。一花一世界,“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所开创的心学想必从这里借鉴了不少。
弦外听儒音
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最早来自《孟子》,孟子说:“完全相信《尚书》,不如没有《尚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我对于《尚书》中的《武成》篇,就只取其中二三处罢了。仁人无敌于天下,凭武王那样最仁的人去讨伐商纣那样)最不仁的人,怎么会血流得把舂米的木棒都漂起来呢?” 和《诗》特指《诗经》,河特指黄河一样,《书》也特指《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