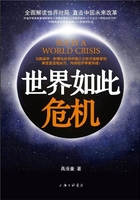刚刚成年的女孩喃芝,在极为朴素的口耳交接里变成了一个传奇。捕风捉影几 经发酵早就成了铁打的事实,附近的村子都知道送桥的喃芝。听说年画上的美人就 是照着她的脸蛋拓下来的 ;听说有城里的公子哥儿呼啦啦开着四个轮子的车专程去 看她 ;听说她出生的那天整个村子的蔷薇都开花了……
喃芝成了送桥村的一块牌坊,就像村口的那棵大槐树一样,是特有的令人莫名 兴奋的标志。只有她,仍然过着不为人知的简单日子,拿着绣花绷做鞋面,在捣碎 的凤仙花里加入烟丝涂手指甲,捧着起褶的《诗经》读一两个佶屈聱牙的句子,或 者在院子里枯坐一整 天,看看乌鸦成 群结队地飞过,看太阳从 东山后面绕 到西山 后面。
久而久之,她恍惚觉得院墙外流传的那个喃芝并不是自己。透过窗户,偶尔能 看见同村的三两个女孩结伴而过,穿着一样的蓝布印花衬衫,编两根俏皮的麻花辫, 边走边说着悄悄话,不经意就被同伴嘴里飘出来的一个男生名字惹红了双颊。她想: 她们多美啊,她们的美丽活色生香。而自己只是被妥善保存的馆藏品,等到青春零 落成泥,也嚼不出酸甜苦辣的滋味。
其实老狗从未想过要对喃芝的生活加以禁锢,只是从小到大,只要她走出家门 都会受到成双成倍的关注。送桥村的人先是问她:“喃芝,你还记得你娘长啥样不?” 她摇头。他们又问 :“喃芝,明明来喜比迎喜先两时辰从你娘肚子里钻出来,咋还是 总被迎喜欺负哩?”她摇头。他们再问 :“喃芝,你乐意被谁讨去做媳妇儿啊?”她 还是摇头。
而且送桥村的女孩们不喜欢喃芝,一是因为爹娘让她们离老狗家的孩子远点, 二是办家家时她们永远只能扮演伺候喃芝的丫头。等到冲天辫可以编成长长的麻花, 同村的少女跟喃芝几乎是不共戴天了,因为让她们芳心萌动的男孩的心思无一例外 在喃芝身上,她们那无处释放的柔情蜜意的目光全变成了仙人掌的针叶,细细密密 地刺落在喃芝的身上心里留下痒酥酥的疼痛。
直到迎桥村的大红花轿停在老狗家的围墙外,喃芝都没说过一个“不”字。她 的婚事由老狗一手操办,自己倒像是局外人。如果送桥村也有一部编年体史书,那 么喃芝出嫁这天一定要用蝇头小楷写上整整三卷纸。从迎桥到送桥的二十里石子路 上都弥漫着一股鞭炮燃尽的硫黄味,大红的爆竹纸被风吹到路边绿油油的麦田里。
“啧啧,真有老狗的,咋就觅得了这么个有钱女婿?” “说到底这闺女儿是享福的命,嫁到许家做了少奶奶还不吃香喝辣,要啥有啥。” “我看那姓许的少爷也是有福,那么俊的闺女,夜里头有他欢的,嘿嘿。”
…… 许家是方圆百里最大的地主,娶喃芝的是三少爷许天白,黄婶用了半个时辰就
把许天白的生辰八字,风流韵事摸得一清二楚。“我妯娌说了,这许天白最喜欢尝女 人的第一口鲜。”黄婶一定要看到他人脸上追问的神色才会悠悠然继续说,“都是叫 许老爷给惯的,当年他要了大小姐房里的一个丫头,那丫头性子烈,跳井自杀了。许 老爷二话没说全给担了下来,打发了丫头爹娘一笔钱。”
若是有人往黄婶碗里送一块红烧肉,她便咬一口继续说道 :“许家长得俊点的 丫头都叫三少爷睡过,这老狗日的也不去访访,为了点彩礼啥都愿意。哪是嫁闺女, 分明就是卖闺女。”
“你瞎操哪门子心?没准儿许天白见着喃芝就收心了。”
“管他收不收心,只要供着吃的喝的,日子好过比啥都强。爹那一辈一房几个婆姨, 还不是活得好得很,女人的能耐大着哩。”
喃芝结婚那天全村人都收到了请柬,大红色洋纸上有几行文绉绉的行书,村里 的老先生告诉大家,大意就是当天晚上,全送桥村的人无论是谁都可以去迎桥许家 吃喜酒,一律不收份子钱。
送桥村的村民哪里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刚嫁给东头开小店家三儿子的女人凤霞 一个劲儿囔着婆家没用,要有下辈子一定得生喃芝一般的脸蛋,也嫁个好人家给村
里人长长见识。
那一晚是从未有过的狂欢,凤霞腆着微微隆 起的肚子和黄婶他们醉眼蒙眬地 看着喃芝跨了第一道门槛又跨了第二道门槛。老狗穿着洗得泛色的中山装和身着大 红唐装的许老爷许夫人等着新人一拜高堂。笙箫锣鼓一直喧腾到半夜,老狗趾高气 扬地在宾客间穿梭,酒过三巡就眯着眼睛夸没见过谁家女婿像许天白这样合他心意。
“那是,不说闹着 玩的,许三少爷是一等一的人才。人长得俊,心眼子也好。” 黄婶夹一块红烧猪蹄放在嘴里,鼓着嘴凑到老狗耳边,“而且听我妯娌说,三少爷虽 是小儿子,但最得老爷的宠,老爷正准备把家里的账交给他管哩。”
老狗举着酒杯,已经有些醺醺然了:“这些……这些都不谈!我……我刘贵虽然 没……没什么大出息,这闺女是……是含在嘴里长大的。其他的都……都算个屁!就 看中天白人……人好。”说完就趴在桌上打起鼾,袖口浸上香菇炖鸡油腻腻的汤水。 许老爷双指夹着酒杯,指着老狗对过往的人戏谑地说 :“瞧瞧我这亲家。”
及至次日中午整个送桥村的人都还在酣睡,前一晚最后的印象是满桌狼藉的杯 盏。醉酒的人在寂静的乡路上引吭高歌,不合时宜的热闹过后留下的是浓得化不开 的黑暗。
迎桥村的大红花轿又停在了老狗家门口,轿子里坐着的仍是喃芝。有过路的妇 人往铁门里伸了一下头就被老狗呵斥回来 :“看!看你娘的看!再看把你的眼珠子挖 下来喂狗!”
那天的阳光里夹着灰,像是被烟熏过,带着一点呛人的又有一点惹人亢奋的味 道。乌鸦仍然成群结队地从老狗家门口飞过,“嘎嘎”的叫声惹得屋顶的瓦楞草动 情地摇曳。静,像是处在龙卷风风眼中的那种静。这静有着巨大的力量,全然不顾 围墙外面摧枯拉朽的七嘴八舌。
消息仍是黄婶从她妯娌那得来的,说是洞房花烛夜许天白要了喃芝的身子,发 现她没有处女血。许天白先是问她的第一次鲜被谁尝了去,喃芝说没有的事,然后
就开始动手打。许老爷一边捋着胡须一边说 :“作孽,我就说那样的爹能养出什么 乖巧闺女。要不是你爹巴巴想攀上咱家,你也不用遭这份罪。”
喃芝被打得鼻青脸肿回来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她从送桥村的骄傲陡然变成 耻辱柱上刻痕最深的那一笔。
“这闺女,平日里瞅着挺本分一人。咋这么不自重哩?” “老狗那么早就砌了个围墙防着,还是没防住啊。” “我看哪,老狗就是 发现了闺女跟男人有一腿子才砌的围墙,要不谁好好地糟
蹋那份钱?”
村里人还等着另一出好戏,就是蛮横的老狗会怎么去迎桥许家大闹一场。但当 他再次走出家门,人们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的半边身体都像缩了水,手垂在两侧瑟 瑟发抖,走路需要人搀扶,口水从歪了的嘴巴里滴出来,“咿咿呀呀”地叫着,像正 在学说话的孩童。
黄婶辗转曲折打探了三五天才在万嫂家的饭桌上传出消息 :来喜听闻妹妹出了 这等丑事赶紧赶回家,要把她送回迎桥去。他说,家里有了这么个败门风的东西自 己今后还怎么讨女人?老狗拿着钉耙追着打,来喜想钻到床下,老狗猛地冲上去扑 住他,却在那时,发作了中风。来喜对喃芝也没有纠缠,他拖开老狗,从床底下发 现了什么,就吹着口哨走了。倒是迎喜有点良心,丢给喃芝几百块钱让好好照顾爹。
此后的岁月对喃芝来说全是虚妄,她放走了链子上拴的那只大狼狗,烧了那本 书页散乱的《诗经》,砸了用来捣凤仙花瓣的小瓷碗。她想不明白,自己清清白白的 一个姑娘家怎么就没流出那滴处女血呢?
哀怨爬上喃芝精巧的眼角眉梢,她几乎不出门了,在院子里种了半垄蕹菜和半 垄韭菜。每天的生活单调干枯,给老狗擦洗身子,或者坐在窗前,看乌鸦栖息在围 墙的顶上,看太阳从东山后面绕到西山后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 起,送桥村 流行起砌围墙。喃芝看不到,在自家的围墙外面,
一叠叠红砖整整齐齐地码着,把每户人家都隔成一座孤岛。她的红颜青春轻薄如同 一张纸片,却最终没能飞过那道高墙。
送桥村的狗越发多了,却因为被关在围墙里,傍晚时分再也叫不出波涛汹涌的 气势。万嫂家的晚饭 搬 到了厨房里,她一早就 锁上围墙上的门,说一句 :“天冷了, 饭菜在外头凉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