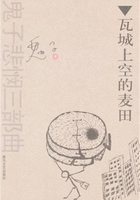胡馨媚
现在这首歌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大雨瓢泼地落下来,我只好跑到街边一处屋檐下,
在路上行走的人撑着各种各样的伞,而那些各种各样的伞又来回碰撞着。雨滴落下 来的声音和路人的雨鞋踢踏声融在一起。这看似平常的声音和这看似平常的画面交 织在一起就像一株有生命的藤蔓那样爬进了我的脑海,因为这样的韵律究竟是那么 熟悉,当初说要成为歌手的你为我不经意写的第一首歌就是以这雨声为主旋律的, 如今这愿望已经成为了现实,你又在哪里。
曾经这首歌 我坐在窗口上,摇晃着双脚,拍打着已被我弄出斑驳痕迹的土墙,尘土在土墙
上翻滚也在我心上来来回回地翻滚。 “小星,小心点咧别栽下来。”阿妈带着些责备嗔怪道,不过我并没有很在意,
反而更用力地去拍打它,反正也不差这几年,它总是要寿终正寝的。 尘土在我脚丫的拍打下越发越大,在飞扬的尘土中我似乎看见了糖糖的瘦小身
影,我从墙上跳下来,奔向村口那棵大树,我蹲坐在那片阴凉之下。糖糖说,在夕 阳落下之前,她会从城里回来。我呆坐了很久,太阳不见得很快就要落下来,而糖 糖也不见得很快就出现。我折了一根树枝开始在树下画画,画些什么好呢。我想了 很久,村口有人走过,多半是对我笑笑,也有人会戏谑地说“:小画家,又在想什么呢? 不画油画改行画沙画了?”
要是在平常,多半时候我会对他们笑一笑,可是今天我却没有,我没有理会他
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自己想自己的。我在靠近树根的地方画了几朵云,在云 的旁边我一笔带过地画了一个太阳,准确些说应该是夕阳。在云的周围,我画上了 几只相依做伴的鸟。然后我画上了自己,一个长着大耳朵的男孩子伸展着长长的手, 我又在旁边画了一个女孩,那就是糖糖了,因为糖糖的左脸上有一颗很明显的黑痣, 同样在这幅沙画中我也画出来了。初次画沙画,我并没有感到困难,沙画的要领我 在画中已经领悟 ——下笔轻。那根树枝在我的手下游走,令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 日落的时间,忘记了日落后糖糖归来的时间。
直到画完,我心满意足地擦了擦沾满尘土的手。抬起头我发现星斗初露,一转 身就看见了等候良久的微笑着的恬静的糖糖,糖糖说 :“我看了你好久咧,小画家。” 她就那样微微笑着,不再说什么,可我却觉得我这一辈子只要看她微微笑或许就足 够了。糖糖急切地想要看那幅画,我却没有给她看,而是拉她回去,因为现在到了 阿妈做好饭的时间。
暑天的热风迎面吹到我和糖 糖的脸上感觉却是凉爽的,我偷偷看糖 糖,她确 实是糖糖,脸上的那颗黑痣还在,我在脸上狠狠掐了一把,感觉到幸福的痛感,才 知道这不是梦。
星空这首歌 吃完饭后糖糖把我拉到树下看我的杰作,其实我也没有细看这幅画,只是在天
黑下去的前一刻,这幅画完完整整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在朦胧的云端,我和糖糖 手牵着手飞翔,夕阳还没有落下,有几只鸟在我们身边绕。
“小星,你真有才,画得太漂亮了!”糖糖依旧是微微笑着,黄昏的天空给她的 面颊染上了那样一层红色,让我甚至觉得布满晚霞的黄昏天空已经俨然变成了一块 美术课上老师用的画布,而糖糖就是那块画布上最美丽的风景。
“我们去看星空吧,糖 糖,总算把你盼回来了,城里没有村里好玩吧。至少我 是这样觉得的。”我双手抱在胸前,十分不满地说道,我害怕有一天城市这样一个 光怪陆离的怪物会把糖糖拐走,今年糖糖的父母三天两头就会把糖糖接回城市,每
次都不超过两天,糖 糖总会要父母把她送回来。“作孽啊,当初抛下糖 糖外出打工 对她不管不顾,糖 糖还是没能原谅他们吧。”我想起在糖 糖第一次离开村子时,我 和阿妈目送糖糖的身影消失时,阿妈突然这样说道。
“才不是呢,小星,你听我说,”糖糖有些激动,“城市里有很多很多的彩灯,虽 然比不上星星,但是和彩虹一样,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光。在商场里很凉快,而且还 有一种漂亮的小人叫芭比,妈妈就给我买了一个套装,可好看了,城市里还有汽车, 开得可快了,爸爸就有一辆黑色的……”
“嗯嗯,”我打断了糖糖的话,“看星空!”然后拉着糖糖躺在草地上。 “真好看,你看那么多的星星,就像城市里一种饮料里面的果粒。”糖糖伸出手
来瞎指。
听到她有又提到了城市的种种,我有些不大高兴,本来想好要给她介绍星座, 可是我想了想就没说,我只是一味地沉默。
糖糖见我不说话,捅了捅我,问 :“小星,怎么了啊?” “没怎么,你说吧。”
糖糖似乎没有听出我语气中的不愉快,反而很愉快地说道“:我唱歌给你听吧!” “嗯。” 然后她就开始唱了,唱的是一首我没听过的歌,她说这首歌叫《白月光》,但是
我使劲地往天上看,却没看见月亮的半点光。于是我问她 :“你不喜欢星星吗?” “我喜欢啊,但是我总不可能唱小星星这样的歌给你听吧,”糖糖停了停,突然
小声说道,“我很喜欢星星,是因为我喜欢小星啊。” “嗯,我也很喜欢小星星。你看那么多的星星啊。”
——“好像妈妈戴的银手镯。” “真的吗,以后我长大了就买一个送给你。”
——“那我怎么感谢你呢?” “你唱歌给我听啊。”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
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 我多希望她能够就这样唱下去,但是在那样一个晚上我确实枕着她的歌声进入
了梦乡。她还唱了很多歌,她唱的歌很好听,让我想起妈妈带我到城里一个唱歌的 地方,城里人说是 K 歌,和那个地方大电视里很漂亮的明星唱的一样。我多希望时 光能在这一个晚上定格,好让我慢慢地领悟那歌声里爱的撒播。那年,我六岁。
分别这首歌 糖糖把一盒糖塞在我的手里。
我久久地凝望着那盒糖,包装很漂亮,我说 :“我会记得你的,可是,你真的 不会回来了吗?”
“唐听,快走吧,就等你了。”她的妈妈在不远处催促着,糖糖的眼睫毛像蝴蝶 翅膀一样来回扇动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没有回答我,然后她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又 转回来在地上用手指写下一串电话号码,然后飞快地向她妈妈跑去。
这次我并不能再次看着她令人留恋的背影,因为她们一家是坐着一辆黑色的小 轿车走的。糖糖没有再回头,我似乎听见她在唱歌,她那么爱唱歌,即使她没在唱, 我也知道她心里在唱,在唱再见的那首歌。
在村口,那个有大树的村口,那个有一幅我为我爱的糖糖画沙画的村口,那辆 小轿车消失在分岔路口。脸上有液体滑过,我不会唱歌,但是如果糖糖看见了,她 也听得懂。
可是她没有看见。 糖糖,我们一定会再见的。那年,我七岁。
听见这首歌 搬家时,从一本书中翻得了一张字条,纸条上是一串号码,直觉告诉我是电话
号码。我犹豫着拨了过去,嘟了几声之后我听见了一个曾经熟悉的声音,那个声音 疑惑地说 :“喂?”
“糖糖,是我啊,我是小星。”我兴奋地跳了一下,居然是糖糖。 “哦,小星啊。有事吗?”那么熟悉的声音,语气却冷淡了许多。但我没在意,
而是更高兴地说 :“糖糖,我就要搬家了,也是搬到城里来哦,你要等我哦。” “真的吗?”
——“嗯。真的,到时候我们又可以一起玩了。” “嗯,好的,没事我挂了。”
——“再见。” 我意犹未尽地听着电话里的嘟嘟声,一声一声地敲击着我的心灵。那年,我八岁。
再见这首歌 再见到糖糖是在一个雨天,她像一只受惊的小兽缩在一个商店屋檐下的一个角
落。尽管几年没见了,可我还是凭着和那个雨天一样潮湿的记忆认出了糖糖。我走 到她身边把伞撑开,湿漉漉的伞沿不断有水珠滴下来,沿着我的脸滑落下来。糖糖 就是在这个时候站起来,带着几分疑惑的语气说道 :“小星?”
“嗯,走吧。”我拉起糖糖的手,走进了雨里。 我才发现我看不清楚糖糖的脸,糖糖瘦了,要不是她左脸上的那颗痣我一定不
会记得她。
“我差点没认出你来呢,小星。”糖糖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的轻,就像田野上一 阵一阵的微风。
“我也是,糖糖要不是你脸上的黑痣我也……”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已经被她没 礼貌地打断 :“哦哦,是吗,这还真是我的标记呢。”
在那时我并没有听出糖糖声音里的不悦,因为天边已经响起了一个炸雷,把糖 糖吓了一跳,雷声混合着雨声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的耳膜。
糖 糖瑟缩在我的怀里,小声地说 :“小星,我会写一首歌送给你的哦,我会记 得你的。”
又是一阵雨声,我朝着小村的方向张望了一眼,遥远的天空远处的云朵十分纯
净,就和当初糖糖的脸一样。我又抬头看了看头顶城市的天空,此时它正被一片乌 云笼罩着,让我看不见它真实的样子,就和现在糖糖的脸一样。
“再过一个月就要中考了呢,糖糖你有什么打算?”
——“我啊,就这样凑合吧,我是特长生,反正以后也是考音乐学院的。” 我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默默无声地替她撑着伞,从她义无反顾地离开村子的时
候,我就知道我和她的路注定了是不同的。那年,我十四岁。
离开这首歌 我站在这座城市的火车站看着熙来攘往的人群,距离我八岁离开小村已经过去了
十年,十年,这时间真的很长。如今,我就要乘上去往我上大学的火车,离开这座城市。 已经很久没有和糖糖联系,当初承诺她的银手镯,也已经买了。糖糖已经和经
纪公司签约,第一张专辑也已经发行。她邮寄了一张给我,但我却没舍得听,我只 是翻开了专辑的目录,关于第一首歌的介绍只有一句话 :“一场大雨,让我遇见了对 的你。”可是,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吧。那年,我十八岁。
最后的歌 我走到附近的报刊亭买了一份报纸来打发无聊时光,我一边打开报纸一边快步
跑回继续躲雨。报纸的第一版新闻头条“新生代歌手唐听又创乐坛奇迹”,旁边是糖 糖的照片,我突然很想听听她的声音。看着街上越下越小的雨,我拿起报纸跑回了家, 打开 DVD,放入那张专辑。第一首歌的 MV 很快在屏幕上出现,我仔细地看着歌 词,一瞥就看到了一句歌词 :“如果能够不把你当成怀念,我等你十年,会相遇在最 初的下雨天。”
后面的歌我听得迷迷糊糊,在合上专辑的时候,玻璃封面突然掉出一张字条, 是糖糖熟悉的字迹 :“打我的新电话 136××××××××,我的私人电话,等你。”
事情过去五六年,我不知道这个诺言我是否还能兑现,我颤抖着拨下了这串号 码,电话通了,过了几秒就被人接起 :“喂,您好我是唐听。”
“糖糖。”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吃了一惊 :“啊?是你?”不过很快那语气又冷淡下来 :“瞿星, 你有事吗?”
瞿星,她只知道我叫瞿星了吧,我捏着茶几上的银手镯,心底里悄悄叹了一口 气。面对这样只出现在我心中不重要的陌生人口中的称呼,我沉默了几秒,说 :“没 事,你挂了吧。”糖糖随后挂断了电话。我一边听着意犹未尽的挂断电话的“嘟嘟” 声,一边又打开刚买的报纸,我端详着报纸上的糖糖,惊讶地发现她的左脸白白净净, 那个标记着她是糖糖的黑痣,已经成为过去。
我这些年来爱的女子,她不再是她了。我看着桌上的生日蛋糕,突然像是安慰 自己一样笑了笑。今天,是我十九岁的生日,我失去了从小到大一直爱的第一个女子。
也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