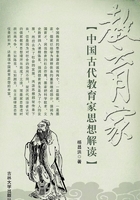再后来他实在受不了学校宿管老师变态的苛求,坚决地迈入了走读生的行列。面对每天单程半小时的囧境,他只得无奈地摒弃了跑步。第一次意识到以后真的要变成一个人的时候突然感觉分外伤感,跑了两圈之后惊奇地发现他正踩着自行车站在操场边缘等着我,那一刻的感觉无可言喻。然后我们一起骑车回家,他一直把我送到楼下。
不过都是最后一次。以后的以后,真的变成了一个人。并且逼着自己去习惯。
南是与我很好的女孩子,我们从四岁在一起开始,到现在巳经共度了+多年的时光。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无论遇到了什么事情,只要同她在一起便会觉得安心。
也许是连老天爷都嫉妒我们这种连体婴儿似的美好,从小学起便把我们生硬地分开,小城虽然不大,一个南干道一个北干道也是一段不短的距离。我曾经至死不渝地坚信着我们可以一辈子走到彼此的终点,就这么相携相依,即使是同性恋也好呢,至少永远都可以在一起啊。
刚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分别进了小城顶级的两所省重点中学,急于在新的环境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闲暇时突然莫名地怀念小时候在一起念书时我坐在她们班门口写作业等她下锞的满足感。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回忆里的斑斓光线,我们就像是突然从彼此的生命中消失了一样。她的外公去世的消息是外婆转告我的,同作为一个单亲的孩子,我很清楚那位拉扯她长大的善良老人对她全部的意义,可是那段最难熬的时光里,我却没有尝试着给她一个肩膀,哪怕是站在她身旁。
重新变得亲密巳经是初二时候的事了。我们一起追星,在偌大嘈杂的批发市场穿梭着捜寻他们的廉价海报,然后像宝贝一样揣在怀里,到+几分钟车程的路边摊吃冰。后来我们养成了习惯,每逢节假日便背着作业到快餐店里边喋喋不休边转动着手中的笔,看着花花绿绿的优惠券不住地咽口水,憋到最后掏出揉得皱皱的钱买两只半价的甜筒,满足得好像上了西天。
我们的外公外婆是邻居,我们的母亲是同学,我们俩是挚友,这一切似乎都是多么理所当然的事情。命运的一切好像都是重叠的碎影,我们都曾悄悄地为了+几年未曾谋面的父亲而落泪,为了母亲的辛苦而难言。对于家长来说,我们的交往几乎是最让他们省心的事情,互相照顾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无数个夜晩,我们盖着一床被子,在凌晨时分注视着对方的瞳仁感慨着自己的心事。青春期的杂乱无章乱七八糟的感情,与学校里的朋友之间发生的点点滴滴,还有关于同一种未来的无数假设。那个时候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她更重要的人了,多好啊,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不是一个人。
偶然间发现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单薄,似乎很久都没有通过一通电话,更没有再手牵着手到偶像代言的店里冲着大大的壁画打招呼:“嘿,六棒!”我写的曰志她很少认真地看完,我们也几乎没有再过多地了解彼此的生活。一切就像是静止了一样,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差别。彼此都是。
我以为,终究是败给距离了。多么令人悲伤啊,青春到底是一个人的旅程,多一个人都只是风景,毋论那个既定却遥远的终点。
直到外婆病倒的那一刻,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消毒水像锥子一样狼狼地刺痛了我的嗅觉。暖气开得很足,我却像置身南极一样不住地打战。直到听到她的声音,然后被她拥住。只听得到时钟嘀嗒而过的声音,还有她的那句棉花糖一样缥渺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把眼睛贴在她的肩膀上,轻巧地抑制住了眼泪的奔浦。那一刻的感觉无可言喻,后来她对我说,我始终坚信,只有在困难面前,我们的友情会迸射出抵挡一切的强大力量,至于那些触摸不到的天空,就让离你比较近的那些人帮你撑起来吧。
那一刻我才明白,原来我并非一个人,原来我并非不快乐。
回答
张晓
时常地,会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尝试着跟我说话,告诉我说,她们读过我写的故事。我自己也常常惊诧,竟然还有人,记得作为一个隐没的写作者的我。
对着这样的探访,我多半只会回复一些温暖的表情,因为我知道,她们也并不期许,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值得惊喜的答复。只是我的感激,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觉到。
最近一篇出现在纸面上的文字,是在去年五月的一份文摘读物上。几乎巳经完全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写字,曾经想要写什么样的字。过去的这一年里,都是在做着让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利用所有能利用的假期到远方行走,巨大的登山包和通向铁路尽头的廉价车票。有时候却卧在住处,抱着电脑混混沌沌就是一天。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写正体字的《国史大纲》。读莫名其妙的专业书,宏观经济学和财务管理。跟传统与红尘的束缚斗争了好多年,+几二+岁终于活出了一种完全分裂的姿态,一半为他人,一半为自己。两方都是满满的怨念。
写写画画仍旧缓慢而肤浅,我也越来越不喜欢有人跟我讨论文学什么的那么假大空的话题,我也从来没有把写出点什么来当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王小波叽咕过一句说立志写作是个减熵过程,而我活着明显是为了给这世界添乱。我不可能平心静气趴着写字,也做不成学问,我甚至很怕自己跟“知识分子”接触太多,谁谁谁说的来着,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渣滓。我深以为然。当然原作者说这话的语境大概是不同的。
年少时,曾经很喜欢安妮宝贝的《蔷薇岛屿》,不算厚重的一本书,都是一些零碎的旅行片段,现在看来,也并不存在什么可以点拨人生的醍醐箴言。你甚至很难从那样的文字中分清,哪些是真正让作者痛过的人生履历,而哪些是出于杜撰。一个写作者越成熟,关于她的真相便变得越难以捉摸。
可是那曾经是让我如此欢喜的一本书,我一次一次地把它带上通往远方的旅途,塞在行囊的最深处,放在长途列车狭窄的卧铺床位上,压在远方陌生城市旅舍的枕下。我甚至巳经记不清,我对它的那种依赖,是在哪一天就突然淡了。有一天我开始独自上路。
中国有4个直辖市、23个省、5个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这些年,我走过了22个。
以前的自己真蠢。时常这样感慨,多了便猜到现在的自己恐怕也不可靠。乐观主义的心态作祟,总安慰自己能进步还是好的。
想来我也曾经傻傻地追着王安忆要签名,我也曾经矫情地与朋友谈理想抱头痛哭,我也曾经怨愤世人不幸不争,我也曾经以为生活是囚笼英雄该有一死了之的觉悟。现在不会了,现在我抱着一碗没有浇头的面也能吃得很开心。
至今为止我仍旧无法诠释或者定义我所追求的强大,这么多年的挣扎也只是拨开了一些错觉,真正的强大不是拥有与一切的不臣服与不爱戴决一死战的决心。至少不仅仅是。
花一整年的时间,想要把自己从环境中独立出来,当我对周遭不满意时,这是我常用的方法,厌倦了,无归属之心,我便不承认这环境对我的意义。
我一贯活得疏离,但又排斥模仿“自外于xX”矫揉造作的名士姿态,迎来送往,还是要的,只是不一定出于真心,多劝自己宽容,便也相安无事。偶尔遇到一些人,让我有众人国士之感,就勾搭结党。我没办法过太孤单的曰子。
诗人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以自全。我给自己修了好多跨海大桥,又造了满坞的船。
年末最后一天了无心看跨年晩会什么的,一个《中国好声音》巳经把我一年对于综艺与娱乐的热情全部透支干净了。想要捕捉就近的记忆,竟然是空网。痛恨自己,竟然对这个刚刚过去的秋天毫无印象。翻过微博才回想起一二。我不爱秋天,也不恨,也不像古人对它伤神,巳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秋风秋雨愁煞人什么的。
可是年关了我想说点喜庆的话。爱抱怨是人自古流传的毛病,也大概真的助力过文学艺术,古往今来看开的不多,多的是不敢,所以在大众的感官上敢抱怨也成了美德,媚曰直言。媚曰敢谏。我有时候会苛责古人,觉得可笑,说什么贫者贫富者富造命奚为的酸话埋怨起造化来。老子老早就说了头上脚下的东西靠不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年后回到杭州,湿冷阴寒的气候让人不自觉又蜷缩起来。原本有很好的设想,新的一年里要坚持素食、慢跑,背完TEF要求的词汇,翻着LP提前制订五个月后去河西走廊的旅行计划。最后却又被这料峭的春寒和无法治愈的拖延症逼进了被窝里,抱着电脑,动漫一看就是一天。
最近,莫名地,连锁反应般地,开始有好多人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出书。妹妹在新西兰,刚刚入大学,很骄傲地在社交网站上发状态吐槽学生会给的袋子里那个夜光的安全套。前面还有状态@我:哥,我想有生之年看到你出书。
突然惭愧得不得了,我都巳经快忘记了,你们竟然还在等。
OnePiece里,为了营救被世界政府挟持的NicoRobin,Luffy带领海贼团攻陷司法岛ENIESLOBBY,站在高处呼喊Robin的名字。Robin含泪喊道:“我想活下去,把我也一起带去大海吧。”作为对伙伴们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