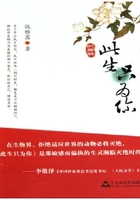故乡的洋槐花
魏春亮
南国的四月,校园里又飘起了洋槐花幽幽的香气,晩风中行走在婆娑的树影下,不禁又想起了故乡的洋槐花。
家乡是一片坦荡的平原,到处是成片成片的庄稼,在庄稼与庄稼的间歇处,如麻子缀脸,散落着一个又一个的村子。所有的村子,也都那么普通,一排一排的房子,几条横穿竖梭,而又坑坑洼洼的小路,承载着几百几千人,活一辈子。每一家人,分得几亩地,劳动耕作,拉扯几头牲口,喂几只鸡鸭,栽几棵树,日子慢慢过着,一代,又一代,都这样,熙熙攘攘总有那么一群在。然而,隐秘的变换却总是逃过了我们的双眼。那一群人中,孙子早就成了爷爷,而爷爷早巳在哭声中入土为安。人世的转换,岁月的更替,现在的一群就再也不是往日的那一群了。离家漂泊的游子经年不归,村子就开始变得陌生了:田地里新添的坟冢宣告了老人的离去,孩子的笑脸在眼前晃动,而于他却显得格外生分了。唯有那石墙青瓦的房子不倒,河畔高树细枝长存,才能给游子以安慰,证明那风物依旧,并非他乡。
平原上的树木种类贫乏,但道路两旁,却随处可见杨楝之类,梧柳之属,在夏曰的蝉鸣中蓊蓊郁郁。每逢冬去春来,新鲜的生命便如锅中之水般沸腾了开来。且不必说那蔓延四溢的野花,墨绿广阔随风翻滚的麦浪,还有那叽叽喳喳乱窜觅食的雏鸡,单单是树木新抽的嫩叶散发的幽香,陶醉其中,也足够心旷神怡。立春之后,村子内外随处可见春风的痕迹,清泠泠流动的河水,远现近却无的草色。然而树枝仍是光秃秃,乱蓬蓬的一团,繁茂喧腾的春天却总是姗姗来迟。可是,不知道哪一天早上醒来,睡眼蒙胧中,你会听到淅淅沥沥的春雨未停,而微风潲一二雨丝入窗,清清凉凉,吹面不寒。睁开眼睛,世界就一片明晃晃的翠绿了。一簇簇肥大新鲜的树叶挂在枝头晃动,黄如透玉,绿似凝脂,欢欢喜喜挤作一团。树叶相击,飒飒作响。雨水划过嫩叶,纷纷扬扬地随风飘洒下来,亲在脸上,落在肩头,也无须拂拭。然而杨花蒙蒙,乱扑人面的情景易衰,待到树叶如妙龄的姑娘,呼啦啦长开时,满树臃肿,便只见威武,不见雅致了。
故乡风树,新旧相续。酥润的春雨刚晕开了娇嫩可人的杨叶,四月的风中就飘起了洋槐花的清香。故乡随处可见洋槐花树,屋前庭后,村南庄北,烂漫时节,景随步移,那一蓬蓬,一簇簇,花开无主,都在你眼前轻摇。一树一树,都挂满素雅玲珑的花串。相形之下,那鳞状的叶子便微不足道了。每当此时,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了芳香的怀抱中,所到之处,香气扑鼻,清心怡神,仿佛每一寸皮肤上都布满了嗅觉器官。而如果恰逢月半,晩风习习,天朗气清,肥硕的月亮高悬长空,光华流泻,打在树梢,一片明晃晃的银亮匝地,摇曳不定。徜徉在明明灭灭的林间,幽香氬,伸展双臂,让晩风抚过肘腋,而灯火阑珊,人声渐远,抚摸着粗犷的树皮,心中常常会浦起种种美好的忧伤,无可名状,却又那么实实在在。以至于岁月流逝,多年以后回想那些恍惚的过往,记忆中的少年仍然沉醉忘归,昨日的感伤如初,依旧激荡着今天的心怀。
然而花红易衰,一旦暖香袭人,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够下洋槐花了。洋槐花树多刺,攀爬而上是不大方便的,高效而廉价的工具是爬钩。寻一根粗细适中,长度足够的棍子或竹竿,再找一把镰刀,用绳子绑在棍子或竹竿前端,系稳扎牢,便大功告成了。奶奶健在时,每年的爬钩都是她弄的。那时我还小,经常跟着奶奶,携着爬钩提着篮子去村头放羊。把羊拴在树上,任它去吃左右的青草,我们就用爬钩去削挂满花串的树枝。细小的枝条好削,锋利的镰刀划过,就干干脆脆地荡落而下。但粗大的树枝却不是那么容易屈服了,通常都需要使出很大的力气,拖着爬钩努力向后下方拽去,那树枝弯得如一张弓,你只要不松懈,继续用力,听到“咔嚓”一声,树枝就断了。而枝之黏刼者却是+分的难缠,削也削不断,拉也拉不折,几枝残损的花束在上面,图然碎落满地花瓣。
洋槐花枝削下来之后,我们就要赶紧拉到一旁,捋起花朵,不然,羔羊的嘴巴是不会闲着的。花序井然,从头到尾一捋,便只剩下一根青绿的嫩梗了。美丽的花朵鱼跳珠溅般落下,须臾满满的一篮便在了。剩下的枝叶委顿于地,也就任羊羔们大快朵颐。将近晌午,艳阳高照,挎着满篮洋槐花,赶着肚子滚圆的羊群归来,咩咩的叫声都格外的悦耳。
洋槐花是香的,无论是在花开之时,还是烹调之后。生的花朵也是可吃的,捋下一把嫩嫩的花儿,细细品味,便是一口丰满的清甜。然而一旦吃得多了,难免作心,所以人们也只是尝个鲜味儿,并不多贪。真正的美味还是需要蒸煮的,把洋槐花放在冰凉的井水中,淘洗干净,铺在早巳准备好的笼布上,满满的一箅子。压上锅盖,不停续柴,通红的大火呼呼腾起,闷闷地烧上一二+分钟,缭绕的雾气中,暖暖的夕照下,屋子内外就飘起了醇厚的香味。我们等不及母亲呼唤,早就迫不及待地拥上锅台,抱着碗眼巴巴地观望。但是母亲还要再点上些许香油,那味道就越发诱人了。多少次,一家人坐在饭桌前,共此灯烛,其乐融融地享受着那点简陋的美味,那味道,那氛围,无论过了+年,二+年,甚至更远的绵长岁月,都会令我依然怀念。
那时候,都是姐姐和我去够洋槐花,带回家来,由母亲动手淘洗上锅的。后来不知从何时起,饭菜就常常是大姐做了,大姐出嫁后由二姐代替,而我,永远是那个烧锅的傻娃子。姐姐在锅台后转来转去,我就坐在锅台前,柴火一把一把地添着,谈笑风生。这时,父母通常会在地里干活,做好饭后,我们便去地头叫他们回来一起吃饭。家里的日子虽然没有饥寒交迫,却也过得捉襟见肘。没有珍馐佳肴,萝卜青菜也足以飨待己了。我依然记得那段难以吃到白面馍的日子,家里一天也只有一两个白面馍,而那又是为劳苦的父亲准备的。但是每次父亲都会故意剩下一块半块,连带一些菜。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小的,通常那饭菜都会顺其自然地归了我。那时蔬菜是很难买得起的,更不用提肉类了,很多时候馍馍加酱豆也就过得去了。但是到了仲春,洋槐花开的时节,桌上的菜蔬便可稍作改观,那种别样的味道总会令我回味无穷。所以夏天涨水时,河水漫漶,被淹没的河沿小路上,河螺遍布,我就会网罗一盆,放在桶中一夜,让其吐出赃物,开水煮熟,挑出螺肉,洗干净,再加上红辣椒翻炒,那味道甚是鲜美。可是辣椒多了太辛,而螺肉虽味美,却不易消化,终究不可多食。相比之下,洋槐花就温润养人得多。然而离乡多年,故地重游却总是假期错过,儿时谙熟的味道却再也无缘重温了。
有时总会觉得生命是一次历险,前途难测,吉凶未卜。昔日那一群在洋槐花树下叽叽喳喳嬉戏打闹的孩子,谁也想不到,年华似水岁月流逝后自己的模样。我本是农家子弟,本应该成为朝雾初升的田野上年轻的种田郎,在父母的安排下,娶一个手脚粗大的女人,生下能吃盐的儿子。可是现在,我却负笈他乡,将美丽的洋槐花,清澈的河流,破旧的老屋,抛在了道阻且长的远方。即使望穿秋水,风雨兼程,你都再也回不去了。只有记忆残存,那些美好的过往依旧,如清清河水下,梦幻虚空般的荇藻,还在脑海摇曳。
可是,有些记忆你以为还在那儿,努力回溯,却发现都早巳蒸发,只留下一种氛围,印证着那时你的欢乐,抑或伤悲。姐姐哥哥是爱我的,但是要记起什么特别关爱的举动,又总是不能。点点滴滴的幸福停留在昨天,组成了我无忧的童年。那时候,姐姐还未出嫁,哥哥也还未娶,奶奶仍然健在,父母也依然那么年轻。我单纯地以为这样的生活可以像春天的小桃树一样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可是现实总是使人措手不及。那年大姐在锣鼓喧天的欢庆声中,流着眼泪出嫁了,而我却不明白为何母亲和奶奶也泪眼婆娑。然而几年后,当二姐也披红戴绿进入婚车,寒冷的北风中我却哭得不能自巳。从此之后,我便觉得这个家巳四分五裂了。不久哥哥也结了婚,父母也出门打工糊口,而我也巳上了高中,进城读书了。再后来,奶奶突然暴病,去世了,在一个阳光惨淡,朔风野大的冬日下葬,葬礼上人们哭作一团。我看到奶奶的遗体安然地躺在棺材里,却总也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就可以那么无缘无故地睡去,千秋万代,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无论是丰功伟业,还是鸡毛蒜皮,都与他无关了呢?如果死亡是那么无常,人们或迟或早都归于荒冢,前尘不曾见,身后未可知,两段茫茫无涯之间,这一刹那虚无缥渺的现世又有何意义呢?多少次站在奶奶的坟前,风吹着离离荒草,呆呆地愣上半天,总是不禁惘然若失。而回过神来,却总是在恍惚间难以找到回家的路。所谓家,也仿佛早巳不是家了。一家人东奔西走,辗转他乡,留下孤单单的老屋,阒无人迹地守候在故乡,只有在春节来临团聚一堂时,寂寞巳久的屋子才能添点生气。阳光明媚的早上,姐姐姐夫带着酒肉来到,还有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孩子们吵吵闹闹,而姐姐和母亲或邻居絮絮叨叨拉起家常。而中午做饭时,姐姐依旧在锅台后转来转去,我依旧坐在锅台前,柴火一把一把地添着,却再没那么多话可说了。吃饭时总是觥筹交错,而父亲每次都会喝醉,有时还会哭。父亲年幼失怙,兄弟姐妹尚小,一家人全靠他支撑,风风雨雨走来,心中苦楚,却无处言说,只是拼命地酗酒,喝醉了,就沉沉睡去,鼾声雷动。任别人怎么劝,他也依旧故我。午后的时光在父亲的鼾声中寂寞地滑落,一霎儿太阳便西斜近地,融在远处那片芜杂的树林里,寒雾轻起,姐姐姐夫又在冰冷的阳光中离开了,抱着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看着他们风中憔悴的脸,心中的伤悲总是无法抑制。觉得生活不能这样过啊,可是生活又该怎么过,我却又说不出来了。我们可以摆脱贫穷,可以摆脱困厄,可一切都在流逝,那遍布华林的悲凉你又怎么摆脱呢?从前那么坚定地认为不变的东西,在人去楼空后,巳经变得面目全非。常常会想不明白,人生怎么会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可那些逝去的,毕竟是远远地逝去了。土地的元气会耗竭,高宇广厦曾倾塌。岁月的河流里,无论你如何努力打捞,得到的始终是一把又一把的空劳图叹。只剩下明日山岳,世事茫茫,嘲笑着浩瀚宇宙中,一颗渺小星球上几个卑微生命的哀欢。
草木无言
魏春亮
河流有声,草木无言。
我相信,树木是乡村最忠诚的守候。立根大地,洒下绿荫,不择细土,不慕繁华。树木远离城市的灯红酒绿与醉纸金迷,扎根于穷乡僻壤和荒山野岭。一成不变地沉默守候一方水土,守候一个村庄,相对无言。
树木美丽而朴实,不需任何臃赘的修饰。一身笔直地挺立于阡陌之间,露出结实而优美的树干。我曾经抚摸过无数树木的树干。粗糙的树皮拉过手心,就像同村庄进行一次心贴心的谈话。那种感觉完全不同于抚摸滑腻的楠木家具。树干是活生生的,带着自然的体温,给人以安慰。而树枝开满一头的绿叶,在阳光照耀下闪烁;或者光秃秃的树杈在寒风中战栗,直峭峭刺向苍蓝的天空。
我无法向你描绘那一片繁密的树林,我坚信那是自然之神赐给大地宽厚的恩典。徜徉在明暗交错的树林里,带着崇敬的目光瞻仰那些庄严肃穆的树木,我常常伥然若失。有时出神地思考回忆,看到渐逝的夕阳拉长了树木的影子,凝视着远处浸透在夕阳中的杂树,试图读懂它,却发现那是徒然。与树木相对忘言,以为对它知之巳深,临纸欲书,却始终笔墨艰涩,言语无味。树木无言,撑起村庄的脊背。它同村庄的秘密一同藏在大地的深处,我永远无法觅得。
走在平原上,细心的你会发现,一个树木密集的地方,就是一个村庄的所在,农民的家也就是树木的家。我一直相信,朴实的农民在有意无意中把树木当成了自家的兄弟子女,不肯让它远离了自己。我见过那些田野中远离村庄的树,孤独地站在低矮的庄稼与野草旁,在辽阔的天穹下,结满一树苍凉与寂寞,就像那些流浪异乡的兄弟,眼神凄迷哀漠。那些树木植根荒野,守望着远处的村庄。树木从疏到密,旅人就知道家要到了。而那远离乡村的孤树,就是这种幸福的起点。
我想,树木是最苍凉的。它在风雨中站了一辈子,守候了一辈子,见过李家的儿子娶进媳妇,听过张家的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也许王家老人离世的幡纸也挂在了树枝上。它见过一代又一代的人出生,又一代一代地老去。旧的去了,新的来了。房子倾圮了,老人离去了,村庄又换了另一个模样。有的树木累了,死去了,有的被砍掉了。在一年又一年的荣枯中,却总有些树木留了下来,一成不变地守候着苦难的村庄,不离不弃。
我不知道该对野草持什么态度。如果说树木是乡村的守护,那野草就是乡村的贼。凶猛恶劣,阴险隐秘。在久置不耕的田地,荒废无人的庭院,野草像横流的欲望肆无忌惮地蔓延至每个可以触及的角落。路边,沟壑之中,甚至在你家砖地的缝隙中,都能看到它们顽强的身影。它吞没庄稼,藏污纳垢,凶险广袤。野草是长虫、蚰蜒、蚊子以及家禽的天堂,走在齐腰高的野草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脚会与什么生命不期而遇。在乡村,野草不属于可规训的对象。它有的是崎岖的枝蔓,蜿蜒的路径。它的美学与城市广场绿地上整齐划一的草坪完全不同,有着浑然不可亵渎的剽悍之美。镰刀、大火、牲畜奈何不了它,就是在现代化的农药面前,它也敢傲然挺立。它那春草年年绿的坚强与顽固让人肃然起敬。